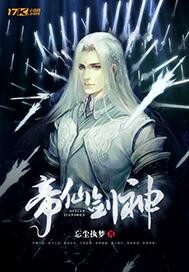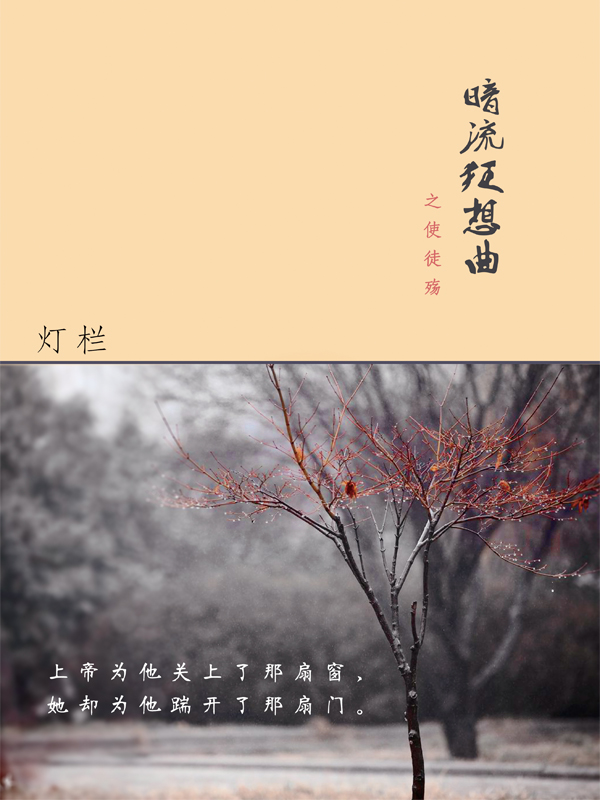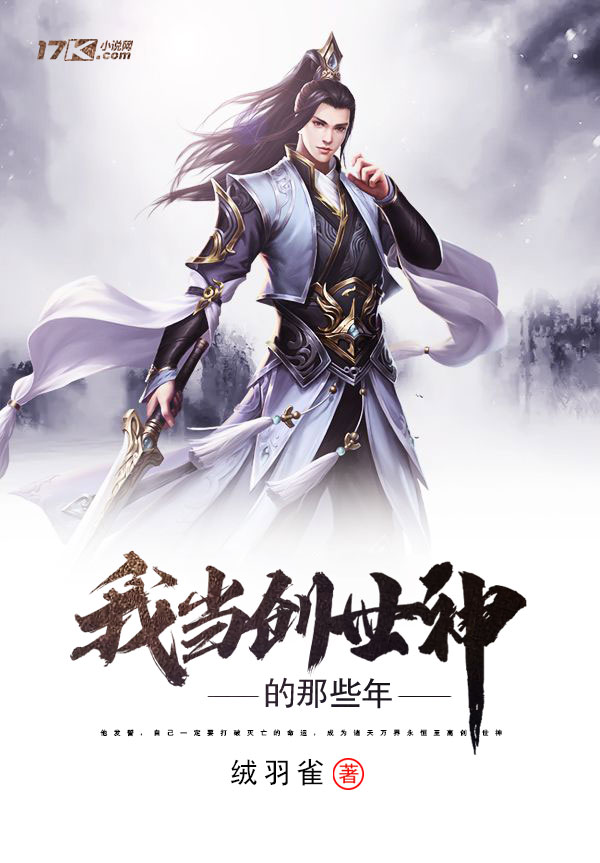金玉兰,不知何许人也。少时聪慧。父母皆从商,而玉兰不以其为意。性好杂学博引,诸子百家、历朝故事悉有涉猎。玉兰十六岁时,偶学诗,自作数篇,对仗韵律无师自通,长者先生甚为赞赏,以为其有天资也。
当是时,格律诗已逾千载,大不若唐宋之时繁盛,亦不属科举之内。故鲜有人读诗,作诗者更是凤毛麟角。故玉兰亦以诗为友,仍从读书正业。数载之后赴科举考,虽非,亦二甲及第为进士。奈何天不遂人愿,入官场后,玉兰恃才傲物,兼不通人情经济,以致寸步难行。玉兰天生有雅致,兼以经典修身养性,见凡尘纷攘,继而生出世之心。于是携书墨耕具,隐居于太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中。
此地远离俗尘,凡人难觅,山明水静,风清物灵。玉兰居于竹林之中,结一茅舍名之为“墨竹斋”,自号为“竹间墨客”,日日题诗咏赋,饮酒闲游,同星月为伴,与麋鹿为友。虽不在富贵场、温柔乡中,倒也悠然自在。
一日,玉兰上山采药,见峰下有一石,其上文章历历。异之,乍读似富贵家族之故事,反复品诵,方知其非等闲之书。日日前往观之,初阅尚迷,再阅则悲,三阅则时掩面而泣。乃至性情大变,一改原乐山乐水之心,居家自守,愁容满面,无端落泪。其诗亦不类少年所作,多以伤春悲秋,兴衰之叹为记。竟茶饭不思,形容萧索,自是积愁成疾。人皆谓其痴病,不晓其真真入了书中也。
如此经年,身渐不支,卧于草榻之上,亦无心求医问药,而书常在枕边。玉兰复诵《葬花吟》之时,忽五内崩催,吐血数斗。自知时日无多,便题绝笔一律:
曾经廿载亦疏狂,偶阅天书枉断肠。
望去人人皆泣血,思来字字总凝霜。
凤鸾怎奈芳华尽,粉黛何辜薄命殃。
但愿千生修正果,红楼圆梦再无殇。
诗罢,语邻者曰:“观某此生,虽有异才,亦无成大事。山中虽静雅悠然,奈何无福消受,今将永诀。我本须眉浊物,生亦无求,死亦无恨。然每每见书中女子,其灵秀若此,竟入薄命司,伤怀泣血,实不忍观之。但求君葬吾于峰下石旁,愿倾千生之力,唯求梦圆红楼!” 言讫气绝,年方弱冠也。邻者亦不知所云,仍全玉兰之遗志,葬之于青埂峰下。
不知过了几世几年,石旁玉兰葬身之处,竟生长出一株仙树,乃金枝、玉叶、开兰花。空空道人再访此地,见此树非但形容甚异,更有文字镌于其上,知又是一灵物,便问其身世。树答曰:“某前世本凡人,隐于此山之中。无意阅石上之故事,悲痛欲绝。今生立于此地,日夜撰文,欲续其情节,以救书中之人。吾知先生即为空空道人,在此俟君,还望君抄录某之故事,传于世间,即使贻笑大方,也权当消遣世人,圆吾之梦,圆历来《石头记》读者之梦也!”
空空道人听罢,抚掌大笑曰:“自古有闻续书者,未曾闻救书中之人也。《石头记》传世二百余载,尚未有人如汝之痴,亦是汝与此书之前缘宿孽,可谓知音尔。仙石由女娲炼成,又经大士真人点化,而汝终为凡人,岂能与之并肩乎?虽然,念汝一片苦心。其文尚有可读之处,我本闲人,纵抄录了去亦无妨,能否传世,就看汝之造化了。”提笔沉吟几刻,在其后提了一偈云:
金枝玉叶绽幽兰,万字文章木上刊。
若问缘何生此地,红楼故事待重观。
金玉兰拜谢不迭,空空道人遂将树上文字记下,分其故事为三篇,各述书中一人,名以“金之梦”、“玉之梦”、“兰之梦”即以金玉兰姓字所题也。篇篇各自独立,自成故事,却又相融互通,其间千丝万缕,观者不可不察。体裁类纪传史书,以记事为基,其间又有诗词曲对,若章回演义般,颇可玩味。不知从何而起,亦不知至何而终,乃《红楼梦》中之人,于金玉兰之梦中所历也。此即《梦圆红楼——金玉兰》之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