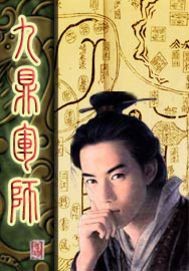接到当朝太宰石天弓亲自命人送来的请赴家宴的请帖,须发皆白的范进范军师既感到喜出望外,又有些诚惶诚恐。
说起来这些天也把这位范军师累坏了。当朝天子亲自下旨,委任平南王唐万年为“征西讨逆大将军”之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免不了他这个军师操心。既要保证大军出征的粮草供应充足,还要协调各路人马服从统一调度,更要动脑筋思索作战方略,为主子献计献策,范军师整个人足足瘦下来了一圈。
他虽然没有细想石太宰在大军出征之前还有什么要特别交代的,同时也仔细审视了自己工作近期可有什么纰漏,但终归是一头雾水。只得早早命人备马,向平南王告假,只身前往太宰府赴宴,内心却对太宰大人如此看重自己这个随行军师有些小得意。
本来嘛,军中有数万将士,朝中有上百的文臣,堂堂当朝太宰大人只请自己一个随行军师赴宴,分明是高看一眼。谦逊乃做人之美德,即使获得石太宰当面夸赞,自己也要沉得住气,不可得意忘形,更不能一时大意,喝多了酒吐露出内心深处埋藏的那个巨大秘密。
一面走着,范军师一面在马上低头想到。不知不觉已然来得了太宰府门前,他连忙翻身下马,向门前站立的护卫抱拳施礼,请他们进去通禀,就说范某如约前来赴宴。护卫入内之后,须发皆白的范军师抬眼望着太宰府高阔的门楼,长长出了一口气,心中暗道:我与石太宰今夜把酒言欢,这也算是惺惺相惜吧?
那名护卫很快就走了出来,挥手示意请范军师随他入内。
跟在那名护卫的身后,须发皆白的范军师步履匆匆,却又忍不住好奇地东张西望。这太宰府原先不只是哪一位大齐王爷的府邸,假山林立,绿树葱茏,花香四溢,长长的游廊弯弯曲曲,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一只脚刚迈过屋门槛,范军师便看到满脸堆笑的石太宰身着便服,迎了上来。
范军师连忙低头准备跪倒施礼,却被石太宰一把拉住。
石天弓笑着说道:“这里又没有外人,范军师何须如此?鄙人也只是准备了一些薄酒小菜,在大军出征之前,想与兄台单独唠唠嗑,拉拉家常而已。”
闻言范军师直起了身子,心里也顿时感到轻快了许多。
二人对面落座之后,石天弓端起酒壶,先给自己的杯盏中斟满了酒,又起身往范军师的杯中斟酒,范军师连忙爬起身来,双手接过酒壶笑道:“太宰大人不必客套,我自己来。”
石天弓也不与他过分客气,伸手就把酒壶递给他。待二人都斟满了杯中酒,石天弓笑着举杯道:“我大军出征在即,想来这些时日范军师里里外外也忙的够呛。今夜此地就你我二人,不妨畅所欲言,喝个痛快,也算是我为尔等壮行了。”
二人将手中杯盏轻轻一碰,都喝了个底朝天。放下杯盏,石天弓眯着凤眼问道:“此次西征剿灭西北马家军余孽,也许是我大楚开国以来平定内乱的最后一战,从此我朝可高枕无忧了。但不知范军师心中对此战可有必胜的把握?”。
范进抹了一把下巴上花白的胡须,开口哈哈笑道:“太宰大人大可放心。马家军虽有小股余孽得以侥幸逃脱,但人心惶惶,已如惊弓之鸟,况且群龙无首,完全不足为虑。反观我方,我家平南王爷亲自挂帅,又有“朱雀将军”一旁鼎力相助,包括“青龙将军”的人马,无论是兵力、士气、装备,我大楚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短则仨月,多则半年,匪患尽平矣!”。
石天弓闻言红光满面,微笑着连连颔首。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主动给范军师面前的空杯中斟满了酒,范军师也不再客套,微微欠身点头致谢。
石天弓抬手给自己的杯中也斟满了酒后,踏踏实实地一屁股坐了下去,笑道:“有兄台的这几句话,当今圣上与在下就都算是吃了定心丸了!我这里只是想提醒一下兄台,也请老兄转告我五弟:斩草务必除根,万不可念儿女情长,心慈手软,为大楚的将来埋下什么隐患。”
范军师先是一愣,继而马上明白过来,低头微微抱拳道:“烦请太宰大人及圣上放一万个心:当初我家王爷却曾对那马大帅之女一见倾心。但既然圣上将那小女子许了定北王,我家王爷就从此彻底断了念想,甚至恨的牙根发痒,绝不会心慈手软,妇人之仁!况且,圣上、太宰与我家王爷乃八拜之交,作为兄长,应该比我这个外人更了解平南王之为人。我家王爷平日里虽心直口快,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国家社稷与儿女私情之间,从未含糊过!”。
石天弓默不作声地微微点了点头,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又用眼角瞄了范军师一眼,转换话题笑着问道:“平定内乱之后,范兄自己可有何打算?是入朝为官呢,还是继续留在我那五弟军营之中?”。
范进低着头,眼珠在眼眶里转了两转,抬头笑道:“不瞒大人,老朽一身的伤病,算起来也是风烛残年了,实在是无意入朝为官。只愿呆在我家王爷身边,帮他出谋划策,或者干脆告老还乡。”
石天弓不动声色地把玩着手中的杯盏,貌似随意地问道:“看来老兄对我五弟倒也算是忠心耿耿,难能可贵!依阁下看,当前定北王重任在肩,带领属下官兵在塞外与那草原悍匪拼死一战,没个两三年恐怕难以抽身;倘若内乱先平,平南王立下大功又兵权在握,他有无可能成为第二个阮武呢?”。
须发皆白的范军师眉头一耸,继而仰天大笑道:“太宰大人您又多虑了!我家平南王爷行事历来光明磊落,是根直肠子。大人怎好将其与阴险狡诈、大逆不道的阮武相提并论呢?别忘了当日平州被围,是平南王马不停蹄,挥军前来为二位兄长拼死解围的!”。
石天弓微闭双目思索片刻,轻叹道:“说的在理!没有五弟统兵前来冒死相救,我与皇兄恐怕早就身在九泉之下了。五弟虽然忠厚,怕只怕将来受了什么宵小的蛊惑,乱了心思!那依仁兄看来,我大楚的祸端将来会起于何处?”。
范进歪着脖子又捻了一下胡须,沉吟片刻开口道:“既然太宰大人说了让在下畅所欲言,那我也就百无禁忌了。依在下看来,将来大楚有内忧和外患两方面。外患便是草原蛮夷,虽然朝廷派了定北王重兵出击,占尽了天时,但地利与人和为我方所欠缺,恐怕难以一蹴而就!想那大齐王朝近百年来,在飞虹关屯有重兵,都未能消灭这些草原悍匪,足见其凶横霸蛮。这其二么……定北王此人貌似忠良,实则诡诈至极。其行为乖张,匪夷所思,万一哪天他要起兵对朝廷不利,恐怕比起阮武有过之而无不及。圣上与太宰大人不可不防!”。
说完,范进翻着眼皮,仔细观察着石天弓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却也未能看出个所以然来,未免心中平添了几分遗憾。
天上月影西斜,二人在觥筹交错、谈笑风声之间,你来我往进行了几番相互的刺激与试探,终于在宾主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晚宴。
石天弓亲自将范军师送到府门外,半醉半醒的范军师行礼拜别之后,摇摇晃晃地翻身上马。
石天弓捋须笑道:“今夜你我二人彼此敞开心扉,喝的痛快,更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老兄没有喝多吧?要不要我派几个人护送你回军营?”。
须发皆白的范进晃着手说道:“多谢太宰大人盛情款待,在下感激不尽。大人请放心,这点酒奈何不了我,请大人也早点回去歇息吧,不必劳烦大人府上差人相送了!”。
石天弓微眯双眼,也不强求,抬手轻捋着颌下长髯淡淡说道:“那就请仁兄一路之上多加小心,多多保重吧。”
马蹄上的铁掌敲击在深夜的路面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马上须发皆白的范军师微低着脑袋,貌似在打盹,其实脑子里一刻也没有闲着,翻来覆去回忆着刚才与太宰大人机锋暗藏的一番对话。
夜深人静,宽大的街面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微风掠过树梢,只有树叶发出的细微沙沙声。
眼见军营不远了,范军师抬起头来,停止了纷乱的思绪,打马扬鞭,加快了步伐。胯下的马匹撒开四蹄小跑了起来。
忽然,昏暗之中横在路中央的一根细细的绊马索发出了一声低沉嗡嗡的混响,仿佛是一根被人无意中突然拨弄的粗大琴弦。
范军师猝不及防,马失前蹄,头朝下从马背上翻滚着跌落下来,前额重重地撞在路边一块锋利的尖石上,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瞬间便失去了知觉。
片刻的功夫,从旁边的一棵树后,闪出了两个蒙面的黑影,此二人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俯身趴在范军师头颅附近观察了片刻,手上却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只是彼此点了点头,使了个眼色,便又同时转身,一前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