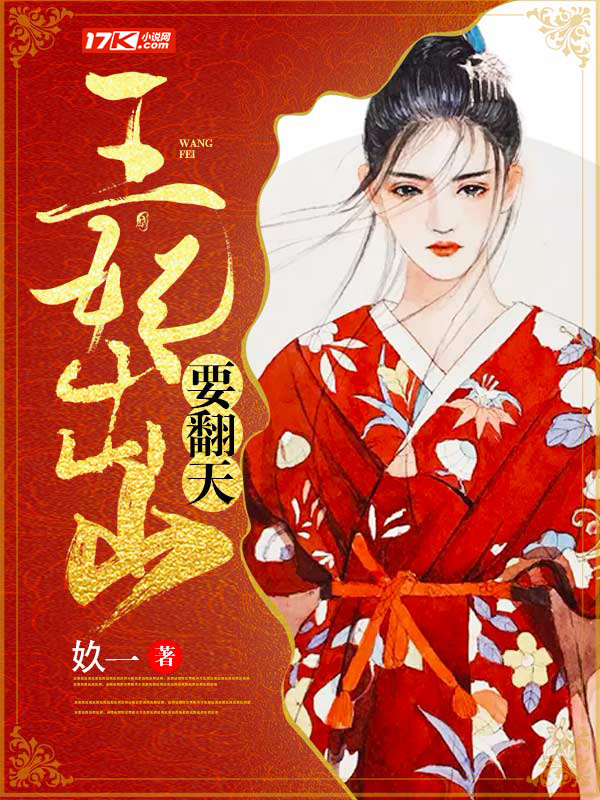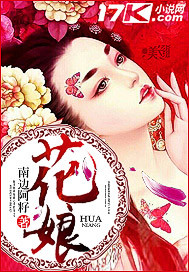沈怀稷进宫同沈昱宸说了风栖鸾已离开的事,面上镇定,心中还有些虚,一直没敢看沈昱宸的脸色,等了许久也没等到那凌迟的眼光。只听到沈昱宸轻叹了一声,“也罢,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沈怀稷怀疑自己听错了,抬头见帝君确实并无异样,对帝君此举深感意外。又听沈昱宸道:“二月上旬将往皇陵,早些准备吧。”
沈怀稷应了一声便退下了,出门却见晓风楼的女官木槿带着一个极窈窕的美人儿来了,这美人儿正是除夕夜宴上博了个好声名的宋伊雪,因着鸾儿的事,沈怀稷对宋伊雪也没什么好印象,也便没有理会。
元福公公来禀木槿与宋伊雪到,沈昱宸淡淡回绝:“不见。”
宋伊雪望向身边的紫衣美妇,想要从她那儿得到一点提醒,木槿却笑道:“此番前来便已告知过宋小姐,必要让您自己入了帝君的眼,倘若借公主的势进了这道门,那么小姐在帝君眼中与这宫中伺候的宫人便无二异了。”
美人儿目光里暗含深思,继而闪过一抹决绝,“请再为小女通传,就说宋太傅女伊雪来向陛下请罪。”
元福公公低头眼里藏着一丝笑,这宋家女倒也聪明。果不其然,沈昱宸指间的笔停顿了一下,继而放下,“传。”
宋伊雪脸上绽开一抹微笑,她知道搬出父亲一定可以,宋太傅是帝师,而帝君又在举国兴学,倘若为人君者尚不能尊师,那又何以面见天下百姓。
待她二人见了礼,沈昱宸也不打算多费口舌,“宋小姐此行何意。”
宋伊雪神态自若,“臣女已言是请罪。”
“你并无罪。”他并无意治任何人的罪,宋浩陵的事已经过去了,既然无缘,又何必勉强。
美人儿双膝一屈跪下,声音纤柔,目中盈盈似诉,含悲带怯,“蒙长宁公主之恩,携伊雪在宫中小住,然半月未见帝君一面,此伊雪之罪也。”
“哦?宋小姐此意是言朕之罪过,长宁公主携你入宫不假,莫非长宁公主的客人,还需朕亲自接待不成。”沈昱宸似笑非笑,目中已含了冷色。
“非也,公主常言帝君国事操劳,令伊雪于闲暇时为帝君排遣忧闷,伊雪有负公主所托,此伊雪罪也。”她将头埋的更低了,目光却不自禁往上飘了一眼。
“是么,多谢公主美意,然则既是为国操劳,如何敢为此烦忧,你,且回去吧!”
宋伊雪霍然抬头,“帝君这是嫌弃伊雪笨拙么,伊雪自幼也是父亲特地请了先生来教导,虽愚笨不曾学得专心,但既是公主所托,伊雪不敢有违。”
沈昱宸望着她,眼中看不见任何情绪,“如此,今日你就留下来吧。”
宋伊雪心中松了一口气,此次铤而走险恐已惹帝君不悦,父亲之名已借了两次,长宁公主也绝不可再谈及,接下来可就真的要靠自己了。木槿见此行目的已达到,便先告退了。
宋伊雪此刻守在沈昱宸身边,心中既欢喜又紧张,她终于又离他近了一步,可到底他不是常人,她的每一言每一行都不能让他生厌。沈昱宸留下她后,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她一眼,嘉宁殿中日日人来人往,多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同。宋伊雪温顺的如同一只小白兔,静静地站在他的案前,连呼吸都是轻柔的,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时辰。
沈昱宸搁下朱笔,眼睛有些酸痛,一如往常闭上眼休息一会儿,一缕若有似无的香气吸入心肺,眼皮愈发沉重了,不想再睁开,沉沉欲睡。好在他还余有最后一丝意识,没有真正的睡过去,睁开眼,望见是宋伊雪往紫金炉中添香。他一手揉着眉心,问:“这是何物?”
宋伊雪柔声道:“这是特制的安神香,可以使人身心皆怡,是伊雪手脚笨拙,打扰了帝君歇息。”
沈昱宸并未做声,宋伊雪又双手捧了茶去,他也未接,“如果你来此是干些下人的事,那还是退下吧,宫中不缺宫婢。”
宋伊雪面色微变,眸光流转,低眉浅笑:“世人皆知帝君爱琴,不知伊雪可有幸为帝君抚琴。”
“世人皆知我喜琴?”沈昱宸冷笑了一声,不甚在意,却是直言拒了,“宫中已有琴师。”
宋伊雪脸上笑容僵了一僵,他说的可是柳清持,长宁公主说过,帝君是绝不会对柳清持起什么心思,可如今看来,倒是在处处维护。
“愿为君舞。”她垂首静立。
“木槿应当提及朕不好歌舞。”如此不留情面,漠然如是。
“帝君何苦为难伊雪。”她抬眸,目中有泪,泪里是他。
“不得君心也是为难?”他抬头望着她反问。
“帝君不曾真心接纳我,不愿看我一眼,又如何能得君心,伊雪何辜?”
“哦?宫中美人何其多,她们又何辜?”沈昱宸淡淡回她,“若是每个人都要用真心相待,又哪里来的那么多真心,只这一颗,自然是只能给一个人。”
“君心尚在?”宋伊雪犹自挣扎,也便直言不讳,他的那一颗可还在?
沈昱宸一怔,目光重新落到她身上,此时才算是看清了她,京中美人以宋伊雪为首,传言不虚,名门闺秀,温婉典雅,诚如是也。他暗叹了一声,也就不再绕了,“长宁公主选中的是你,朕并未选中,宫门深似海,你大好年华,何必困在这宫墙里。”
泪珠凄凉滑落,他竟如此直白的不给她一丝机会,喉头哽咽,“但为君故。”她声音柔婉,此时听来却分外悲凄。
“你说什么!”沈昱宸深感意外,这怎么可能。
她抬袖拭净了眼角,道:“伊雪思慕帝君,常听兄长提及帝君圣明,伊雪记在心中多年,幸得长宁公主垂青,伊雪心甘情愿久伴君身。”
“退下吧。”他再不看她一眼,淡淡下了命令。
宋伊雪难以置信,“帝君说过今日留我在此侍奉。”
“不必了,你退下吧。”他神情疏离,不容置疑的口气让宋伊雪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唯有依照他的命令,脚步虚浮地出了嘉宁殿。
沈昱宸心中似压着一块巨石,烦闷不已,便也出了嘉宁殿,信步而走,不知不觉又到了隔水亭。亭中一抹绿影如春色,正是昨日才回来的柳清持,倚着朱栏,不知在想些什么。他有一丝无奈,“你这病才刚好,就在这吹风,还真是任性。”
柳清持听到步声便知是他,也就没有起身,听到他说任性,她恍惚是笑了,细想这段时日她的所作所为,还真是任性的紧。
沈昱宸站定在她身边,神情有些飘忽,“近日我听人说,世人皆知我爱琴,清持,你以为呢?”
“嗯。”柳清持脸上透着疑问,不知他何有此一问,此事世人皆知,君主是爱琴的。可她身为他的琴师,至今还未为他弹上一曲。
“果然啊!”他嘴角泛起一丝苦笑,那是他最不愿想起的过往,“我其实很讨厌琴,只因十年前你说我不如他,自此我便存了与他一争高下的心思,时至今日,你可还能说我不如?”
“对不起。”柳清持心中隐隐作痛,她知晓幼年那番话说的太过狠毒,时至今日还是他心里消不散的阴霾,“你当时意志消沉,我是为了激你,那些话当不得真。”
“当不得真,可是我当真了,又该如何呢?”
“你想要如何?”
“不许把我当成他。”只要不将他当成是那个人,那便没有什么兄妹之名了。
“好。”她点头,其实她又哪里把他当作是谁了,只是他心里有这个结,那便遂了他的愿去,应下就是。
“二月初会前往帝陵半月,无须带上阮和。”
柳清持皱眉,“不去,你去祭拜父母我跟着去做什么。”
“他也葬在那里,长山与帝陵相隔不远。”
“人都已经死了,还要这些虚礼何用。”柳清持从未去祭拜过那早夭的哥哥,他是个自尊极强的人,生前不用人怜悯,死后自是也不愿别人看到那半壁残碑,倒不如就此让他烟消云散了罢。
“也罢,随你。”沈昱宸不勉强,沉吟道,“那么,便将卫小蕤召进宫来,陪你些日子吧,卫家小妹这些日子不知犯了何事,禁足已有好几日了,算起来,还是从云岫请卫奚喝茶那一日算起的,这卫家小妹在城中也是出了名的率性爽朗,你出城那几日还救过你,便算还了她这个情分,你看如何?”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