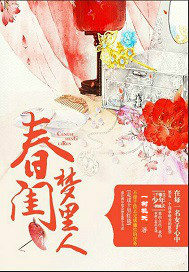夏日深夜,天朗风清,迢迢星汉布满禁宫上方的天幕。居中最为巍峨高大的含章宫里,四角垂下巨大的宫灯,方圆十丈内,清晰可辨,殿内,沈昱宸颓坐在地上,苍白的面容阴郁沉默,仿佛这已是一架无主的躯壳。身侧散落着几封开启的密信,一字一句,如箭穿心,拔不出,也穿不透。
他眼中闪过一丝阴霾,抓起信笺将它们撕的粉碎,泄愤般的举动不曾让他得到解脱,有些东西从来不是毁了就不复存在,无知也是一种幸运。他从来不知道,原来他还有过一个哥哥,一个在仇恨中死去的哥哥,他无法知晓,他的父亲到底是有多爱那个无情的孩子,才会为他冠以兄长的名字,跪坐在一地残篇字句里,一种痛苦的悲哀涌出眼眸,“父皇,你好残忍,你可有想过我半分···”
靖宇帝,昔宇朝储君,弱冠得子流落于民,七年,迎而归,名曰昱宸,归三月余,持素玥银环共外戚白氏女相斗,利刃穿胸,伤重不救,殁于禁宫,帝抚尸而泣,悲痛欲绝,感其年少而夭,遂将子驱逐皇室,藏而不记,子故后,生母慕氏夫人去处不明。
——《靖·宇帝秘史纪·卷三》
他此时心里似乎只剩下沈昱宸三字,他那死去多年异母兄长的名字,后来又成了他的名字。若那人还在,这含章宫,天下至尊,原本都是要给那个人的吧。父亲是有多看重那人,才会在他死后还让他顶着兄长的名字存活于世!母亲,又怎么肯答应?
长夜漫漫,从没有像今日这般难过,空旷的殿宇一如他此刻心无所依,连呼吸都是压抑的,溺水般的神智晕迷,沉浮无力。
待到天色大亮,一众宫人守在殿外,领头的元总管很焦急,时辰不早了,帝君再不唤人进去,可要误了今日早朝了,帝君虽年少,却向来勤勉有加,从不肯误了政事,今日这般,莫不是夜里凉风吹着病了,思及此处,心中大骇,也顾不上规矩了,匆忙就要推门而入。
才走了两步,殿中传出少帝冷淡的声音:“传旨,今日免朝,另,宣祈王来见。”
祈王沈君翌乃靖宇帝堂弟,同长宁公主更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若据礼法监国重任该由祈王来担,奈何祈王生性懒散,偏好美人香茗之流的风雅逸事,当年还是前朝瑜王世子之时,美名已四国盛颂,尔后随靖宇帝征战四方,人皆轻视之,不料藏锋多年,名剑拂尘方有惊世之姿,功高足矣震主,靖宇帝登位之时,又以战伤休养为名远离朝堂,领封诰居于皇城王府,悠游自在,不理政事。靖宇帝故后,也仅是领了个参知政事的虚名,逍遥半生,羡煞旁人。
直至晌午时分,一辆华贵富丽的四驾马车才悠悠地行走在阔朗繁华的御街之上,宝蓝锦缎的车身折射出淡淡的光晕,乌木车椽,四角饰玉坠流苏,随风摇摇,引得众人一阵侧目,带着惊奇探究的目光引颈而望。众所周知,此乃祈王车驾,祈王雅意举世闻名,从不肯轻易出府,今日非大节,祈王出府倒是件趣闻,瞧这方向,竟是要入宫去的。
车驾行至宫门处,稍有停顿,请示了令牌之后依旧放行,祈王年轻时便少有据礼守法的时候,当时只道是年少轻狂,且瑜王爱子,便也随他去了,后靖宇帝待弟甚为宽厚,封赏不断,如今这性子是越发改不过来了。
马车一直到了含章宫外方才止步,车中男子抬手掀帘略微倾身而出,锦衣玉带,束发如墨,玉质般的面容俊朗如昔,唯眼角几丝微不可察的细纹透露出他已过不惑的年纪,抬眸望着这巍峨的含章宫,唇角携了丝玩味儿的笑意,小侄子今日罢朝可有些奇怪,独召他来却是何事,也罢,着实有些日子没见过他了。踏上白玉阶,入了帝宫前殿,也不必人通传,径自走到了寝殿之外,并无人在此陪侍,已收了随意的心思。
小侄子向来聪明,此番越过宁芊来寻他已是反常,这情形怕是不简单,当即在殿外叩首高声道:“臣请见帝君。”
“皇叔且进来。”避开众人,只因他想知道的只能从祈王处知晓,在长宁公主的威压之下,也唯有祈王才敢告诉他。
沈君翌入内后便坐下了,小侄子面色苍白,神色困顿,竟是一夜未睡么,昱宸向来沉稳有度,遇事从容,何事竟缠他至此,不过小侄子若是不开口,他自是不会问。
“皇叔,”沈昱宸开口唤道,双目直逼叔父,却也难掩眉宇间的疲倦之色,“宸儿有一事请教。”
祈王唇角弯起轻笑,双眸与少年相视,清明非常,“何事?”
沈昱宸默然不语,想知道,又不想知道,别过头轻声道:“有关···大哥的事。”至少他还有过一个哥哥。
倚靠在座上的锦衣男子有笑声溢喉而出,如闻戏言,字句分明,“大哥?什么大哥,今日罢朝召我前来就为了问这么一句无根无果的话,你当真是长进了。”
沈昱宸心中煎熬一夜,倘若之前还有顾虑,当问出口之后就已决定必要问个清楚,此时听他这般推脱,心中那股怨愤又被挑起,“皇叔又是何苦再瞒,我既问出,必是已经知道,皇叔是想我暗自揣测一生心结难解,还是据实相告让我自己分辨,宸儿并非不明事理,我唤他一声大哥就已承认他的存在,而今我只想知道的更多一些,你们也不允许么?”
沈昱宸自懂事以来还是头一次控制不住情绪,苍白的面色也因气息紊乱染上了些许潮红,不悲不喜终只是个笑话,触及自身,他也不过是个悲喜绊心的普通人。
祈王端起茶杯轻呷一口,面色冷静如常,却已不见疏散随意,淡声问道:“哪里听来的。”
“皇叔是想灭口么?”愤怒中的少年似已失去理智,赤红的眼中透出微微的嘲讽之色,如愿地给了他一个名字,“栖鸾。”若非风栖鸾手上的素玥银环来的太过蹊跷,他又怎会牵扯出这么一段往事。
祈王沉默不言,目光涣散情绪难明,忆起旧时往事连他自己也未曾发觉莫名地带了几丝沉重怅惋,“宸儿,此事与你无关,你又何必深究,过去的便算了,靖宇帝的子息自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
“是吗?”苍白的少年反问,“那他呢?纵使你们做的再干净,也掩盖不了真相,沈昱宸这三个字烙在我身上,也时刻提醒我事关父亲另一个儿子不为人知的过往,父亲此举,又将我至于何地?”
“你错了,他从来都不是你父亲的儿子。”记忆中那个七岁的孩子,从来不曾见他笑过,冷酷,果断,固执,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含恨而生,含恨而亡,至死都不肯认一声父亲,血流而尽,仅有的血脉也还了沈氏皇室,自此两清。沈君翌慨然而叹,这段鲜血淋漓的往事他本不愿触碰,更不愿让宸儿知道,他是局外人。祈王暗想,只怕从今往后,他这侄儿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当初大哥把隶属于帝君的‘惋晚’组织交给宸儿,怕是也没有想到这秘辛竟会以这种方式让他知晓。
“你大哥确是个难得一见的少年英才,流落在外多年,你父亲很心疼他,只是宸儿,他不是你父亲的儿子,他从来没有认过沈家的任何一个人,自小长在落樱阁,饱尝世间人情冷暖,怨怪你父亲也是应该的,然而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他的恨竟会那样深,那样重,回皇室,只为寻仇,至死血脉流尽也不肯与沈氏再有任何牵扯,甚至···他的死,也是你父亲一手造成。”
单薄衣裳的少年猛然一退,双目中充斥着不可置信的惊惧之色。他的震惊落在祈王眼中无疑又是另一种悲哀,被掩埋的真相从来都是残忍的,若非伤人至深,又何必去掩埋,“你不该怪他,实则是你父亲欠他,亦无须自责,此事与你无关。”
“无关?”已然无力的少年反问叔父,沙哑的喉间发出一声涩然的苦笑,心肺如割,赤红的眼中溢满了泪水,酸楚无奈,原以为是他欠了自己,到头来却是自己对不住他,他们所有人都对不住他,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怨恨他的名字,又如何能怪父亲把对他的愧疚思念加诸己身。
沈君翌走近两步将侄儿扶稳坐下,少有的严肃神色,“是,与你无关,不要多想,你并非由父亲赐名,而是你母亲清漪皇后所取。”
沈昱宸心下一颤,竟是母亲,未及多想,只听祈王道:“她也只是想为你父亲减些负罪,皇兄只有你一个孩子,他最疼惜的始终是你,你可知,当你还在腹中之时,他已为你备好了‘惋晚’,惋晚的存在,便是我与宁芊都不曾透露分毫,你如何还能任意揣测他不爱你?”
一头乱绪如麻的少年心智已乱,只是叔父最后的话他听进去了,父亲从未把他当作是兄长的延续,如此也罢了。
“昨夜该是一夜未曾合眼,睡一会儿吧。”将侄儿扶至内室躺下,末了,又是一句带笑戏言,带着些许警示意味,“下次若再敢这么随意罢朝,我可就任你姑姑训你,这次么,便罢了。”
“皇叔且慢,”闭目休养的少年忽而出声挽留,匆忙中抓住叔父的衣角,“还有一事。”
祈王复又坐下,“还想知道什么?”
“他···他葬在哪?”
沈君翌微怔,心头千斤重负此刻也化作了虚无,他这个侄儿,一点儿都不像取舍果决的靖宇帝,更不像那个漠然无情的兄长,明是非,亦重情义,这样的昱宸,大哥该是欢喜的。
“长山,你姑姑亲手葬下的,当年也就只有宁芊能多亲近他些。”
“长山。”沈昱宸重复道,瞬时明了,“宸儿知道了,谢过皇叔,皇叔请回。”
长山是座极普通的小山,只因靠着帝陵,平常也就少有人去,姑姑将他葬在那里离父亲也近,落樱阁终究不是他的家,这里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