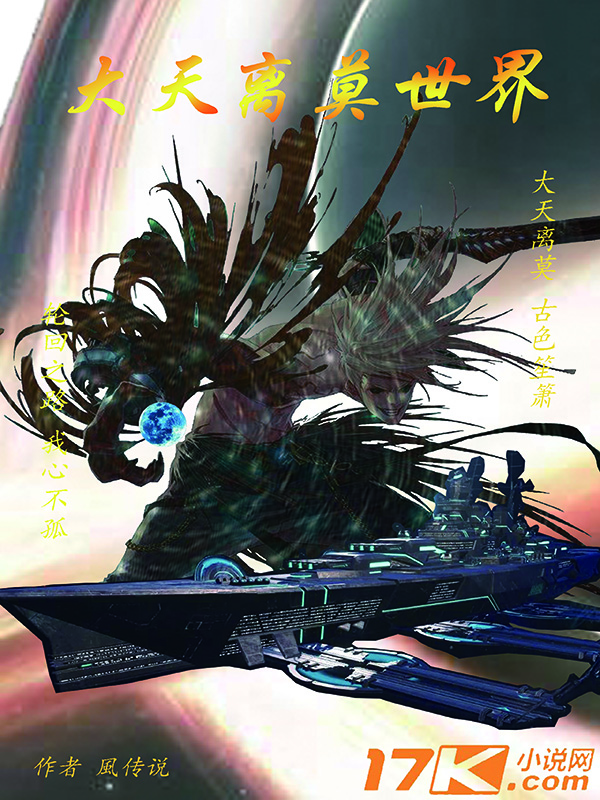三日后,钦差传旨至河双城,改河双城名为颍城。原本驻守城中的将士井然有序,不曾惊扰无辜百姓,唐老将军戎马一生,盯着梁族二十余年,终将这最后一城攻下,自此梁族顾氏俱化作飞沙,了无痕迹。
与此同时,碧水城紧闭了三个月的城门终于再次开启,逃难而来的一些尚未染病的百姓见战事消亡,终究还是不愿背井离乡,收拾行囊,回家去了。亦有不少身虚体弱者,依旧留在碧水城中调养身体。
柳若尘敏锐地觉察到其中不同寻常的地方,眉头一皱,脚下一转就去了女儿的院子,单刀直入问道:“近日碧水城中着实有些变化,莫不是哪位贵人到访?”
屋里燃了炭火,柳清持畏寒,见父亲来了,才起身行礼,点头道:“不错,是他来了。”
柳若尘证实猜测,一时也没什么好脸色,甩袖而去,“添乱,他想做饵,也不掂量自己够不够格。”
“父亲这是何意?”柳清持连忙追问,只见得父亲一片碧青的衣角消失在门口,忙取了斗篷追上去,碧水城冬日干冷入骨,离开了炭火,顿觉一阵冷意包裹。
柳清持寻路而去,长廊曲折,终踏上青石小径,绿竹猗猗,愈加苍翠。柳清持入了内室,顿觉一阵暖意盈怀,解下斗篷,望着檀木小几前饮茶的父亲,青衫隽骨,稳如苍松。自觉的在父亲对面坐下。
柳若尘斜睨她一眼,罢了,女儿是自己的,断不能受屈,抬手将一杯热茶送到她身前,“这般沉不住气,为父教了你十三年,算是白教了。”
“多谢父亲。”柳清持捧起茶杯轻啜一口,暖意游遍周身,驱散了寒气,父亲没有赶她出去,是打算告诉她了。
柳若尘道:“当年梁国亡后,太子顾慎尧只身入都城为质,这也是个难得的人物,可惜晚生了几年,没能跟靖宇帝争上一争,否则这天下未必就全姓沈。”
柳清持闻言不由得一惊,父亲从不夸大其词,这顾太子甘愿降国,不伤一兵一卒,仅这份心性,也非常人所有。
“顾慎尧在都城三年,与沈宁芊,国师风渊相交莫逆,不料三年后,竟突然死在风渊剑下,个中缘由,无人知晓。”柳若尘缓缓道来,“顾慎尧心悦沈宁芊,亡国之前两度求娶不成,入都城为质却成挚友,这巨大的反差,也怪不得他人想偏。”
“所以,顾恒意在长宁公主。”柳清持心头一凉,如此说来,沈昱宸以身犯险倒真是多此一举。
柳若尘悠悠道:“原本是的,可现在却说不准了,毕竟一个退隐多年监国公主与国君比起来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柳清持闻言眉尖一紧,父亲所言倒是不虚。
“把你身边的暗卫送回去,这段日子就在府中,莫要出去乱跑。”柳若尘适时说道。
柳清持点头应下,回到自己的小院,便唤南羽现身,令其到蘅园去。南羽是一贯的冷漠,亦无态度,听完便回了原本的藏身之地,丝毫不为所动。柳清持明了,南羽只听命于君主,如此看来,还要她再走一趟。
次日,柳清持再访蘅园,宋浩陵亲自出来引她进去,才免了层层盘查。
竹舍中,沈昱宸听罢前尘一笑,“想不到姑姑与梁族竟还有这样的恩怨,浩陵,你且安排,过几日我亲自去接姑姑过来养病。”
“是。”宋浩陵暂且先应下,事关重大,还须从长计议。
说完了前因,柳清持道明来意,“你让南羽留下,不必再跟着我。”
沈昱宸望着她道:“不如先说说你想好的理由。”
“我父亲不喜家里藏着个外人。”
这真是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沈昱宸想了想,道:“若是这样,那你留下吧,倒也无须让南羽再跟着。”
柳清持起身,淡看他一眼,“告辞。”
才转身,尚未走两步,已被沈昱宸困在臂弯中,上方传来清晰的声音,克制着冷静下的不安,“让你单独离开的蠢事干一次就够了,跟岳父抢人,实在是件很让人为难的事。”
“你讲点理,碧水城中戒备森严,岂是那么容易出去的?”柳清持低声规劝。
“国士死而复生,滔天谎言,不也瞒过了天下人?”他丝毫不退让,布衣国士柳若尘,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你多虑了,我父亲从无虚言,他说过不会再阻拦。”清冷的声音也放轻柔了些,旧事翻出来,总是父亲做的不厚道了些。
“公子,此处守卫虽众,却也危机四伏,为了柳姑娘安全着想,还是让她远离是非为妙,再者,敌对当前,藏美人于身侧,对公子和柳姑娘名声皆有损。”宋浩陵取出一枚精雕细刻的香囊,“这是一味特制的追踪香,柳姑娘佩在身上,不管身在何处,皆有办法能寻得踪迹。”
柳清持默默接过,“我不取下就是了。”收好那精致的香囊,辞别回府。
沈昱宸这才道:“你倒是准备的齐全。”那银纹镂空香囊一看就是特意做的,一般人哪有这样的对待。
宋浩陵一针见血地指出:“概因公子见了柳姑娘就常常做出一些任性之举,臣不得不想法子解决的公子的后顾之忧。”
沈昱宸一笑了之,转身步入内室去了。
不消多久,便有小厮自蘅园中出来,绕了半个城,才到沈大公子的住处,递了拜帖。好一会儿,才由管家亲自送出府来,拿着回帖才慢悠悠地回去了。
府内,沈云岫扫了一眼拜帖,十月二十八,还有三日,顺手将帖子放置在了书案上。思索再三,还是去了阮和的屋外,抬手轻叩了门。
“公子?”阮和眸中闪过一丝讶色,沈云岫重礼法,自两人定下婚盟之后,极少踏足她的屋子,成婚之前,亦不让她再贴身照顾,唯恐被人传了不尊重,堕了她的名声。
沈云岫举步踏入,微笑道:“这天气越发冷了,我近日频频想起从前家里的梅蕊清来,还需你这双巧手为我煮一壶来。”
阮和微微蹙眉,“公子,梅花尚未开,还须得等上些时日。”
梅蕊清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从前祈王府梅园赋雪乃是盛景,于是便将梅花摘下数朵,混着雪水煮茶,沾染了梅香,别有一番清醇之味。
“想念的紧,不想等了,我听说城外有座庵堂依山而建,这梅花每年都开的早,算来也就这几日了,阮和,可否为我走一趟?”沈云岫执起伊人手,笑容温浅,目光里尽是温柔暖意。
掌心传来恰到好处的温度,也解不开她的眉心结,阮和抬头望着如玉公子,柔声道:“许是变故将生,公子是想支开我?”
沈云岫一笑,道她多心,“莫要多虑,什么变故,同你又无半点相关,我不过是想茶了,如此而已。”
阮和低下头,双手十指紧绞在一起,好一会儿才低声道:“公子让我走,我便走。”
语诉沉沉,满心失落。
沈云岫见她如此,心中蓦地一疼,忍不住将她轻拥入怀,“这般难过做甚,五天就回来了。”
“阮和不想再离开公子。”她敛眉低诉,那一年也是他亲手送她离开,入宫六年,未得一面。
“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再将你送走。”沈云岫低头吻上她的眉心,眼角微润,“待过了年,挑一个吉日,我们便成亲。”
他这一生恭谨谦顺,不负君主,无愧亲友,唯独亏欠阮和良多。知冷暖,明心意,解烦忧,何其有幸,得此一生心。
阮和浑身一颤,神色似喜似悲,双目中含着薄泪,仿佛不敢相信,望着沈云岫郑重的神色,才抹去眼角沁出的泪珠儿,“嗯。”
“公子,阮和有一事相求。”她有沈云岫庇护,自当无恙,可有一人,却不能不管。
沈云岫温声道:“你同我何需客气?”虽止了泪,可她眉间忧色却未有半分退去。
“请公子救下闻悦姐姐。”她一字一句认真道,神色无比郑重,“她真心待你,三番几次救你性命,请公子尽力保下闻悦姐姐。”
“闻悦。”沈云岫低声呢喃,提起闻悦,心情颇为复杂,闻悦在他身边多年,他自是不愿见她身陨,可人犯了错,总是要承担后果的,其它任何事都可原谅,唯独卫小蕤无辜一命,无法挽救,纵然此时留下,戴罪之身,又如何能在卫大人那里讨得一命?
“请公子救下闻悦姐姐,”见他久久不言,似是无动于衷,阮和颇为急切,终于忍不住道出从未与人说起过的真相,“她是我的堂姐,阮和仅有阿姐一个亲人。”
“嗯,什么?”沈云岫的思绪被她这句话惊醒,甚觉奇怪,“你与闻悦从未有过交集,怎会是姐妹?”
闻悦虽出身王府,却不是从祈王府出去的,而是从他的祖父瑜王爷府上出去。阮和却是自幼长在祈王府,是母亲一个侍女的女儿。
阮和娓娓道来:“我的母亲并非侍女,她是梁国豫侯阮耒的妹妹,自幼体弱,养在深闺,无人识得,顾王妃当年出嫁,母亲扮作侍女,是为陪伴王妃。闻悦姐姐是侯门贵女,她是彧侯的幺女。当年梁国亡后,顾太子杀了好些旧臣,其中就有彧侯,后来几经辗转,锦璇姑姑将阿姐带入了瑜王府。”
这些秘辛是锦璇姑姑告诉她的,她自小便知道了,藏在心中多年,如今才得以倾吐。她随了母姓,锦璇姑姑格外照顾她,祈王府中陪伴沈云岫从未受过伤害,深宫六年亦是安稳。她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亲人正在阴谋诡计的漩涡里苦苦挣扎求生,而她却在都城的同一片天空下安稳度日,连看那人一眼,同阿姐说一句话都是奢望。
沈云岫大为惊异,心中似有洪波卷起,阮和与闻悦都是他身边的人,却从不知这两人竟是血亲。思及此,不免慨叹,锦璇真是将阮和护的滴水不漏。
“公子……”阮和声细如风,尚浮动一丝焦虑,眼底是殷切期盼之意。
沈云岫沉吟道:“我尽力。”
“多谢公子。”阮和秀眉渐展,笑如轻絮落水,荡开一层浅漪,微湿了眼角,染了红痕。她深知闻悦身犯诸多重罪,必得严惩,纵是公子,怕也保不住阿姐性命。她不过是想让公子也为阿姐做些事情,看到心上人为自己忙碌奔波,阿姐总归是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