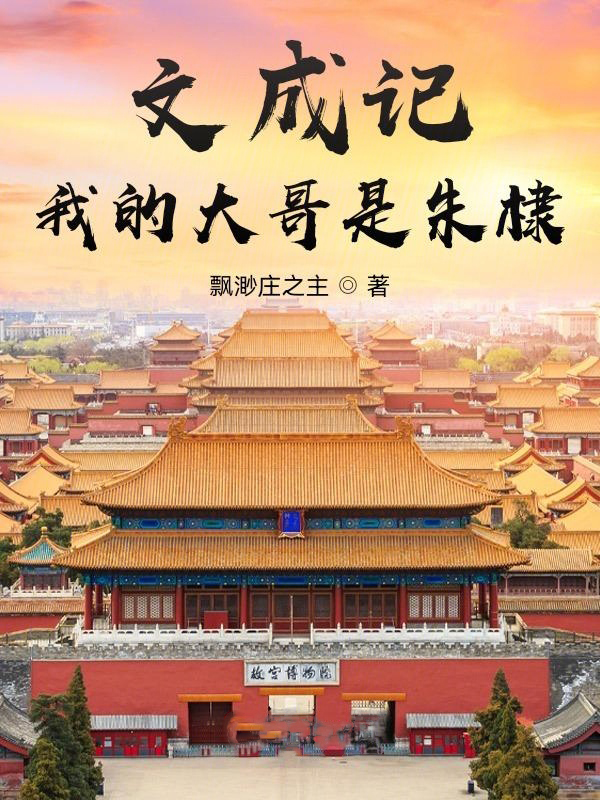身为王者,尼布甲尼撒果然是一个会将想法立即付施于行动的人。从里斯浦府邸出来的当天下午他就领着里斯浦直奔格齐伍布的宅邸“登门造访”,虽然口头上是持着要征询这位建设大臣对城内设施的意见,可是待话题摆上酒桌,三人手中的酒杯频频见底之后。他和里斯浦就开始一红一白的唱和着,分明说着与泥土石板相关,两人却总是将话题有意无意的绕进“袍服”,以此试探对方的口风,也不直接把话挑明,只是暗中作着细微的观察。
而格齐伍布到底是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下为官多年,不愧练就了一颗比铁块还要硬实的心脏,接连几杯周旋下来,他既能从容应对尼布甲尼撒和里斯浦的百般刁难,也能保持沉着与他们继续把酒言欢。一杯又一杯的烈酒灼喉,在那些热辣液体的推敲作用下,通红的脸色和醉意朦胧的眼神替他掩饰得恰到好处,未露出任何马脚。面临如此的尼布甲尼撒也不着急,他轻轻搁下酒杯,简单交待了几句关于塔庙的进度,便撂着笑,起身离开了宅邸。
自那晚以后,就这样平安无事的一晃整整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清晨,和往常一样,格齐伍布趁着天色朦亮之际就准备妥当,动身前往塔庙的施工现场。可就在两名仆役刚为他拉开门闩的刹那,从外面突然闯入一群穿甲的侍卫,将一行人团团围住……
当日,等把与格齐伍布一同犯案的官僚全部擒获,天色差不多也完全亮透了。里斯浦对部下大致作下一些交待以后,便打算回宫向尼布甲尼撒报备此事。
“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拿回去重做。”空寂森静的走廊上,远远就能听见从书房内传出尼布甲尼撒震天的咆哮。
“……是……是……”于书房正中央的地板上,两个身穿官袍的官员各带着两名随从弓背撅臀,战战兢兢的伏地作跪。而现在答话的是靠左的一个绿袍官员,只见他额头紧紧贴在冰凉的地面上,颤抖断续的声音就像是被人用手指拈住了喉咙。“…….可,可是……陛下,这……这是宫……宫中历来,历来的传……传统……”
“传统?”拘着耐心听完绿衣官员“冗长”的辩辞。尼布甲尼撒冷傲抬眼,沉下的眸子无不向外界逸出更加危险的讯息。“是谁给你们规定的这种传统?”
“回…...回陛下……”此时,尼布甲尼撒冰冷的声线仿佛圈化成了一把沉重的枷锁架在绿袍官的脖颈上,卡制着他的喉结。
“回禀陛下。”大概是担心身旁绿袍官结结巴巴,半天这样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会恶化尼布甲尼撒的情绪。跪在右侧的栗色袍官终于大胆的直起身板接过了话头,听他的声音要比绿袍官的年纪小不少,却显得镇定许多。
“这并非由谁定下,只是早在古时的巴比伦王室,但凡国王娶妃,国王和妃嫔就必须穿上这种在衣料上镶嵌着珠石的长袍行完仪式。曾经的米梯斯王后殿下及后来的每一位嫔妃都是如此。”
“是吗?”似乎只是唇齿间一次的无意磕碰,之后尼布甲尼撒便再不动声色的侧身拿起一旁托盘里的紫色袍子捏在手中。眼神辗转复杂的盯着袍子上那一颗颗打磨圆滑的宝石,五指关节渐渐发白。“既然你能做到对巴比伦忠心耿耿,那本王就随了你的心愿……”
“让你们荣耀一生的卡加涅奇家族统统去伺候列位先王,如何?”语气猝然拔高,脸色也随之阴云骤集。尼布甲尼撒毅然高举手中的紫袍,再狠狠摔进托盘。
“……啊……”听见尼布甲尼撒决绝的发落,绿袍官被吓得失声惊叫,猛然抬头惶恐的看一眼前方居高临下的王者,再转过脑袋焦急无奈的看着栗色袍官。张口哆嗦着两片微厚的唇瓣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伊卡,你放肆。居然敢在当今执政陛下的面前出言不逊,还不赶快叩头谢罪。”已经站在门外很久的里斯浦看见房内这一幕,唯恐尼布甲尼撒真的会一怒之下将这二人送上断头台,便假装威吓怒斥以缓解气氛。
“臣无意顶撞陛下,不慎之处请陛下宽饶。”看着身旁面色锡白的父亲,栗色官袍,被里斯浦唤名“伊卡”的青年又重新俯身匍在了地上。尚且年轻,涉世未深的他原本只是想为父亲向陛下解释清楚,却没想到弄巧成拙。不过更让他感觉奇怪的反倒是陛下对这件事的态度,纳过不少后妃的陛下从未像今天这样计较过,往往都是直接交给他们的作坊,断不过问。
“犬儿无知,大言不惭冒犯了陛下钦定的规矩,请陛下恕罪责罚……请陛下恕罪……”全身上下早已被尼布甲尼撒的话吓得如同挑筋抽髓一般,绿袍官欠着一身软咧咧的骨头趴在地上一个一个的磕着响头。
本来就无意大开杀戒的尼布甲尼撒也不过是为了一泄内心的烦闷才放此狠话,加之又有里斯浦站出来为他们求情,他也就顺着这道台阶软下了态度。“按照本王的意思拿回去重做。大致的图形都不许变,或绣、或织……不管你们怎么弄,只要不是镶嵌这些宝石,越轻越好。另外就是冠冕,也必须换成发带的形式,依旧要用古拉花的图样,可以简单镶饰一些较轻的蓝色珠石在上面。”
“是,是……老臣这就回去照办……”刚领完命,绿袍官就迫不及待的直膝起身,拖着自己的儿子和其他四名随从快快闪离了书房,生怕脚下稍慢一步就会成为尼布甲尼撒改变主意的陪葬品。
“其实陛下无需动怒,卡加涅奇家族确实从很早以前就忠于侍奉巴比伦王室至今,对于王公贵族来说,这一族的手艺绝对堪称巴比伦最优秀的裁衣师。”目送着卡加涅奇父子走出书房,里斯浦才放心的继续说道。“陛下做这么多,应该也只是想要给予塞米拉米斯一个最风光的仪式吧?”
“里斯浦,你很清楚我生气的真正原因。依塞米拉米斯如今这副身体,我不希望她在成为我的王妃的同时,还要忍受这样一件衣服带给她的痛苦。”视线极不耐烦的扫过散乱在托盘里外的镶珠紫袍,尼布甲尼撒对自门外踱步走进的里斯浦说道。
脑中触景晃过上次看见的那张血色尽失的脸庞,内心不由得再次纠结一团。他甚至怀疑,那副过分纤弱柔细的身躯现在能否承受一件最为单薄的短袍?就更别说他面前这件满载着各种宝石重量的卡吾那凯斯了。
“相较于以前的所作所为,颠覆一个传统算得了什么?”尼布甲尼撒长吁,记忆不禁回到了多年前烧毁尼尼微的那次,凌厉的眼神也逐次变得柔和。“我不需要她穿什么华丽的衣饰装扮自己,只要她能永远陪在我的身边,健健康康,不必承受任何负担的陪在我的身边,她就便是这个世上最美丽的王妃。”
“我仅需让世人永远记住她……是我尼布甲尼撒二世此生唯一的王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