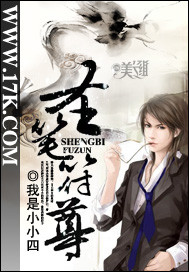“还在为昨天下午的事心烦吗?”耶利米刚走进房间,就看见塞米拉米斯无精打采的趴在床头的窗台上,歪着脑袋盯着窗外逸静的景致,意兴阑珊。
“昨天?”闻声,塞米拉米斯眉目不悦的回过头,为身后那支与她房间沉溺的氛围格格不入的轻快声音。
冬日的阳光总是会为冷冽的空气渗进些微暖意,即使窗外有着如此明媚红润的光色,却也始终照不透那张精致素净的脸蛋儿,它依旧和昨天一样毫无起色,苍白得令人心疼。
“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塞米拉米斯略带戏谑的口吻调侃道,只是一眼,她便将视线退了回去,没有心情再施与理会。
“只要是我不想知道的,就会装作不知道。”听出她话中的弦外之音,耶利米毫不在意的一笑了之,仍是走了过去,坐在她的床沿边上。“上次在我的激将下,他都没有松口承认喜欢你。没想到昨天只是不忍看着你受苦,他就什么都说了。”
“你说什么?”塞米拉米斯再一次被耶利米的话吸引了注意力,她转身看着他,淡漠的眼神被诧异转浓。
“你放心,里斯浦自有他的分寸,否则早就会不顾一切的带你远走高飞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一直就在为了你和尼布甲尼撒努力克抑自己,所谓的身份责任都不过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他只是舍不得让你离开尼布甲尼撒的身边。尽管这与他真正的心意南辕北辙,他也要将你留在喜欢的人身边。”耶利米将自己熟知的里斯浦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
“这次你错了,我并没有在想昨天的事,只是担心他出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塞米拉米斯借故望向窗外,欲掩饰眼中的慌乱。
“‘假设终究不能成为现实,仅凭想象,里斯浦也不会是那位巴比伦王’,直到刚才我进门之前,你都一直在这样提醒自己,对不对?”耶利米故意忽略她说了些什么,此时的他就像一个读心术者,能从她失落的脸上轻易看进她的心底。
“我没有。”塞米拉米斯愠怒,却又底气不足的细声反驳。她轻轻将背脊倚靠在身后的窗壁上,蜷缩起腿,将头埋进两膝之间。
“如果不是‘魂卜’,可能我至今都不会察觉他当初拒绝陛下赐婚的理由。我承认,昨天的确有那么一瞬间,里斯浦的言行让我错以为,他就是陛下站在我的面前,因为实在太不像他了,不像我平时认识的里斯浦。”大概是将头埋于膝间的缘故,塞米拉米斯的声音听上去透着轻微的鼻音。
“当听见他说要把我送到那位陛下身边时,我很害怕……忍不住会很害怕。”音量随着每一个字符慢慢变小,塞米拉米斯又收了收细窄的双肩,将面前的双腿紧紧环抱。仿佛仅是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就能为她驱散满心的恐惧。
“你相信他会那么做吗?”看着塞米拉米斯仍然不住微颤的双肩,耶利米问道。
“耶利米。”
“恩?”
“你恨我吗?”塞米拉米斯抬起头颅,睁着那双严肃异常的棕色美瞳。
“恨?我为什么要恨殿下?”耶利米错愕反问,转而又失声轻笑,为她的莫名其妙。
“因为之前我拒绝了你的请求。”她指的是上次在花园里要她为犹太王求情一事。
“哦,那件事啊。”经她这么一提,耶利米的眼神反倒变得不自然起来。“不怪殿下,是我自己太强人所难。”
“是吗?”塞米拉米斯神情落寞的轻哼道,如同宝石一般韵色饱满的明眸此时也宛若匿于黄土厚坯之下,黯然垂色。她把下颌磕在膝盖上,松开圈住小腿的双臂,将两只小巧的手掌搁在铺着软和的短绒毛毯上,十指在上面来回抚摸着。
“你应该恨我的,就像他们恨我一样。尼布甲尼撒说过,我已经不再拥有曾经塞米拉米斯的身份,只不过是他从纳西比纳的战场上捡回来的,一个连最低贱的身份都不配拥有的奴隶……还有叛徒。”她自顾的说着,低眉凝视着被自己的手掌压扁的一小片绒毛。
看着意志如此颓丧的塞米拉米斯,耶利米的心情也没由来的变得惆怅。或许他应该如实告诉她的,把自己所知道的,尼布甲尼撒对她的真心实意统统说出来,只是这样一来,他便丢失了日后营救陛下的唯一筹码。虽然这种做法并不磊落,也够卑鄙,但是只要尼布甲尼撒还没有将她纳入王宫,他就仍有机会。
“殿下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能够领军三十万吗?”耶利米表面如是问道,内心却有着另外一番想法。他对不起塞米拉米斯,为自己的欺瞒。可是只要她能答应自己的“求情”之请,他也断然不会出此下策。如此,她曾经的居所“卡斯奇兰”能够在巴比伦得以重建,就权当做是他的赎罪吧。
他实在无意伤害她,所以他正力所能及的去弥补。在尼布甲尼撒面前提及尼尼微的“卡斯奇兰”,一方面确实是为了不让她掉进后宫争宠的泥沼深潭,还有一方面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为了那场刻在犹太人命运中的浩劫拖延时间。
“因为我所拥有的预知能力可以确保百战百胜,只有打完胜仗,他们才能被父王加官进爵,享受永生不尽的荣华富贵。”塞米拉米斯抬眼望着他,一副冷冰冰的腔调。
“不是的。”耶利米摇头,否定掉她的说法。“他们愿意归入殿下麾下,我想一定是因为被殿下吸引,是你的笑容坚定了他们取胜的决心。难道殿下没发觉吗?你的笑脸当比这世间最美丽的一束阳光。”
这不是谄媚的讨好奉承,是他的真心话。回首自己于世的这六十载,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能够心无城府的叫出他的名字,不在乎他曾经拥有多么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如今也不计较他是一个沦落到此的逃犯,只是随心所欲,单纯的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而已。
然而塞米拉米斯在听完他的这番赞美以后,心中竟无半点感动和欣喜,她只是两眼怔怔的盯着他的脸,尔后幽幽吐道。“他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他说我没有资格站在他的面前。但是我想,若我不是弋兹帕特的塞米拉米斯,便可以任性的赖着他,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留在他的身边,即使会被厌恶,没有身份也没关系,哪怕一辈子都不被允许微笑。”
正因为她是那个拥有千年诅咒的弋兹帕特族族长,所以她想要和他在一起的勇气都被逐步否决了。只能站在触摸不到他的地方说出一句“我喜欢你”,却永远都不可能抵达离他最近的距离。
“这个给你。”突然,耶利米伸出右手,将手心摊在塞米拉米斯的眼前。
“什么?”塞米拉米斯茫然的看着他手心里躺着一个和手镯差不多大小,但外形奇怪的环状物。
“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是刚才去过庭院后面的古拉花园,便捡了掉落在地上的花藤随手编织的。”看着手中自己的“杰作”,耶利米依此解释道,“想到你对古拉花情有独钟,所以就带过来了。”
听他这么一说,塞米拉米斯原本冷淡的表情顿时缓和不少,嘴角还泛出了淡淡笑意。她伸手拿过花藤编环掂在食指上,饶有兴致的细细观察着,却恰好看见了站在门边的尼布甲尼撒。
“陛下……”瞬时所有的五官又趋于僵硬,藤环也从指尖掉落。她已经不清楚这个高贵的称谓是如何蹦出唇齿之间,只知道身体动弹不得,不听使唤,大脑一片空白,忘记了该有的礼数。这一切的变化,都只因赫然出现在她面前,如神一般降临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