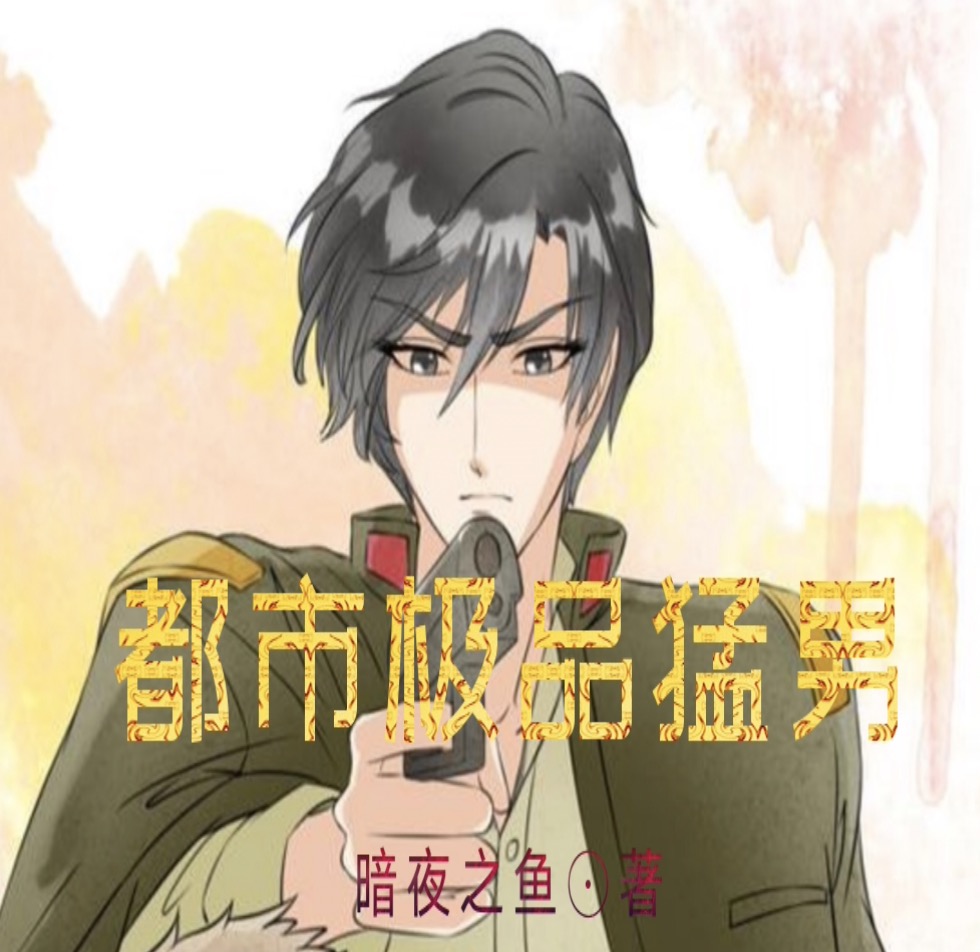她挣扎着朝我扑过来,“孟婆,等我,等我!”
走了几步,她一只手掉了下来,接着,整条胳膊摔在地上,她怪笑了几声,踉跄着向前。
“扑嗵!”又一条腿掉在地上,但她并没有停下来,趴在地上一步一步的爬着,那笑声,既痛苦,又愉悦,好似要完成一件千年的壮举。
“不要过来!”我喝道,“再过来,我不客气了!”我幻出一个寒冰结界罩住她,她在结界里挣扎,呼喊,“求求你,放我出去,带我走,带我离开这里,我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为了能离开这里,我等你等了好多年,好多年!求求你,带我走吧!”
“你是谁?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我?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这里是哪里?”我连着问了一串了为什么,我真的不记得自己怎么会来这里的。而且,我对这里毫无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她在结界里匍匐着,用仅存的一只脚踢打结界,“咔嚓!”这条腿又跌落下来,在结界里抽搐了几下,她上半身蠕动着爬过去,把腿抱在怀里,“想知道我是谁是吗?问问敖睚眦那个怪物不就知道了?”她又大声怪笑,手开始拍打结界,“快点放我出去吧!我要离开这里!要不就永远也离不开这里了!”
我大吃一惊,问道:“敖睚眦?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为什么你还被关在这里?”
“哈哈!死了?你说敖睚眦死了?他死了,为什么我们还会被关在这里?”她单手抱着断腿,一遍一遍的抚摸着,宛如是一件珍爱的玩物,“断了……断了,还是断了!”
我看她就是一只怪物,前面的人群依然拥挤不堪,他们到底在围观什么?
我正要绕过结界,何必为一个奇怪的女人纠结?这时,她却哭了,“我的腿……我的大长腿……就这么没了!太浪费了!”说完,一直默默注视着断腿,突然,喜笑颜开,用长舌头舔了舔断腿,然后,一口咬了下去,大腿被撕掉巴掌大一块,连皮带肉一半在她嘴里,一半吊到下巴上。她咀嚼得津津有味,“真好吃!”她把肉咬断,拿在手里往我面前伸,“孟婆,你也尝尝吧!”
太恶心了!我蹲在地上呕吐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来,“你不要再吃了!”
“不,太美味了!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原来,好东西就长在我身上,我却不知道!孟婆,快放我出去!我要把那只腿、那只手捡回来!我自己的东西,只能我自己吃!”她边吃边喊,血,从她嘴角溢了出来,顺着下巴一滴滴落在结界里。
她生怕浪费了,马上伸出舌头舔得干干净净,又接着吃断腿,不久后,她手里只剩下一条完整的腿骨了。她好像还没有吃饱,东瞅瞅,西望望,口水和着血丝拉得老长老长。
“饿,好饿,还有吃的就好了!”她仔细地望着自己的手,那是一只很漂亮的手,青葱般的手指白白嫩嫩,又细又长,手背稍微有点肉感,却起了四个可爱的小窝,指甲修得尖尖的,上了淡绿的指甲油。
爆笑声如雷,在房子里的四堵墙上撞击着,回旋着,把那微微颤抖的尾音拉得很长很长,未免多了几许悲怆,几许惧怕,几许感伤。是的,人就是这样,长大了之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总是习惯笑。笑,成了所有感情最基本、最常见的表达,变成了交往过程中最好的掩饰。所以,我们都习惯笑了!不仅习惯自己笑,更习惯自己比别人笑得好看。
我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种笑,表面上是开怀的,内心却充满恐怖和无奈,甚至是绝望。可我真的想知道他们因什么而笑?我也想体验一下,自己会不会像他们一样笑?可是,这堆人堵得固若金汤,让我无隙可乘。
“大家听好了,”结界里的女人大喊着,“孟婆来了,我们等了很久的孟婆来了!”
什么?他们聚在这里只是为了等我?
结果,她的喊声淹没在大家的哄笑里,她没有放弃,不停的喊着:“孟婆来了!大家快安静一下!孟婆来了!能救我们命的孟婆来了……”
笑声如同即将退却的潮水,一浪连着一浪远去,呼啸声逐渐平息了,屋子里静得可怕!所有的人转过头来,神色各异,有惊喜,有企盼,有哀怨,有诧异,有崇拜,也有不屑。
“孟婆?”
“孟婆!”
“真的是孟婆?”
“怎么可能是孟婆?”
我把结界撤掉,女人像菜虫般蠕动,她依旧在怪笑,“怎么,你们不相信?她就是孟婆!”
“你怎么知道她是孟婆?”一个男人恶狠狠地问道。
“我见过她!她就是他画里的那个女人!”女人用牙床啃着自己的双唇。
男人阴森森朝我走来,每走一步,房子颤抖一下。我并不害怕,不管在哪里出现危险,陆判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
他对着我摇摇脖子,发出吱吱咔咔的声响,充满戾气的眼神,似乎要把我吞没,“说,你真的是孟婆?”
我仰起脸,冷冷地答道:“对,我就是孟婆!”
他“扑通”一声跪下,匍在地上高喊:“求孟婆救救我们吧!”话刚说完,整个人像只打烂的花瓶,裂成数片。
其他的人好似木头棒子杵在原地,纹丝不动,齐声高喊:“求孟婆救救我们吧!”
我不解的问:“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我救你们?”
“我们?我们是一帮等你的人。至于为什么要等你,你问问他便知道了!”他指指扎堆的人群,伸出的手断在地上。
大家见状,纷纷原地侧身,我从中间露出的缝隙朝里望去,好大的一个鱼缸,却被他们遮挡了,无法看清鱼缸里的东西。
“让我过去!”我对挡住我的男人说道。
“对不起,我也想让你过去,可我动不了,我们都动不了,只要我转个身,骨头便会像她一样散架,再也接不回来了。”他看看地上的女人。
“那我没弄清怎么回事,如何帮你们?”我一时间烦躁不安起来,大概是因为始终没看到令他们狂笑的东西吧?
“难道你看不见前面的鱼缸吗?”男人的语气十分不悦。
说了等于没说,我恼了,“你们挡得严严实实的,叫我怎么看得到?”
不是求我帮你们吗?什么态度?气得我一甩广袖,“再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可要走了。”平川一干魅正等着我一道回地府,干嘛要跟一帮稀奇古怪的人消磨时间?
“孟婆,不要走,我们这就给你腾地方!“背后焦急万分的呼喊,让我忍不住回头,身后七八个年轻男女碎了一地,手、脚还在剧烈的抽搐,光秃秃的躯干蛆虫般的蠕动。
我无从得知他们是否痛楚,因为,他们笑得那样灿烂,“孟婆,你不要担心我们,你是上天派来解救我们的,只要你愿意,我们都会变成正常的人,过回正常的生活。”
不不不,我敢用项上魅头担保,我明明来自地狱,与上天完全不同时区,所以,把希望寄托
在我身上,就大错特错了。“各位,我真的赶时间,人间的事,不是我管得了的,很抱歉,我先走了!”
“不要!中间两排男女齐刷刷跪下,身体的零部件散得满地都是,“害我们的,就是那鱼缸里的东西,世界上只有你能救得了我们。”
“我?”那个男人的话,让我受宠若惊,我缓缓向鱼缸飘去,好大的鱼缸,竟然像大海一样广阔无边,
淡蓝的水浅浪轻涌,在水面折起一道道奇形怪状的褶子,似叠皱的纸张。偶尔一群群大小不一的鱼惊惶失措的游过,有人在捕捞它们吗?
突然,淡蓝色的水里翻起一片鲜红,艳得如满树的东方朱砂。水面瞬间波澜壮阔,翻滚的水花相互拍打出一串串的白沫。
一只红得闪闪发光的怪物由远及近,浑圆的长长的身体霸气十足的扭动,巨大如机翼的尾巴神气傲慢的扑打水面,把深不可测的鱼缸搅得天翻地覆。头上的两只赤红的小角,以及下巴上两条如红丝带的长须,使它看起来多了几分娇萌。
我趴在鱼缸上,等它游过来与我四目相对时,我对它摇摇手,打个招呼。它似乎对我有好感,逐渐平静下来,水面也恢复了平静。
我正揣测着它是否能听懂人话,它突然张开了血盆大口……
“啊!”我尖叫出来。
“岑儿,岑儿,你做恶梦了?”夫君问道。
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各色落花已将我和夫君掩盖得厚厚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