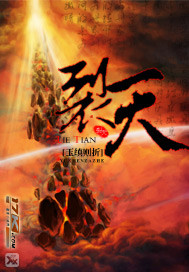说话,仓颉为寻求天地二皇早日为民除害,不辞千辛万苦来到了神圣仙山幽云洞,
当他进洞一看,洞内却空空如也,不禁令他大失所望。
一时间使他极度悲哀与失落,竟一下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有人告知他天皇伏羲氏、人皇神农氏、地皇燧人氏早在多年前就去了天庭,做了上仙,如今洞府里只剩下几尊塑像。
因此他十分沮丧,只好原路返回。
不过,在回来的路上却听说:黄河彼岸有个熊国部落,出了个轩辕黄帝,此人非常了得,并深受民众爱戴。
于是他想,若去求助轩辕黄帝兴许能制服二怪。
主意拿定,他便匆匆忙忙赶回住处,想与隶首再次商议对策。不提。
再说,隶首自从那日送走了仓颉之后,他生怕蚩尤发觉仓颉出走之事,整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可谓是度日如年。
一想到仓颉对他所述惨状,就浑身毛骨悚然,脑海里时常会迷迷糊糊地闪现出象怪和大青琵琶精的模样,二精怪正将一具血淋淋的死尸大口大口地分餐,那黄黄的皮肉、黑黑的毛发、白白的骨骼、红红的鲜血……
不时的在他眼前横飞、翻转,使他常常从梦中惊呓,并被那惨状惊醒,醒来后浑身上下俱是潮漉漉的冷汗。
白天,他神不守舍,无精打采,心里念念叨叨,总盼望着仓颉早日归来,好解心中之忧。
可他心里却明白一点,如果这样长期下去,自己恐怕支撑不了多久,趁着蚩尤尚未觉察,不如暂躲一时。
他不敢见到蚩尤,经常推托有病或者有事,他独自一人躲在僻静之处不与他人交谈,时时想寻机溜之大吉。
说来也怪,他的想法,就像被蚩尤猜到一般,几次要逃脱了却又被蚩尤手下撞个正着。
他越是如此心里越是害怕,如惊弓之鸟,似脱钓之鱼。
有时他在心里默默祷告:苍天啊,快来救救我吧!
可是,事与愿违,世事有时确实如此,越是害怕发生的事情,它偏偏就要发生。
仓颉出走之事,终究被蚩尤察觉到了,并派出了许多武士四处寻找于他。
那天,隶首无心思研究数学,他屈指算来仓颉已走多日,按路程计算,这两天应该返回了,但不知道此番是凶是吉,他心里着实是忐忑不安。
他想出去迎迎仓颉,并可及时告知于他,这几天武士们正在寻找抓他。
当隶首刚一出门,竟被蚩尤的武士拦住,其中一名武士说道:“隶首先生,酋长有请。”
隶首顿感汗毛倒竖,知道情况不妙,再想推托,却也无济于事,自己身单力薄又怎能斗得过这些彪悍武士?
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随武士们一同去面见蚩尤。
他暗暗下定决心:事已至此,走一步看一步,看二怪能奈我何?
想到此,他心中反而镇静了许多。
于是,他仰首阔步,由众武士们“护驾”向蚩尤住处走去。
再说,自从那天蚩尤和夫人察觉有人到过白骨洞,知道他们害人的事已经败露,这人究竟是谁?
必须查找出这位知情的人,才能使二怪安心。
他们暗地里寻找与洞内气味相同之人,二怪深知此事一旦传出,非但无人再敢在东夷居住,还会招来杀身之祸。
这几天二怪生怕事情闹大,除了下力寻找那位知情之人,还将每日食一人改为二日食一人,而且他们只在远方觅食,周围不曾少了一人。
人们自然不会注意这些,只管耕食织捕,整日忙忙碌碌。
这天,大青琵琶精忽觉身体不适,腹内空虚灼热,自知体内精血不足。
每当此状发作,非得食人不可,可是,蚩尤正为找不到那位知情之人而烦恼,常常发一通无名火。
大青琵琶精忍住不适对蚩尤言道:“我们几乎查遍周围众人,却仍未发现此人,如今只有一人值得怀疑。”
蚩尤问道:“是谁?”
大青琵琶精答道:“自从那天起,一直未曾见到过仓颉,所以此人必是仓颉。”
大青琵琶精一语提醒,使蚩尤恍然大悟,他大声叫道:“着哇!我怎的把仓颉忘了?对,此种味道正是仓颉。仓颉何在?”
大青琵琶精道:“还不快将仓颉拿来。”
蚩尤这才冲门外武士们喊道:“你们速叫仓颉前来见我!”
武士得令直奔仓颉住处,不多时,武士们回来禀报道:“启报酋长,仓颉不在住处,我们四处打听他的去向,众人全都不知道,我们只好回来禀报。”
蚩尤和大青琵琶精闻报,更加坚信这位知情之人定是仓颉。
那么仓颉究竟身在何处,他们当然不知。
蚩尤向武士们下令说道:“凡见到仓颉者,立刻将其带来见我,他若是不从,可以当即处死。”
命令传下,武士们整日到处寻找仓颉踪迹。
夜间,蚩尤与妖妇在白骨洞食完人后,那妖精便又想起了仓颉,只要仓颉一天找不到,他们就一天不得安心。
大青琵琶精想了想恶狠狠地对蚩尤说道:“听说仓颉一直与隶首十分亲近,仓颉隐藏何处,隶首想必知道,不如明日将隶首抓到一问便知,他若是不肯讲出仓颉去处,可严刑拷问,到时候也可做我俩之餐,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你道如何?”
象怪蚩尤闻听此言,顿时一阵哈哈大笑,言道:“还是夫人高见,就依此言。”
第二天,隶首正想去迎接仓颉,以免他落入蚩尤之手。
可没走出多远却被武士们拦住并押到了蚩尤住处。
沿街民众得知隶首被抓,许多人跟随至门口聚集观看。
当然,人们也少不了交头接耳纷纷议论与揣测:隶首因何被抓?他所犯何罪?这等能人实在太可惜了……好一番乱乱哄哄。
起初,隶首心中也着实恐慌,他被武士们带进门来,只见二位精怪端坐在上方面带怒色,两边站着俱是面目狰狞的武士。
隶首见状,不由得心里一沉,闪念间暗自说道:今日来得,恐难去得;不过,二精怪若无真凭实据或理由,量他们也不可轻易处置于我。
想到此,他静了静心情,稳住神态拱手言道:“隶首参见酋长、夫人。”
蚩尤深知隶首能言善辩、智力非凡,自不必与他拐弯抹角,非得来个开门见山、突然袭击,方能使他措不及防。
蚩尤开口问道:“隶首先生,仓颉今在何处?”
蚩尤猛然一问,使隶首先是一愣,方知他与仓颉做的事情已经败露。
可他一想到二精怪害死那么多人,如今自己也被他们抓住,当然也难免一死,反正是一死,倒不如求个痛快,反落个清静,免得整天担惊受怕。
他暗下决心,至于仓颉出走之事,当然他会矢口否认,并宁死不说。
刚才听见蚩尤所问,他瞪大了眼装做奇怪和不解的样子。
他反问道:“酋长不是向来是能掐会算么?仓颉不是始终在你身边么?我不是多日以来身体不适么?今日不是刚刚好了一些,就被武士们叫来见你不是?”
隶首一连几个“不是”直问得蚩尤张口结舌,十分尴尬。
蚩尤暗暗骂道:好你个鼠辈隶首,难怪夫人说你诡计多端、狡诈无比,今日即便你再有鬼才,我也要将你生吃活嚼!
想到此,蚩尤一拍桌案勃然大怒,指着隶首大声喝道:“你与仓颉一向交往甚密,仓颉失踪你却不知?谁会信你?据我所知,你干了非分之事,被仓颉发觉,你怕他告知别人,便杀人灭口将仓颉害死,并抛尸他处,可是,你害仓颉之事又怕被别人察觉,故此你心中难安、神情不定,这几天却一直报病躲藏,惧怕见人。你且道来,是也不是?!”
隶首闻听此言,不禁心里大吃一惊,他万没料到蚩尤竟然会出如此毒招。
他看看门外围观的民众,稍后,稳定住神情,转头对蚩尤笑道:“酋长好会猜测,请问,我害仓颉有谁见到?不过,仓颉因何失踪,想必酋长与夫人自是心知肚明……”
“住口!大胆隶首竟敢在此胡言乱语,来人!将隶首绑了!”蚩尤也没料到隶首之言带有弦外之音。隶首肯定也早就知道他们害人的事了,定是仓颉告知于他。
若不除了二人,将会后患无穷。
大青琵琶精在一旁非常冷静,她看见门外有众多人围观,只怕把隶首逼急了会当众戳穿他俩。
对待这种人只能暗下毒手,何必当众与他计较,免得引出事端。
听到蚩尤吼叫,她急忙起身喝退了武士,笑眯眯对蚩尤说道:“酋长息怒,依我看,似隶首先生这般善良贤能,怎能去干那些害人之事?定是酋长听信了谗言,才如此震怒。”
她一边嘻皮笑脸地说着,一边走下台阶来到隶首跟前,故装慈悲地隶首说道:“酋长言举,请先生不必介意,你可知道,酋长向来器重你与仓颉。这几天不知仓颉去处,又见你报病不来理事,再有人向酋长说三道四,酋长以为你俩真的怀有二心,这才将你请来想当面问个明白,谁知又动了肝火。罢了,罢了,现在事已查明,实属一场误会,请先生内堂闲叙,其他人等全部退下。散了,散了!”
武士们听见夫人吩咐,一同退出门外,又把围观众人全都驱散。
众人不知内情,刚听夫人之言,信以为真,一场虚惊,便随即散去。
情况突然,未等隶首开口,所有人等包括蚩尤手下的武士们早已一哄而散,有谁还听隶首再说什么。
这下隶首着实慌了手脚,他连连叫苦,看来这位大青蝎子精的招术比那象怪更毒,叫你有口难辩。
隶首深知内情已经败露,二精怪怎肯饶他。
当人们纷纷散去之后,庭堂内只剩下隶首和二位精怪。
只见蚩尤自是得意,他大笑一阵后对大青琵琶精言道:“还是夫人智谋超群,能言善变,高见。我看你隶首此时有何话说?请讲,尽管道来。”
大青琵琶精也得意的阴笑着,使隶首直觉得这庭堂内:
冷飕飕凉风刺骨,阴森森寒气袭人。
却说,二位精怪的阴笑,使隶首感到从头到脚如浇冰水一般凉得透彻,他懊悔没能及时当众说穿二怪害人之事。
事已至此,只有与二怪殊死一博。
他壮起胆子冲二怪大声喝道:“尔等害人无数,而今落在你手,要杀要剐快速速动手。”
大青琵琶精止住狂笑,她扭动着腰身慢慢脱去外衣,露出了青青的上身肌肤。
她到了隶首面前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脸颊,冷笑一声,然后阴阳怪气地说道:“隶首先生此话差矣。你乃是我东夷九黎之能士,若是痛痛快快的死了岂不实在惋惜?今日,我恳请酋长将你赏赐予我,我先吸点你的精血补补身子,等抓住仓颉之后,再一同品尝你俩不迟。敢问酋长,你道如何?”
蚩尤又是一阵大笑说道:“夫人所言极是,请夫人尽情享用。”
此刻,隶首身陷囫囵,举目无天,他十分绝望,与其被折辱而死,不如自行了断而亡。
他鼓足力气,猛然把头撞向墙壁。
怎料到,大青琵琶精手疾眼快口吐妖气,隶首的头未触碰到墙壁,便昏昏倒在地上。
这下象怪蚩尤吃惊不小,他见蝎精施展出妖法,连忙说道:“幸亏夫人出手及时,才保得这具活食,否则就不新鲜了。这隶首倒是个刚烈性情。”
那蝎精恶狠狠撇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隶首说道:“想死?没那么容易。抓不住仓颉,管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二怪同声大笑。
这时有武士进来禀道:“启报酋长,在隶首处发现仓颉身影。”
蚩尤传令道:“速将仓颉拿来,他若不从可当场毙命,把他尸身带回便是。”
武士们得令,一并去抓仓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