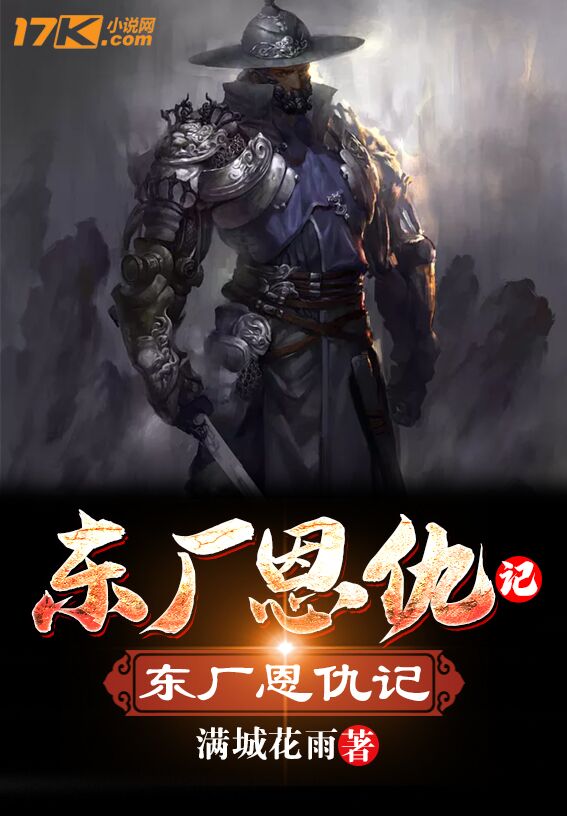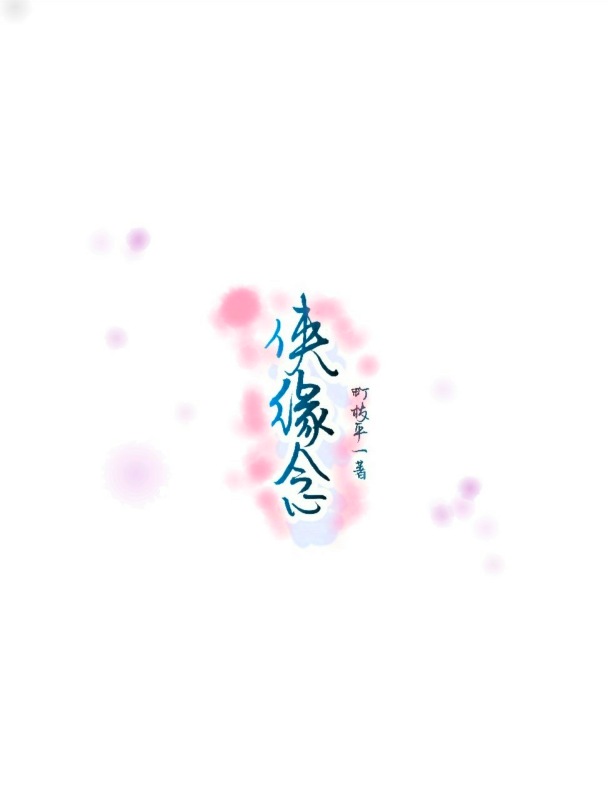床很大,只有会享受的人才懂得床的舒服。
叶秋觉得很舒服,从他被歹匪带上山的时候,就懂得享受,并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浇灌气,而是想以此来穷尽歹匪的家财,那时候的想法太天真。
每每想起他砸掉歹匪刚从商人手中夺来的上好瓷器的时候,就会得意的笑起来,这样的笑即便他要求歹匪给他大鱼大肉,锦衣华服的时候都没有露出过。
何庄的床和山上的床睡起来的感觉差不多,只是少了点喧闹,他竟然希望有人来吵他。
不知道是哪天,歹匪突然将乐彩云绑到了山上,冲着叶秋大吼道:“小崽子,送你当夫人吧,以后你就是京城首富的乘龙快婿了,以后可别忘了老子我呀。”
乐彩云初来山寨,惊恐万分,整日哭哭啼啼,弄得人心繁杂。
匪头扬刀而起,怒目圆睁,再加上本就是粗犷黝黑的脸,着实有些鬼怪的模样,大喝道:“再哭,兄弟们就把你煮了下酒。”
乐彩云声音越哭越大。
匪头瞬间没了耐心,刀尖闪过白光,劈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叶秋横冲而出,抱起乐彩云滚到一边,刀刃只是劈断一张长凳。
叶秋心中凛然,愤怒地捡起那破坏的长凳,抡起到头处砸向匪头。
匪头哪里料得叶秋有如此一举,刀重压手,已经回刀不及,眼中闪过诧异。
“嘭!”
凳将匪头击得脚步不稳,重心一个趔趄便倒地不起,匪头手捂满是鲜血的头颅大喝道:“小兔崽子,你他奶奶的找死。”
要不是平常几个跟叶秋关系不错的匪类拦住了匪头,估计叶秋早已经分头落地了。
最主要的就是,这件事情以后,乐彩云见着叶秋就感觉跟见了菩萨一样那个虔诚跟随呀。
即使叶秋躺在床上的时候,乐彩云也会跟猫一样偷偷挠着他的身体,那种感觉有些痒,也有些让人觉得舒服。
叶秋现在就感觉有些痒,猛地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乐彩云正在用草撩拨着自己的鼻子。
叶秋心中其实还挺有些怀念,笑道:“好几日不见你,还真是有点想念呢。”
乐彩云挑眉坐起在叶秋的身上,挑逗道:“想我就赶紧娶我呀,娶了我天天都可以看见了我。”
要说人就是奇怪的生物呢,不见就想,见了又嫌烦,叶秋现在深有体会,他被个女人这样骑着,身体不自然来了反应,脸色因羞涩泛起红光,咬着嘴唇道:“小姑奶奶,你别折磨我了好吗?”
乐彩云越瞧越喜欢,长长的睫毛像蒲扇一样扇着,嘟着嘴就准备往叶秋的嘴上亲去。
叶秋哪里肯定,但也不能就这样突然翻身,正在苦无逃脱之法的时候救星就进来了。
易含笑当然不忌讳看到这些,谁没有点热血沸腾,年轻气盛的时候呢。
现在他的心给了一个朴素的女人——花妹,他甚至都舍不得去细想,每次脑海里面刚浮现出这女人面容的时候,他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阻止自己继续想下去,否则真得难以抑制那不能陪伴左右的自责与痛苦。
他摇了摇头,露出笑容,道:“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乐彩云斜过头大骂道:“知道还不赶紧走。”
叶秋扯着嗓子喊道:“别走,别走,救命啊。”
乐彩云瞪着叶秋,又瞪着易含笑,说道:“大半夜不好好睡觉,打扰人家睡觉,你有没有王法了。”
虽然这么说,但是她还是爬到床边穿了鞋出了门,回头不忘说道:“小叶子,你给我等着。”
乐彩云不会武功,脚上的力道没轻没重,奔走的时候像只没有任何防备的兔子,既然是兔子就应该是这样活泼的。
易含笑袖口一拂,门像是被股奇异的风刮起一般自动合上。
他的神情突然变得不自然,嘴角时不时会抽搐,凝视着早已经整理好衣衫坐在他对面的叶秋,字字缓缓道:“你挑这时候喊我过来就是为了看你们嬉闹吗?我不觉得你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很聪明。”
叶秋淡淡道:“你不觉得跟我这个聪明人交朋友很累吗?”
易含笑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了,悠然道:“挺累的。”
叶秋眼睛里光芒闪动,想说些什么。
易含笑突然出手,速度很快,他的笛子像个有灵性的生物一样抵在叶秋面前,面露微笑道:“请我喝杯茶,这夜色如此撩人,喝茶舒心。”
“好!”
窗外的人影闪动几下,终究离去。
易含笑这才吁了口气,像摆脱巨大的监视一般,叹道:“身不由己。”
叶秋低声道:“我知道。”
易含笑道:“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叶秋替自己倒了一杯茶,自顾自地喝起来,知道易含笑是不喝茶的人,所以对其也没有必要太过于客套。
他又呡了一口茶,才淡淡说道:“从胡二峰被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当日你并没有见过女尸,自然也不会知道女尸脚上没有穿鞋,你却突然告诉我胡二峰这个名字。”
易含笑板着脸,不是生气,只是在认真倾听。
叶秋舔着舌头,手又开始情不自禁地摸着自己的鼻尖,或许是习惯,总之他每每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没来由的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易含笑看着他。
他们恍若两个对弈的老者。此时的叶秋将要走出最后一颗棋子,这颗棋子是不可能走偏的,落子的时候便是易含笑输掉的时候。
叶秋走出了最后一步,他冷静的不像个少年,反而出奇的沉稳,继续道:“你告诉我胡二峰名字的时候,我就知道除非那天你早早就发现过尸体,又或者有人陈述了那天的情况。”
易含笑道:“说下去。”
叶秋继续道:“你不可能在那天出现,你名气太响了,有人见过你抱着一个人在万福镇的潇湘楼出去,如果说你要安顿一个受重伤的人,还能够同时在另一个小镇的话,断然是不可能的。”
易含笑苦笑着,脸上像凝固一样,叹道:“不是重伤,是死了,他死了。”
他好像要哭出来,没有任何预兆就变得如此的脆弱不堪。
他还是那个风趣幽默的易含笑吗?
他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