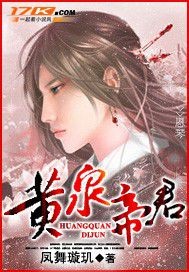此时天空中乌云早已消散,东方天边太阳只露个头顶,大地上百里空旷,天空中万里无云,山下尽是干草,那马吃得饱了,早已蓄势待发,此时它逆着风却也跑的飞快,它身上黑毛被风吹得齐刷刷的向后方倒下去。
辰和琅只觉冷风扑面、凉气灌耳,他们此时都已全无心事,畅然之际不但不觉风冷,反觉说不出的飒然清爽。
他们饿了吃些干粮,渴了在河边喝些水,空旷草地之上也不缺干草,那马便尽管吃来。过了不几日,他们便到了辰几日前买马的城中,此时辰所带的干粮也所剩无几,他们下马,牵马进了城去。
二人到得城中,买了些干粮,又买了匹马,也不在城中停留,牵着马往城南门而去。
此时行人往来不绝,许多人肩上挑了担子,担子两边是两个封了盖的木桶,也不知里面盛了什么,二人见了此情景都颇感诧异。将到南门时,琅说道:“师弟,我们去个地方找碗水喝吧,这马也该饮一印了。”
辰早已闻到了酒馆传出的阵阵撩人酒香,说道:“我们去喝几碗酒吧。”
琅笑道:“师兄这见了酒就心痒的病非但我治不得恐怕连师父也给你治不得了,我陪师兄喝个两三碗还是可以的,我们赶路要紧,师兄可不要贪多。”
辰笑道:“师弟又不是不知师兄酒量,我就是喝个两三百碗也只是润润喉咙而已,今日我只喝个十几碗就当是解渴了吧。”
琅假装无奈,摇头叹气道:“唉!师兄见了酒就是谁也劝不住了。”
二人欢笑声中牵马到了酒馆旁边,辰说道:“店家,劳烦饮一下我们这两匹马,先给我们沽五斤酒来。”
那店主见了辰,说道:“吆,这位客官又来了,上次客官自己一人便喝了十斤酒,这次怎么此次你们两位却要五斤?”
辰仔细打量那人,想起这正是他要十斤酒而只给他沽了二斤的那人,原来此次他们又到了这一家酒馆中,辰说道:“此次不同上次,你先上了五斤来再说,别忘给我们饮马。”
那店主听了笑道:“客官,你们要我给这两匹马饮多少水?”
辰听了微怒道:“怎么这么多废话,你只管将它们喂得饱了,你还缺得这点水吗?”
那店主苦笑道:“客官,听你说这话定然不是本城之人,客官可知道我们这城是什么名吗?”
辰摇头道:“这我还当真不知道。”
那店主笑道:“这城名叫旱城,这“旱”字便是干旱的“旱”,我们城中祖祖辈辈缺水,这城里的水有多数是从临近的城中买来的,你看街上这些人辛苦挑的都是水。我们帮客官饮马都是要按水量收钱的。”
辰惊道:“竟有此事,好吧,你只管将这两匹马喂饱了,水钱我一文也不少你的。”
那店主给二人安排了张干净桌子,高兴着去沽酒了,那两匹马由店中管家牵了下去饮了。
琅说道:“想不到这城中之人生活如此困苦,就连用水都要从其他城中买来。我虽可医得小病,但见了这满城之人悲苦度日的惨状却没有一点办法。”
辰叹息道:“师弟不要介怀,此城连年缺水乃是天灾,又岂是人所能解决的了的?”
琅摇头道:“方才那店家说他们这里多数水是从临城中买来的,可见临城中是并不缺水的,若自临城与此城中打通渠道,将水引到城里来,旱城城民也不用日日受这般苦难了。”
辰说道:“师弟如此仁爱胸怀当真是菩萨心肠,可这两城之中各有城主管辖,两城之间不起战争能令得百姓平安已是难能可贵的很了,要在两城之间打通渠道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琅摇头叹息:“这些城主割据一方,各自为王,只顾自己荣华富贵、逍遥快活,却害得这满城百姓困苦不堪,这天下何时才能统一了?”
辰摇头道:“天下要统一难免的要烽火四起,又有多少生灵涂炭?自古以来,这天下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如此分分合合,又有多少无辜百姓丧身铁蹄之下?又有多少将士冲杀战场血染黄沙?这好不容易平和了的各方分据局面却用多少鲜血洗刷出来的?”
他脑海中一时泛起的便是疆场上万马奔腾、血肉横飞的悲惨场面,一时又闪过大军入城欺辱平民、淫奸妇女、肆意烧杀抢掠的场景,仿佛身临其境,感觉竟出奇真切。
琅此时沉默不语,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那店主沽了五斤酒来,琅果然只喝了两碗,剩余的都让辰喝了,辰虽未喝的尽兴,但也解了酒瘾,他结了帐,二人取了马走了。
他们只要了五斤酒却足足花了五两银子,其中有三两多竟是那两匹马饮水的水钱。这些银两本就是辰自宣城中盗来的,他一路大手花来竟也还剩了许多。
出了旱城,二人分马而行,过不多时,便到了宣城外寸草不生的空旷之处,辰的马跑得快,辰便教那马放慢了跑,二人便之隔了几丈远,辰勒马停下,琅也跟着停下,问道:“师兄,怎么了?”
辰说道:“我上次同你提起过的那身患怪疾之人便居住在这左近。那晚我便是在此处遇到了他。这地上的火把便是那晚一群聚会之人所留下的。”
琅低头看去,见地上果然零零散散有几只火把。
辰向左望去,见前方不远处那口油锅犹自架在那里,不解说道:“这宣城地广人多,白日里开城之际城外人也不会少得,怎得这口铁锅还一样架在这里,也没有被人取了去?”
琅说道:“平民百姓见了这么大一口铁锅哪有不取的?这事真也奇怪。”
辰向东望去,看到那座小山,说道:“师弟,叶便住在那山林中,我们前去看看吧。”
琅早就想亲眼看个究竟,喜道:“甚好。”
琅和辰不几时便到了那山林脚下,琅将马栓在树上,辰只将马停在原地并不拴住。
琅问道:“师兄可知道叶住在何处吗?”
辰摇头道:“这山林不大,我们进去找找就是。”
正在此时,一声驴叫自林中传来,辰喜道:“这驴子正是叶的坐骑,我们循着叫声找去自然就找到他了。”
辰说完,便向林中去了,琅紧跟其后跟了进去。
只走了一会,便远远见到一间小屋,小屋前一头瘦驴正在吃草,二人又向前走近了一段,便已隐隐听到悠扬琴声。
辰喜道:“他正在屋中。”
二人向小屋靠近,那琴声已清晰入耳,琅笑道:“他倒弹得一手好琴。”
辰朗声说道:“叶兄弟,辰看你来了,莫搅了你雅兴。”
屋内琴声立止,一个声音自屋内传来:“可想煞我了,快来跟我对弈几盘。”说话间一个穿了件脏呼呼的白色长衣的高大男子自屋中走了出来,他走到离二人两丈远处便停下,琅和辰二人只觉奇臭扑鼻,辰早有防备,便不以为奇,琅虽听辰说起过此事,但初次闻到也不免吃惊。
辰笑道:“今日我却不是来跟你下棋的,这位便是闻名江湖的琅医生,我请了他来给叶兄医病了。”说完指指琅。
琅刚欲说话,叶已抢先冷冷说道:“原来是江湖名医到了,久仰大名,不知你那医死人的医术有多高明?”他将母亲之死全部怪到庸医头上,是以他对庸医甚是憎恨,便恨巫及屋,开口便是讥讽言语。
琅听他说话如此无礼,也不发作,淡淡说道:“我虽不会将活人医死,但这紫兰草的毒我却能解得。”
辰大惊,惊的是他虽然将叶的病情同琅说过了,但却未跟琅提起过紫兰草一事,叶听他说出这话也是吃惊不小,却面不改色说道:“这紫兰草乃是一味难得的药材,我便是为了寻找它而得了此怪病,琅医生竟然说我中了紫兰草之毒,真乃贻笑大方,我根本就没有找到紫兰草,若是找到了它我娘的病便早已治好了,我又去哪里中了它的毒了?想来大名鼎鼎的琅医生定是听了我辰兄弟之言,便出此言语耸人听闻,叶某可真佩服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