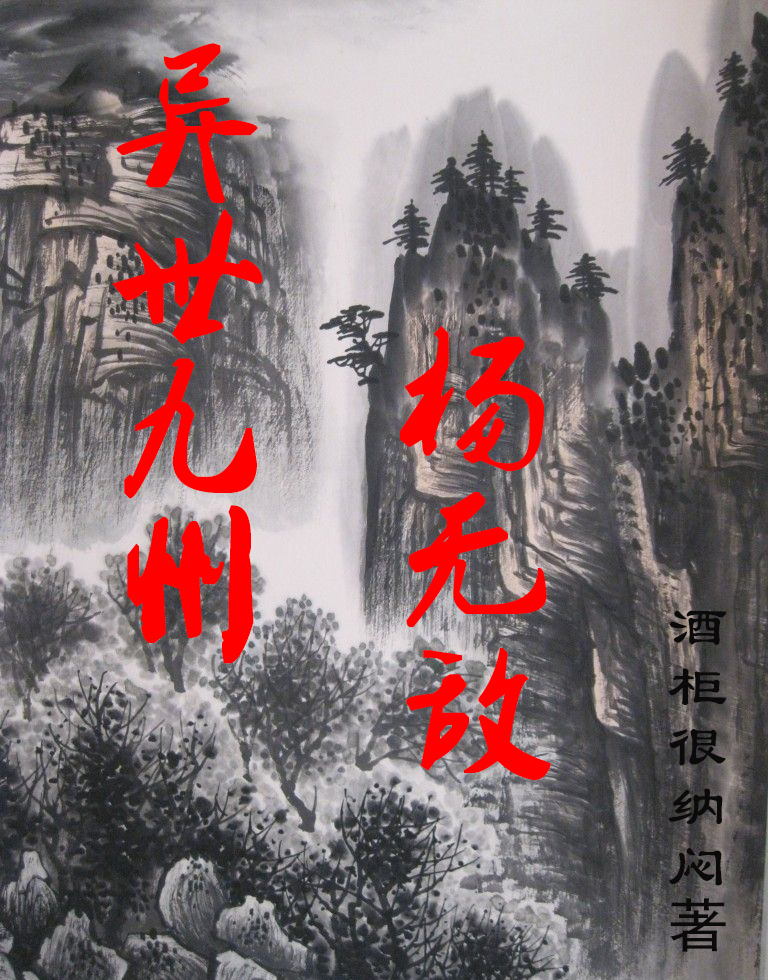程贵嫔是真不知道家里的状况已经差到这种地步,她一出来家里也没人入宫来,别的人更不会无缘无故地过来跟她说你家里快不行了,就算有,恐怕她也不信,反过来还会怀疑此人心机叵测、别有目的。
女人的圈子都是随了父兄的,有时候不用看男人之间如何,只要看他们背后女人的往来就能将几个党派的情况猜个七七八八的了,而不巧的是,程家因为和静大长公主以纯臣自居,直到程陈两家联姻,这才与京中其他几家有了往来。
如今,程家被陈家所累,其他几家跟程家本就交情一般,出自这些家族的妃嫔连捞程贵嫔出来都不出力了,更别指望她们会好心来提醒她家里的情况。
见差不多了,白苏燕这时候出来做好人了,“行了,都差不多得了,阎充媛你如今既然已经是陛下亲封的正三品充媛,虽然是九嫔之末,那也是实实在在的品阶,如今这宫中四妃之下唯你最尊,那你就该拿出你身为充媛的气度来,莫要为了几句酸话就骂骂咧咧的。”
阎充媛微躬身,道:“是臣妾失礼,臣妾谨记。”
说完这个,另一个也不能幸免,“还有程贵嫔,本宫以为你日前已经受了教训,如今看来这紧闭关的还不够,也罢,本宫罚你紧闭七日,抄写宫规静心,要知道这是在后宫,是以后宫的品阶上下定尊卑,别把前朝的事带进来,你们听明白了吗?”
“诺。”
毓才人如今是死心塌地的依附白苏燕了,立马马屁跟上,“贵妃娘娘教训的是,后宫是后宫,前朝是前朝,后宫不得与前朝勾结这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谁敢违背?”
“正是如此,”白苏燕扫了一眼众人,“连来自民间的毓才人都如此懂事,程贵嫔你可莫要再闹情绪了。”
程贵嫔知道眼下不清楚家里具体如何,也不敢再摆架子了,一咬牙,直接离座正跪叩首,“嫔妾谢贵妃娘娘与充媛娘娘的教诲。”
白苏燕懒洋洋的挥了挥手,道:“没什么事,就都散了罢,德妃,你留一下。”恪德妃微微一愣,却还是一贯恭顺的应下。
待人都退出去了,白苏燕看恪德妃紧绷的模样,暗衬自己很恐怖吗?思及她是宫中最受珝月太后喜欢的,白苏燕不禁语气也尽量放得柔和,道:“你也别紧张,就是问问嘉善帝姬的洗三礼。”
恪德妃谨慎的道:“一切照旧,就是别越过她的姐姐们。”
白苏燕想了想,道:“那就依垂佑帝姬当时的礼仪办吧?”嘉善帝姬的洗三礼说实在的还真不好弄,一方面按太后她老人家的心思定是要压掌珠帝姬一头,而洛霜玒就肯定不乐意了,要是这个度把握不好,遭殃的就是她了,另一方面恪德妃习惯了低调自然不想大办,免得给永宁宫招来麻烦。
恪德妃也是明白白苏燕的难处,想了想当初垂佑帝姬的洗三礼规格也是不小了,也比不上掌珠帝姬,便也点了头,道:“此事就麻烦贵妃娘娘了,臣妾是觉得升平一出生陛下就为她赐号,已经是独一份的殊荣,洗三礼还是一切从简的好,臣妾还要去太后那请安,先行告退。”
“去罢。”
恪德妃离开后,宁贵嫔、良嫔、毓才人相继入内,良嫔笑眯眯的恭维道:“有德妃娘娘帮贵妃娘娘在太后面前说话,嘉善帝姬这次的洗三礼贵妃娘娘不用如此为难了。”
白苏燕耸了耸肩,抬手示意她们落座,又对毓才人关切的道:“头三个月最是要紧,你这样上蹿下跳的,本宫看着都跟着心惊肉跳的。”
“没事的贵妃娘娘,太医说了要适当走动,生产时才不会气力不足,”毓才人笑呵呵的,又转而说起早上的事,“不过今日对阎充媛真是要刮目相看了,这气势摆的还真足,挺像个样子的。”
良嫔道:“如今她可是四妃之一的第一人,膝下又养了皇长子,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程贵嫔是活生生送上门给人家当立威的靶子。”
程贵嫔在宫中虽然也没有作威作福那么夸张,但是仗着大长公主的后人,说话、行动间总是隐隐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早惹得不少人心中不快了,尤其大倾以世家望族血脉为傲,又有几个真看得上她。
宁贵嫔却道:“嫔妾只怕贪心不足蛇吞象,阎充媛是一个小小的县官之女,她的娘家可以说对她毫无助力,她能靠自己爬到今日的地位可见不一般,如若她真的……嫔妾怕她会是娘娘的心腹大患。”
白苏燕略微思索了一会,道:“说来这事,本宫说出来也是给你们提一个醒,阎嫔在年节时,收到过一封家书,就混在尚宫局奉上的年礼中,本宫私下审问了她身边的人,得知那封家书上写了她兄弟因为出身被考官落榜,她父亲为此气倒了,卧病在床。”
毓才人扭捏的道:“这也不是她害安妃的理由啊,安妃对她多好,再说了贱妾听闻安妃可是一族人都指望着她一个了。”
良嫔犀利地问道:“敢问贵妃娘娘这封家书的来源可查了,是怎么递进来的,这入了宫的女人可不许往家里递信的,就是娘家人入宫也不能多谈宫中之事,这幕后之人恐怕所图非小,若真是如此,可阎充媛也没吃亏啊!”
白苏燕道:“本宫一得到消息就派人去查了,可巧了,还真是什么都没查到,阎充媛的娘家又在丰县,本宫无缘无故的也不好派人去取证是真是假,万一这是真的现在过去了人已经打好了,万一假的,宫中居然还藏着这样的人物,岂不叫人害怕?
你们既然都是本宫身边的人,本宫希望日后遇到什么事,只要不过分越界,本宫能帮的一定是竭尽所能,定不辜负几位妹妹的情谊。”
三人躬身致意,道:“臣妾等也定不辜负娘娘的情谊。”
重新落座后,毓才人试探的问道:“贵妃娘娘,您看李答应这块朽木,可值得您花费工夫雕一雕?”
白苏燕不答反问:“怎么,她坐不住了?”
毓才人尴尬的扣了扣手指,道:“那倒不是,是贱妾觉得自己都对她夸下海口了,却……给贵妃娘娘添麻烦了。”
白苏燕心道:你还真给我找了个麻烦。
但话肯定不能这样讲的,白苏燕依然端着温婉的笑容,道:“如今陛下的心思全在落红殿那里,剩下的就是朝政,此事本宫就算勉强能帮李答应安排上侍寝了,也不过是让他过后就忘,不如再等一等,毕竟男人是猫,不是吗?”如今说起这种瞎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良嫔张了张口似乎要提一提自己宫里的人,最后还是闭上了嘴,掩饰的端起茶盏喝了一口,毕竟自己现在都还没着落,哪里顾得上旁人,不过董贵人最近未免也太安静了,反而让她放心不下。
白苏燕也趁机自然而然的转了话题,说到了日常、应季的衣饰上面,说真的,她以前总不耐烦学这些,东拉一块西拉一块,入宫后没事干反而一次性都齐活了,别人说起某某某衣裳的绣纹时,对于刺绣针法也是张口就来,当然她女红实操还是一团糟。
好不容易良嫔与毓才人也走了,宁贵嫔这才说起自己对“家书”的看法,“嫔妾以为这封家书是假的,不过是有人知道了阎充媛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野心,推了她一把而已,安妃……嫔妾反而希望她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白苏燕叹了口气,道:“你说这宫里的事怎么就都那么复杂,一后面还跟了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环套一环的,没完没了的,家书的确是假的,推了一把的人是锦贵嫔。”
宁贵嫔也不觉得意外,按锦贵嫔的性格会提前出手打击有子的妃嫔防范于未然也属正常,“不过嫔妾看来阎充媛反而比安妃更难对付。”
“比起这个,本宫更头疼的是贤妃居然也掺了一脚,”白苏燕端坐了半天早就累了,眼下都是自己人都更没骨头一样直接叫人搬来引枕,该坐为半躺,靠在上面,“这锦贵嫔的肚子可能有点问题。”
宁贵嫔皱眉道:“肚子?锦贵嫔不是跟随陛下到围场伺候时怀上的吗?”话一出口她就反应过来了,围场那边规矩不如宫中严,加上又是与流国、原国会面,这来来回回的外男就不少。
白苏燕道:“告诉你是让你心里有个数,日后离锦贵嫔远一点,接下去的事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你好,其实罢,后宫与朝堂哪里真的能泾渭分明,根本就是一个漩涡,知道的秘密越多就陷得越深,一旦被卷了进去,到不了漩涡中心的,最后都得死。”
宁贵嫔也不多问,只是道:“贤妃娘娘若真的有心与娘娘您争个高低,就算贵妃娘娘如今样样比她强,可要完全压制她,难免要伤筋动骨的,若让旁人趁虚而入,眼下的大好局面可就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