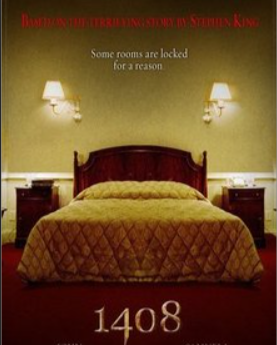直到远远再也看不见那一片石殿,木姑娘那近乎于落荒而逃的脚步才稍稍慢了下来,她重重地喘了一气,很是无语地开口:“明霜,我现在有些理解,为何暗溪会看上你了。”
潇洒风流气度不凡且风骚入骨的司水魔君暗溪,大抵便是见了自家隔壁彪悍的一大一小两个魔女被其荼毒已久才转而被掰弯惦记上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暖萌系少年明霜,木姑娘表示,这是她总结的血一般的真理。
闻言,明霜那不笑而弯的薄唇可疑地僵了一僵,再一想到某人那大胆而露骨的撩拨,他白皙的侧脸很是不争气地泛起了一层浅薄的红晕,似是有些不自在,他故作镇静地开口:“阿花,你想多了。”
对于这般苍白而无力的解释,木姑娘很不厚道地笑笑,继而好心地转移话题:“明霜,你们,期待有阳光的地方么?”
虽然瞎瞎的眸间满是小狐狸一样的狡黠,但木姑娘却是一眼看到,那藏匿于其间的执着,懵懂之中隐隐透着一股让人心疼的失落。
似是没想到她话风转变如此之快,明霜初时愣了愣,继而沉声开口:“当然,六界众生一般,谁甘愿永堕黑暗,晨光晚照,烟霞万千,若有此,我魔界何苦战乱,屠戮流离,你以为神凡两界有多么让我们稀罕。”
这是木姑娘第一次听到明霜说出这样一番近乎于冷厉的话,她一直以为作为暖萌系少年的明霜该是温和的,正思忖间,便听他接着开口:“城主很早以前就说过,魔帝陛下他原也是厌恶血腥杀伐,只是,他想要为我诸天魔界臣民开辟一番天地罢了。”
听罢,木姑娘也是陷入了沉思之中,连明霜是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了。
七位夫人喜欢晒永远也洗不完的衣裳,瞎瞎姑娘渴望成为诸天魔界的大地主,那位传说中的七魔将据说经常偷偷跑到人界漠南去晒太阳仅仅是因为自家夫人喜欢古铜肤色的美男子……
好像,一切的期许,都源自于再正常不过的天地自然,却在诸天魔界变得虚妄而飘渺,她甚至有些怀疑,她该不该绝了这最后的一线生机。
青弦自万魔殿回来,一眼看到木姑娘似是神游天外地坐在石阶上,他不自觉地把那缠绵着凤羽花的赤色袖摆往下扯了扯,转而缓步上前,倾身蹲下,那妖冶的凤眸微挑,美得山河无色,似是戏谑着开口:“阿花,不过一日,想本主想得这么入神?”
木姑娘却是摇头,她那明媚如花的月牙大眼稍显黯淡,连声音,都不自觉带上了一丝沙哑:“青弦,你说,神魔还会开战么?”
倒是没想到她会如此一说,青弦那妖冶的凤眸稍稍敛了敛,他甚是随性地坐到木姑娘身侧,闲散地撩了撩那旖旎了一地的衣摆,转而状似漫不经心地开口:“为何,有此一问?”
闻言,木姑娘缓缓侧头,一眼望进那一双不觉幽深的凤眸里,近乎一字一句地开口:“因为,有很多我喜欢的人,不想失去。”
“喜欢的人,包括我么?”青弦似是玩世不恭地笑了笑,那薄削的唇,微勾起一抹诱人的弧,摄人心魄。
见此,木姑娘却没有他预想中的鄙夷,反而甚是平静地点点头:“当然,青弦,你该知道我有多在意。”
她知道什么叫不能分心的亏欠,譬如楚修,譬如少尊,譬如青弦,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些在她心里扎根的惦念,不错,她是把刑大公子看做唯一,但是除了那些风花雪月所谓镂刻在烟火里的痴缠,她还有很多的心来留待那些不能抹煞的邂逅,不若刻骨相思,但分离依然会痛在心上。
她鲜少有如此一本正经的时候,青弦眉梢的邪肆的笑不觉收起,似是思索了一番,他长腿一撩,很是慵懒地躺倒在身下的石阶上,似是漫不经心地开口:“央儿,你比我想的,要聪明许多。”
闻言,木姑娘那隐在层叠云裳之下的小身板不觉僵了僵,她轻轻抚上腰间那一枚妖娆的血色凤羽,几乎轻不可闻地开口:“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很笨?”
许久不见他有何反应,木姑娘不禁抬眸,明媚的月牙大眼看向那暗沉的天际,寥廓如斯,不主沉浮,她自顾自地开口:“其实,我一直都在等,等着你亲口告诉我。”
闻声,青弦不禁伸手盖住那一双妖冶的凤眸,唇边那一抹隐秘的笑也消失殆尽,似是过了许久,他轻声开口:“可是,我有些不敢了。”
九凤遗族,魔祖之子,本该是随心所欲的天地主宰,可是,在她面前,他却是总也少了那么些许的果决,这个上苍连施舍都稍稍嫌晚的半个邂逅,他再经不起一点点的失去,所以,他不再给自己任何的不确定。
听她说罢,木姑娘那黯淡的眸子蓦地一缩,就只一句话,便教她心上开裂一般,她不自觉地抓紧了身侧的裙摆,近乎恍惚着开口:“那么,让我来说。”
就像那些注定错开的路口,没有人可以避过,既然他不说,那么就让她,再做一次狠心的人。
狠狠地吸一口气,只觉胸腔里都是呛到人眼眸发酸的味道,她艰难地扯了扯淡到发白的唇,近乎轻颤着开口:“怎么办,我好像不知道要从何说起。”说着,她似是无奈地笑了笑,继而轻声说道:“嗯,要不就说说碧落之巅好了,其实,当初借着轻薄我的名义坑了我许多玛瑙的,是你,对不对?我一直在想,比襄那个伪君子怎么可能给我一种莫名的温暖,对了,就是掌心的那种温暖。”
大概是源自于灵魂深处的熟悉,她竟然忘了拒绝。
“原本,我以为一切都是巧合,可是地下王城的一切历历在目,楚修死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我的绝望,在那声嘶力竭之后的千疮百孔,深深烙印到灵魂里。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失去,正如我不想亏欠任何人,可是你却偏偏给了我最狠的一刀,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宁愿百倍千倍地应在自己身上,也不愿背负任何的血腥。”说到这里,她似是无尽怅然地笑了笑,掌心那纠缠的脉络似是被生生掐断。
然再是不愿又怎样,那些不能倾覆的过去,终究改变不了。
“你说得很对,其实我一点也不笨,但是又有谁知道我宁愿自己笨一些,什么都不知道,那些点点滴滴的暗示,我一次又一次地忽略,可是,终究还是自欺欺人罢了。”说着,她长袖一挥拿出那一把青色的纸伞,再一一细致地抚过那雪色的九凤云纹,恍惚着开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只九凤,与你那夜在未央城所画的几乎一模一样,如果这还不够,那么我腰间这枚血色凤羽呢?九凤遗族,诸天大妖,不说浮华六界,单看这诸天魔界,除了九歌之子,魔族少尊,又有谁可以这般肆无忌惮地着凤纹绾凤羽?”
至此,青弦终是不再沉默,他薄削的唇无声地勾了勾,转而轻声叹道:“还有么?”
闻声,木姑娘只觉心上那紧到极致地弦一下绷断,她倏地倾身,几乎是半趴到他身上,那隐隐染着血腥的手死死抓住他赤色的襟口,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开口:“你还要我说什么?是说无数次的亲近你们都给了我一样的感觉,还是说明明没有死却偏要我许下来生?你到底想要怎样?”话落,那双明媚的眸子早已被湿意模糊一片,落在他脸上却是刺骨的凉。
见此,青弦那妖冶的凤眸无声地眯了眯,看着咫尺之间那一双朦胧的大眼,他却是倏地笑开,悲怆至极,连四周轻颤的空气,都一下冷凝:“我想要你怎么样?央儿,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之于我,从来都是无法,我又能拿你怎么样?”
这一刻,万千风华尽敛,山河无寂,公子未央,失了那通身的气度,他不过,一个爱而不得的男人。
他话里的绝望那样让人哀伤,木姑娘只觉心上已是寸土荒凉,她手下的力道紧到不能再紧,勒到掌心的裂痕都是钻心的疼,那原本粉白的小脸也是一片灰败的白,她几乎是恶狠狠地开口:“谁让你自作多情了?又是谁让你无法了?你诸天魔界随便拉一个女子都比我美上百倍,为什么要来招惹我?”
看着她眸间的狠厉,他却是难得地柔软下来,浅笑着开口:“好了,不要生气,是我自作多情,你若不喜欢,那我以后改,好不好,我会试着少想你一些。”
原谅他,只是不愿再寂寞,既然遇见,再晚,他也要走下去。
见此,木姑娘却是摇头,她似是恍惚着笑了笑,继而凑到他眼前,深深望进那一双勾魂摄魄的凤眸里,近乎一字一句地开口:“我不许,想也不行,你一定要学会去爱别人,如果你真想我过得好。”
闻言,青弦那凤眸稍稍一敛,继而邪肆一笑:“我考虑看看。”言罢,他倏地伸手,扣着木姑娘后脑重重压下。
那般温软而甜腻的触感,是他肖想过无数日夜的,如今尝到,却是再也不愿放开,那近乎肆掠的一吻,带着不容拒绝的霸道,还有飞蛾扑火般的绝然,他一向不愿亏欠自己,与她,更是如此。
唇齿相依的感觉,陌生而刻骨,他细细品味着掺杂在其间的咸香,用上了一生的力道才压下那挠在心上的挣扎。
亘古沧桑,不绝红尘,他不过一次的情难自禁,都湮灭在了这一场焚心烙骨的痴缠。
直到连心口都麻木,他才恍惚着松开,把她柔软的小脑袋按到自己胸前,隔着那赤色的织锦,他隐约感受到浸染的湿意在悄然蔓延,然他却是再没有力气,去哄一个注定要松手的姑娘。
这样无力而绝望的青弦,是木姑娘从未见过的,她甚至来不及质问那一个肆掠的吻,便陷进了铺天盖地的哀伤里,双手无力地垂下,她扯了扯唇,才很是艰涩地开口:“青弦,我说的是真的,你要学会去爱别人,其实,我这么笨,又无耻,还无赖,一点也不好,就是斩冬美人,都要比我好上许多。”
感受到他片刻的僵硬,她似是不死心地开口:“斩冬美人不行,那裁春呢?或者是离夏?还有剪秋。”
见她恨不得把她认识的魔界女子都过个遍,青弦无声地摇了摇头,那一双妖冶的凤眸黯淡到连天际都幽沉如夜,他浅叹一气,似是无奈地开口:“你这么急着把我推开,是不是怕我找你履行当日的诺言?你说,只要我找上你,便以身相许,可是连我的嫁妆都收了的。”
闻言,木姑娘倏地一僵,转而迫不及待地开口:“没有,我是真的希望,你过得好,至少要比我好。”
“也罢,就算你愿意以身相许,我也要不起,不然,我诸天魔界就得被某人碾成灰了。”说着,他恍然一笑,纤长的手不自觉抚了抚她披散的墨发,却是再无一言。
感受着他掌心那难言的温柔,木姑娘不自觉地吸了吸鼻子,很是软糯地开口:“那你告诉我,要怎样才会学着去爱别人。”
她想,他已经是自己生命里不可剥离的伤痛,既如此,便给他一个新的归属,让那些刻骨相思彻底烂到暗处,直到她终于不再亏欠。
闻言,青弦似是一下回归了那个风华绝代的城主大人,一袭红衣猎猎妖娆过墨色流年,他妖冶的凤眸斜斜一挑,转而邪肆一笑,戏谑着开口:“何日我永夜不昼的魔界得见晨光晚照,烟霞万千,我便如你所愿。”
“那么,我们说定了。”
只是,大概谁也想不到,在很久很久以后,当某个姑娘真的实现了诺言,那个眸色万千的红衣城主,却因着那寸断在血腥里的执念,再也学不会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