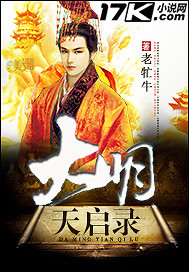周毅因为参与机密,也破例入坐,席上最重要的还是讨论曹彰受命去宛城的事情。不过,曹操既然下了明令,让这几人也计无所出。
用完饭,军士前来收拾东西下去。曹彰等人还是继续探讨。却听帐外军士喊道:“将军,司马大人求见。”
几人脸上神色都是一变,曹彰正要请入,韩浩却道:“某与夏侯将军还是回避的好。”不等曹彰答应,便与夏侯敦一起退到后帐。周毅这才走到帐前,掀开门帘道:“将军有请司马大人。”跟着几声朗笑,司马孚便走入帐中。
行礼坐定之后,曹彰问道:“先生此来莫非又有什么礼物见赠?”
司马孚微笑道:“下官听说将军奉大王诏命,不日即要前往樊城御敌,故而前来送行。”
曹彰心里苦笑一下,果然是坏事传千里,脸上却微笑道:“先生有心了。”
司马孚故意叹息一声道:“下官虽与将军只有数面之缘,却深感将军雄才大略,本想多受教益,不料远离在即。下官恐再与相见之日,心中悲切不安。”
这一句隐含的意思,不仅曹彰,周毅听的出来,后面的夏侯敦,韩浩也心中有数。曹彰被司马孚这么模棱的一句话,触到伤处,正不知如何回答,就听周毅道:“大人说哪里话?大人春秋正盛,何来相见无日之说?”
司马孚微微一笑,看着周毅道:“这位将军常随越骑左右,难道不能看出越骑将军祸无日也?”
“大胆。”曹彰一拍案几,低声喝道:“汝怎敢在此危言耸听?”
“下官冒昧。” 司马孚起身一礼,道:“既然将军处之泰然,下官这就告辞,望将军善保千金之体。”
曹彰当然不能放他走,忙起身道:“先生且留步。”看着司马孚停住身形,叹气道:“先生既然知道吾之福祸,何妨再明言赐教?”
司马孚转身大咧咧地坐下,道:“荆州战事方息,赵舒纵有百般谋略,也不敢再妄兴兵马来犯樊城。此时,大王何以派将军前往樊城?下官着实不解。”
这全军上下都能明白的事情,司马孚又岂会不知?曹彰拂然不悦道:“先生既不愿明言,又何必留此多废唇舌?
司马孚也哈哈一笑道:“既然如此,下官也就畅言无忌。”停了一下,放低声音道:“将军,此时大王所忧心的不过两件事。”
曹彰知道司马孚终于要说出真实来意了,自己也需要宛城的十万兵马暂时相助,但却不能让他看出自己的心意,于是平淡道:“愿闻其详?”
司马孚收敛笑容,正色道:“大王此番南下,家兄也知其意不在荆襄,而在宛城。大王所忧虑二事,一是家兄,二便是将军。”
曹彰冷然打断司马孚说话,道:“吾岂能与令兄相提并论?”
“是,将军屡立战功,又贵为王子。”司马孚冷哼一声,道:“可这正是世子心腹之忌,对大王来说,家兄的危害大过将军。而对世子来说,只怕将军才是头等大患。”
这个道理曹彰也明白,在曹操看来,他始终是亲生儿子,而在曹丕看来自己却是他登上王位的最大阻碍。在曹丕的眼中,自己自然比司马懿的威胁大,当下微笑道:“吾与大哥总是同胞兄弟,他朝大哥即位,吾定当恪守臣节,辅助大哥。先生此言又是挑唆之辞。”
司马孚又叹气道:“将军能有此心,可惜世子未必体谅。想家兄跟随大王数十年,多献奇策,广立功勋。却因为杀叛贼徐庶而倍受猜忌,此事家兄虽作的卤莽,却是对大王一片忠心。而将军拥兵更重,身份更贵,也难免受世子猜忌。”
这几句话,既说出司马效忠之意,又言明曹彰的处境。曹彰心里也清楚,司马就算心怀不轨,现在也只是南阳一地,而曹丕一旦掌权,轻则终身闲置圈禁,重则死无葬身之地。现在父王又派自己前往樊城,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问道:“既然如此,敢问令兄是何打算?”
司马孚忽然起身拜倒在地,朗声道:“家兄素来仰慕将军威武,愿为将军效犬马之劳。”
曹彰心中自然高兴,正要说话安抚,就听帐后一声咳嗽,乃笑道:“先生与令兄美意,吾在此多谢,只是世子才德兼备,吾不敢有格非分之想。”
司马孚眼见自己将曹彰说动,却被中途的一声咳嗽破坏,先是一愣,接着起身道:“将军既然甘愿为鱼肉,任凭宰割。下官这就告辞。”
曹彰本想挽留,但是知道后帐的夏侯敦对曹操一片忠心,就算支持自己争夺王位,却绝对不会同意自己与司马懿合作。也只好道:“伯弘,替我送先生。”
等司马孚,周毅离开,夏侯敦和韩浩才从后面走出来,前者面色沉重地向曹彰道:“子文,吾愿意支持汝与子恒争夺王位。但绝不能与宛城司马懿联手,此人素有大志,怀有异心,吾不想曹氏基业易姓。”
曹彰见夏侯敦说的郑重其事,急忙道:“叔父过虑了,某也知司马懿此人图谋不轨,只不过现在大哥一诸曹势大,不得不借助一下。”
“不行。”夏侯敦一脸坚决地打断曹彰说话,道:“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吾宁可让你失去王位,也不能让司马懿坐大。”
曹彰心中大为不悦,却不敢再言,只好道:“一切听从叔父安排,不过司马懿不支持某,必然转向大哥,那样岂不是?”
夏侯敦见曹彰答应,脸色神色也大为缓和,乃道:“子恒名正言顺的世子,怎敢去招惹这乱臣贼子?这点汝勿须担心。”
曹彰也觉得有理,曹丕再不智,也不会落下这等把柄,心中释然,却见周毅急匆匆的跑了进来,慌慌张张道:“中军的兄弟传来消息,大王病情加剧。”
三人互望一眼,曹彰心中大喜,这样的话,樊城之行就可以推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