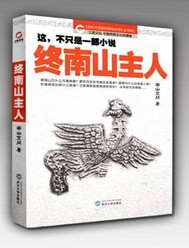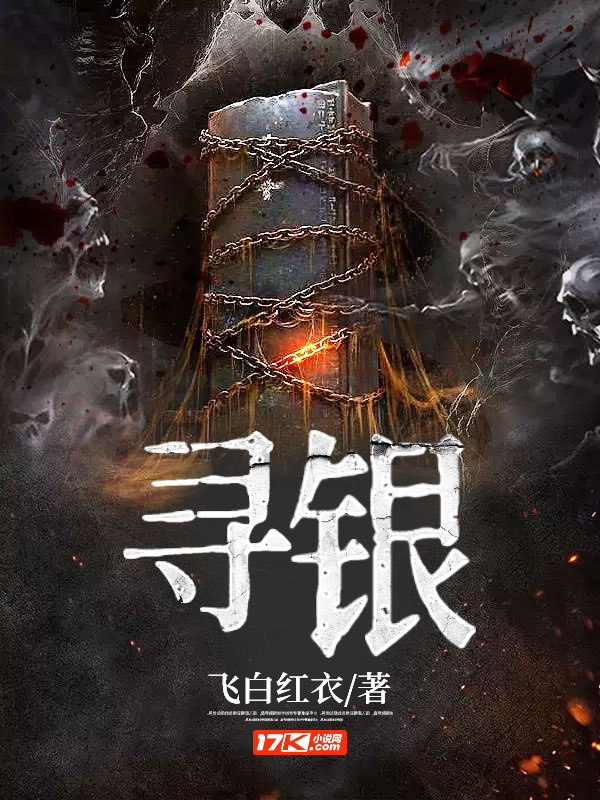秋风很烈,抽打在道旁树身上,时不时发出几声闷闷的悲鸣。韩可孤觉着有些冷,赶紧将衽衣的领子紧了紧,深呼吸了两口气,打出一个寒噤,眯着眼往四方望去。
远处是一排平地起的简陋棚房,不是地窨子,一定是流民的新建。人的求生欲望不可挡,虽然有金兵四下围剿阻拦,仍止不住不停有其他地方过不下去的人们通过各种渠道逃难来此。韩可孤一面想着,一面带着韩炜往那方走去。
棚户中人自然不会识得面前站着的是能够一语决定他们生死的大人物,只是北人豪爽好客,也不问来历,便让进屋来,虽然家中无甚拿得出手的东西招待这二位不速之人,但凉水温成的热水总还有,家中妇人忙碌了一阵,将烧开的水分倒在碗里,热情递到这二位客人的面前。韩可孤也不嫌灶台肮脏,称过谢后端起来喝了一口,那双清湛有神的眼睛,只是望着棚上的漏缝开口问道:“如果风再大些,这房子经受得住?”这些陋舍果真如韩可孤所料,是近日各地逃过来的难民逐渐修起来的,看着单薄,所以韩可孤有些担心。那家里的男人愣了愣,心道这两位路过的客人心肠倒好,自己挨着秋风摧残还有闲情操心我这间破烂房子,遂憨憨地笑笑回道:“这几日的风倒是不打紧,只是担心冬天的雪,究竟能不能顶住。”韩可孤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心想即然如此怎么不见脸上有着急的模样?便温和笑着问道:“那么就该早作打算,否则到时候岂不一家大小要受冻?”男人呵呵笑着略作个揖表示感谢:“客人有心!”怕韩可孤担心,笑着解释:“您别瞧这些房子不起眼,但却是有四梁八柱支撑。过几日风小些,再从新苫过顶草,应该不碍事。”见韩可孤仍仰头瞅着棚耙发呆,又笑了笑说:“等来年天暖化冻,也都起成地窨子住,便好了。”居处的事情到这里便打住了,韩可孤又略问了几句粮食够不够吃之类的话,就结束了与这一家人的互动,心里不禁涌现出了一丝复杂的情绪,自己刚刚还在想往闲云野鹤不问世事的生活,而现在———虽然只是路过,却又忍不住问上几句。看来啊,自己的确如蔡大人所说,就是天生操心命。
韩可孤叹息着走在街上,眯眼看着己经升起老高的太阳。风依然很大很冷地刮着,他的心思也随着飞飞扬扬的落叶打着旋飘向远方。自己这次算是第二回逛通州的街,第一次还是在初到的时侯,由李长风陪着走?????。
?????李长风走了?????
是带领着一部分乡军主力被派走的。既然逢到出兵的好时机,下定决心做出的决策便不容更改。不过兵马出行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哪里会有那么简单,粮草筹备、选兵点将、征前动员,一应前期准备工作做完,就进了草长莺飞,夏草繁盛的六月天。
军府众人之前进行过讨论,金国是个极要强好面子的国家,从最初完颜阿骨打不受天祚帝之辱,以二千五百部落兵决然攻辽,便可見其种族性格之一斑。如今辽境尽殁,通州独存,在自己卧榻之侧任由他人酣睡,这很没有道理。如此分析下来,唯一的解释便是金国如今形势一定很不好,与宋南北对峙,夏虎视于北,蒙扰与西北,说明他们正处在疲与奔命之期,肯定涉及到了国本,唯如此才会对于通州快速发展表现出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他们眼中通州不过是秋后残留的一只頻死蚱蜢而已,他们不愿意顾小而失大。况且,正在头痛于四面楚歌,对于通州,他们非不想阻止,实不能也。金国人有这个心态便给了通州机会,做为一直致力于覆金复辽的韩可孤正是需要这种政局变数。制造一些小麻烦,扩充一些实力,即使趁此时节练练兵也是很好的。就目前实力而言,出兵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分寸,即要打得金人出血,又不让能他感觉很痛,循序渐进很重要。关键点是让金国不要过早把关注的目光急切地投向自己,对通州动歪心思。
韩可孤很思念过去的岁月,他清楚,虽然大辽国己经名存实亡,但仍有许多忠诚于她的人,为了这些人,他必须坚持下去,哪怕明知是在玩火。如果仅仅只是韩可孤自己,他真的什么也不怕,己经死过一次的人了,何惧再死一次,他可以很热血很冲动地与顽金拚个你生我死,总在青史上添上一笔忠名就是了。在金国人的眼中,韩可孤的一切力量其实很幼稚很不自量力,根本不堪一击。但他自己清楚,辽国的子民们,对于辽国的皇权仍然残留着天生的膜拜,不要说自己,就是通州,甚至正苦苦挣扎在沦陷区里的人们都或明或暗站在金人的对立面。所以他无惧,因为他背后有很多人支持。通州得道,所以多助。
得道者多助是一方面,有自知之明又是另一方面,金军气势虽见低落,但虎死威风犹存,何况这只老虎不是死,只不过患上小疾而已,绝非通州现在所具备的实力能够正面招惹的,所以制定的作战方案很明确,即是以搔扰为主从而达到牵制目的,伺机攻克通州附近城池,以为屏障之用。
本来韩可孤原定的计划由自己亲自挂帅,只是后来由于萧平之、蔡高岭一众官将坚决反对,将这个的决定给彻底否决掉了,换成了李长风和常子恒。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对这二人,韩大人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