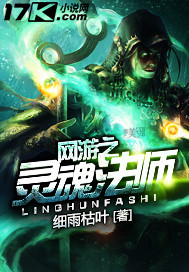“你可知为兄因何要将这桩事体弄得众人皆知?”既然对方不论官称,出口必言兄长,韩可孤不好在称呼上显得生分,却也没有把萧平之的担心放在心上,笑吟吟地问了这么一句。萧平之微微皱眉,他本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此时被韩可孤一问才想到,在传闻中韩大人是极稳重老成、肯与忍让的人,竟突然做出这么一桩表面上看似很不顾全大局的冒失举动,看来并非是单纯为了出口恶气那么简单。他品了一口已经有些微冷的茶汤,感觉有些涩口。诧异地看向韩可孤一眼。韩可孤微怔,没有想到萧平之从军从政许多年竟仍不太通官场世故,而且在骨子里有瞻前顾后的成份,但又不好直接责备他故息养奸,脸上挂起笑容:“为部下出气的心思是有的,同时也是想让一些人清醒一些。”这句话说到后来隐隐有些威胁的味道在里面。极长的沉默之后,萧平之狹长的眉梢忽然间一抖,终于想明白了韩可孤的用意,竟是哈哈大笑起来,旋即平静说道:“京州兵骄悍不驯由来日久,此次吃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亏,想来也能让他们有所警惕?????说不定,真会起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彼此都是聪明人,韩可孤马上抓住了这话里的关键点,想了想后,和声说道:“若要真成警示,还要请贤弟配合一二,才能使京州军知道些进退????。”萧平之极感兴趣地瞧了他一眼,似乎应承了下来,又好像很为难的样子,疑惑说道:“弟愚钝,尤不明白你为何对京州兵????这般坏印象?”韩可孤心想,京州兵这些年所作所为,你如何会不知道?不过是怕得罪了人,不便宣于口、假于色,只做掩耳盗铃罢了。但这份怨慲是无论如何也不好说出口,只能打了个哈哈推搪了过去,而且他明白萧平之对自己依然心有警惕,唯恐对通州存在觊觎之心????。
事情说到这里,两个并不熟悉的兄弟坐在逼厌禅舍中,竟是一时找不到话题来说,场面显得有些冷清尴尬。李长风出恭,用的时间特别的久,二人坐在那里,有些没滋没味地喝着茶,良久,萧平之开口说道:“平之久闻大人贤名,今日得见,喜甚!幸甚!不过也发觉哥哥是很特别的人。”官场之上,开口说话是极考究学问地一件事情,萧平之前面唤大人,后面改称了哥哥,就是公私分开的意思,即能够有效地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又表明可以如唠家常般出言无忌。
经过前面一番浅浅交谈,韩可孤对萧平之有了初步印象,很疏朗直接的性情,这在官场里面很罕见,或许是因为他是军人出身,所以不怎么有那种年少得志的浮躁之气,说起话来并不太讲究遮掩功夫。韩可孤如是想着,脸上浮着笑容问对方:“贤弟缘何如此说?”
坐在他的身边,萧平之却不向这边看,微倾着头望杯中泛花的茶叶,说道:“你是一个很仁厚的人。”他的唇角微微翘一翘:“你对身边的一切人?????都很好??????顾念别人的感受?????”。韩可孤平静回答道:“人为人人才能人人为人,就如货贾交易一般道理明显????人心换人心的意思。我对他们好些,虽然说手段可能有收卖人心的嫌疑????但是没有办法,以我的能力只能做到这一个程度????我只能说,我在尽一个人地本份。”萧平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皱眉头又说:“你还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韩可孤沉默,知道他还是纠结在云内处理闹营事件的情绪里面。 “国体丧失,兴辽正在用兵之时?????你悍然撕破了对方面皮,完全不顾及军人感受,这么狠绝,让很多人大跌眼镜。”萧平之说道,神情中有些茫然。
韩可孤脸上没有什么笑容,跳跃一下目光反问:“你以为人之一生,所活尽为何事?”一问一答中,话题貌似有偏离,萧平之微微一怔,摇了摇头:“我所想简单,就是忠于大辽,铁马金戈,恢复国家。”“复兴大辽?”范闲苦笑说道:“谈何容易!”萧平之又愣了一下,没想到堂堂韩大人竟出现了消极的一面,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接话。“战争频生,百姓流离失所????兵祸日盛之下旧民还有几人暇念大辽故国?”韩可孤叹了一口气:“这些年已经死了太多的人,还且还在继续,我现在很厌倦打仗这种事情。”萧平之嗤之以鼻:“你这是悲天惘人吗?难道为了避兔杀戮,就把恢复江山的念头轻易放弃了?”韩可孤再苦笑了笑说道:“若如此能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亦我所愿耳。”这句话完全发乎与心,是自然而然中的思想透露,让萧平之的脸色为之一白。韩可孤此时才反应过来这话很大逆不道,由愚忠与君到博爱万民,这个转变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他摇了摇头暗自叹息一声,看来受长风的涂毒太深。
“本来就知道你非是简单人物,听明白这句话,才知道比我了解的要更复杂。”萧平之忽然皱了皱眉头:“既然抱着如此想法????为何????还要努力整军?”“我不是圣人。”韩可孤自嘲地说,不等他回应,连续道:“金人对异族狠苛,观以往行径便知残忍程度,只有抗争才可能博出一线活路。”韩可孤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况且????他们与我有灭族亡妻害子大仇!"萧平之默然,这时方才想起眼前的人当年所承的悲痛之巨,难怪对女真鞑子恨心不抑,难怪对同泽劣行深恶痛决。眼睛再看向这位仿佛瞬间便苍老十龄的老哥哥时,心中怜爱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