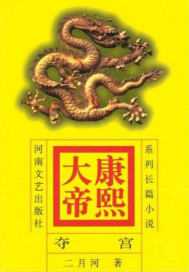皇宫宴席结束后,懿妃单唤季子棠到承乾宫里问话,季子棠看着身子软塌倒靠在她一侧肩膀上微醉的江孝珩,不得不让沈灼先行送他回去。
本就是不能喝酒的人,还非要贪杯将自己灌醉,惹得这般难受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何。
一入承乾宫,便发现早几步回宫的懿妃,早已褪去宫服换了一身简单的常服,懿妃叫季子棠到跟前,询问了王府里的诸多事情,又忍不住多问了两句沈灼:“人还放心吗?”季子棠知道她顾虑颇多,于是说道:“很用心的教主子爷武功”。
“你多盯着点”懿妃无非是防着一点,就怕沈灼是别人安插在江孝珩身边的奸细。
沈灼那头好不容易将酒醉的江孝珩搀扶回王府,一入王府,江孝珩便双脚发软的倒靠在正厅的太师椅上,沈灼言语急促:“主子爷您先在这醒醒酒,我去去就回”沈灼一个大男人,哪里会伺候人歇息,只得去偏院寻人。
府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三人今夜入宫参加宴会,于是各自睡的早,唯有季子棠书房里此刻还掌着灯,沈灼推门进去,看见棠隐时,如临得到救兵一样,紧忙唤她:“王爷回来了,在前厅醉的很,你快来给我搭把手”。
棠隐紧随在沈灼身后,不用近身江孝珩,远远的就闻到了浓重的酒气,两个人搀着扶着将江孝珩架回前院屋里,使了全力又将江孝珩平稳的安置在床榻上。
待江孝珩平稳的躺在床榻上,棠隐才开口说道:“大人也早点回去歇息吧,这里交给奴婢就是了”。
沈灼有些不放心,怕她一个姑娘家照顾不了酒醉的汉子,反复的问她:“你一个人真的可以?”。
“大人是习武之人,照顾人自然不拿手,早些回去吧”棠隐揽下了照顾江孝珩之责,又直轰沈灼回去。
说话的功夫,棠隐从屋外端来了一盆清水,拧干了白巾替江孝珩擦拭脸颊,见状沈灼未在说话,转头就走了。
擦净脸面,又帮其换下了衣裳,只留了一身里衣,盖好锦被,转身端着脏水出屋,等到一切都收拾利索时,已经是夜半时分。
劳累了一天的季子棠从承乾宫里出来,直了直腰板,一个人拿着一盏宫灯穿越在漫长的宫内长廊里,阵阵微风吹得树枝沙沙作响。
一回到王府里,脚步不停的扎进了蘅芜苑里,更是很快就倒在了自己的床榻上。
第二日一早,季子棠是闻着声音起床的。
念奴来到季子棠寝房,极为小心的推开房门,又在床边的隔幔前轻声唤道:“姑娘,醒了吗?”念奴知道季子棠睡觉比较沉稳,又是个贪睡的主儿,自来不敢轻易打扰她的美梦。
可眼下情况紧急自然顾不得她的习性,总之语调十分轻柔,生怕惹恼了她。
季子棠听见有人叫她,忍不住翻了一个身,稍有不悦的嚷道:“再让我睡会”。
“棠隐姑娘被主子爷从前院屋里扔出来了,甚是难堪,姑娘起来去看看吧”季子棠猛然惊醒,撩开帘子,脑中一片混乱:“你刚刚说什么?”。
念奴脸上不禁一红,有些难为情的又重复了一次:“今早以冬姑娘去屋里伺候主子爷起来时候发现的......”以冬原以为躺在江孝珩身边的人是季子棠,二话没说就退身出屋,可就在出屋之时,发现地上的锦鞋不是季子棠平日里穿着的,这才知道是另有他人。
目光细细的打量,呈现在眼前的人竟然是棠隐,一时没忍住便惊神出了声音。
王嬷嬷这时已经带以冬下去领板子了,而棠隐则是被江孝珩一气之下扔出了屋,院子里围着一众的丫鬟小厮,任由王嬷嬷也不敢私自处理,只好让念奴来寻季子棠出面解决。
季子棠顾不上梳洗,随便换上了一件衣裳,迈着细碎的步子赶到前院。
棠隐只身一件里衣,跪在院子里,一旁婢女小厮指指点点的声音起起落落,大家见到季子棠前来,纷纷闭嘴不再多言。
念奴挥下人们离开:“都别看了,各自下去忙吧”又将搭在臂弯的袍子落在棠隐身上。
顺着摔打声音,季子棠一人进屋,江孝珩极为震怒,恨不得一鞭子打在那贱人身上,若不是无法言语,这会儿早已口中开骂。
屋外的哭哭啼啼声音更是让他心中怒烦,丢了一张写着:“立马让她消失”的字样扔给季子棠看。
季子棠手里握着宣纸心中忍不住替棠隐不平,皱着眉,气道:“好歹也是睡在主子爷身边的人,怎么就非得让她走”江孝珩听声,更是又气又急,恨不得立马开口朝她嚷道:“爷只想睡在身边的人是你”。
可奈何季子棠看不明白他的心。
“我先带她回去了解一下事由”季子棠寻思,怎么也算是他的女人了,这要是赶出王府,来日棠隐气急败坏随处去说,到头来还不是丢了他的面子。
季子棠出了屋,望着跪在地上的棠隐:“你先起来,别跪在这”念奴试图伸手扶棠隐,却被她撒开了手,没等季子棠反应过来,棠隐挪了身子已经跪向她季子棠。
“我知道主子爷一惯听姑娘的话,帮帮我,不然我就长跪不起”季子棠伸手拉她,一直在劝她:“你先起来,跟我回去,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棠隐跟在季子棠身后,一跨进季子棠的屋里,棠隐又伏地跪下,解释道:“昨日主子爷大醉,沈大人找我去帮忙伺候主子,我见王嬷嬷、以冬等人都睡了,就硬着头皮答应了”棠隐泣不成声,委屈连连。
“我去服侍主子爷,谁知......主子爷却一把将我抱住”说道这里,季子棠与念奴皆是羞红了脸:“若不是主子爷主动,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爬上床榻的”。
季子棠长叹一气,尽管表面上依旧保持原态,可是心中隐藏着很深的百味杂陈。
棠隐爬了几步跪到季子棠脚边,拉扯着她的裙摆:“姐姐,帮帮我,我不求名分,只要别赶我走,什么脏活累活我都能干,算我求你了”。
这一声“姐姐”打乱了季子棠的思绪,棠隐黯淡的说道:“我也是走投无路了,不然怎会入王府,你放心,只要我以后还能留在王府里,定会离前院远远的,绝对不抱有非分的念想”。
如此一来,季子棠也不得开口说道:“这事我做不了主,待我入宫请了旨意在说”季子棠唤丫鬟送棠隐回自己屋里。
辞别后,望着棠隐逐渐变小的背影,一种不详的预感如雨后春笋般在季子棠心头生根发芽。
当下年关,季子棠入宫参拜懿妃,将事情一一说来给她听,懿妃望着手中的佛珠串,听季子棠说完后,交代她:“那就留她在王府里吧,既然珩儿见她厌烦,随便找个差事给她不再近身就是”懿妃对于这等事情,早已见怪不怪。
季子棠应声,好歹棠隐也算是江孝珩睡过得女人,虽说没有名分给她,但是也不好太随意安排她,于是打发她去佛堂理经文。
希望随着时日久了,她能平心静气,不然落在谁身上遇见这事,都难以平心头愤恨,不管是谁主动,好端端的处子之身的黄花大姑娘论人糟践,哪怕是帝王子嗣,也觉得心生不衡。
府里的下人对棠隐更是嗤笑不断,被主子爷睡过,却连个通房都没混上,任谁都要指点她几分。
以冬因为办事不力挨了五个板子,原本也不至于挨打,却惊不起那么多旁人看笑话,奈何她这一嗓子,生生的把事情闹大了,由于板子是王嬷嬷命人打的,季子棠也不好插嘴,毕竟王嬷嬷是宫里的老人,又是江孝珩的乳母,自来她拿主意的事情,季子棠从不多嘴。
好在王嬷嬷派去下板子的人手道不重,随后又来季子棠处,拿了上好的药膏给她:“以冬姑娘伤势不轻,这是上好的药膏,你拿给她用”。
季子棠不解,为何王嬷嬷不自己送去。
“老奴哪里是真想让以冬姑娘挨板子,不过是做给王府里的人瞧瞧,省的日后各个犯了错,都觉得无关紧要,不好生伺候主子爷”王嬷嬷顿了顿,忧心不已的说道:“她一个姑娘也是有的受”。
季子棠托人送去时,自然没声称是王嬷嬷赏她的,以冬也全然当是季子棠心疼她,一口一个谢意不断:“谢谢季姑娘”季子棠打眼一看,细嫩的皮肤上像是乍开了花一样,血肉模糊。
只是看着都觉得疼,季子棠要她好好养伤,却不想以冬问了她一句:“我听人说棠隐被调去佛堂了,我是不是以后也不能跟在主子爷身边伺候了”。
季子棠轻轻安抚她肩膀:“放心吧,你和她不同”的确不同,不论情分,只说为人。
过了这年,皇四子江孝玢也适逢十六岁,江孝珩本是该在这个时候同他一起出宫建府,岂料他先被皇帝迁出宫。
江孝玢搬迁入府的规格自然与江孝珩不同,因着他母妃荣嫔也算得宠,对于宫中也算得上是喜事一件。
看皇帝为其选择的府址就知道,柳溪街正中间的位置,正门五间,比起江孝珩广陵王府三进三出,这“五进五出”的院落自然宽阔不少。
季子棠在王府库房里找了几样雅致的物件,让秋竹包装得体,待江孝珩到时前去贺喜送礼备用。
江孝玢被封为淮安王,府邸淮安王府,正经八百的择了好日子,才送出宫外,而王府内,宴席不断,与江孝珩当日入住广陵王府截然不同。
自此宫中除去太子,唯有养在珍嫔陈氏身边的皇八子江孝琛一个男嗣,公主则都是宝林姜氏所生,说来血脉的确不宽厚。
就连远在南江的恭王膝下都有六子及三女,皇帝这一支实在尽显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