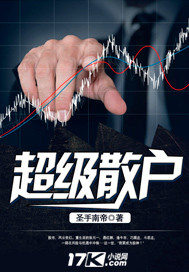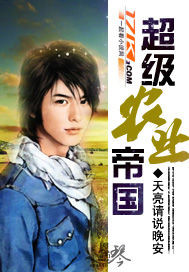等到进了高中,我可以遇见二小姐的机会就变得多了。虽然如此,可是她想说的话却不曾减少。话题内容也不再是一些懵懂的困扰,反而多是一些学术性的东西。
“就是这一题,答案都给你了,你不会都做不出来吧?”这是她少有的机会可以嘲笑我。
“这一章节应该还没有学到,就算给答案也没有用啊,并不能教会我正确的方法。”我想着法子为自己开脱,几何图形的边角问题,三角函数的已知求未知,还有铺天盖地的用那些无聊人名字命名的公式,总是容易让我怀疑自己的智商。
“那这个呢,能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是什么?”她又不知从哪弄来一张试卷,捡了一个打着红色问号的题目问我。
“要我说,老师就应该把这些东西依次准备好,我会在显微镜下观察过后,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正确的答案。”这是一道四选二的单选题,要是凭运气难度会有点大,我也没有说不会,只是换个方法搪塞过去。
“话说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说喜欢一位男生来着,后来怎么样了?”我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强行转移话题,当然这也是我一直都很感兴趣的问题。
可是当我说完话,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像没有听见我所说的,故作深沉地继续解着题目。
“没听见吗?要不我再说一次?”我并不急于戳穿她的谎言。
突然,她把脸转向我:“不许再问这个问题!不然要你好看!”满是威胁的语气,但配上那精致的面容,实在是让人生不起一丝害怕的感觉。
而且,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想要的答案。她绝对去付诸行动了,同样,结果肯定不会太过美好。
事实上,这一年年初我见到她的时候,就看出了她的改变。
她又开始留起了长发,说是长发,只不过是比之前要长得多,散开也会自然地搭在肩上。不过她总是把它们扎起来,这样,脑后就多了一个可爱的马尾。眼神之中,那种缘由害怕而装出的凌厉劲儿不复存在,开始出现了一种带着顽皮的聪颖。当然,还有那一股依旧存在的神采。
左手手腕上的花朵纹身,不知是渐渐消散了,还是她可以用袖口去遮住。我很高兴她有这样的转变的,这种感觉就像花朵盛开在氤氲的暖阳下,海鸥翱翔于广阔的碧海蓝天上,那么的让人舒畅和迷恋。
学习之余,她总会喊我走上一段路。学校位于市区的一处高地,沿途往下则是大大小小的商店。有的大门敞开,喜迎宾客,门庭若市也是常态;有的则静谧安逸,一扇木门开在隐秘的巷脚,或是繁茂的香樟密叶下,像是鼓捣药瓶的魔法小屋。
但大多数,她总会溜进一个半大的乐器行,面积不大,上下两层,却也五脏俱全。而且,楼上有一架可以免费弹奏的钢琴,她总是冲着它来的。
最初的几次,我只能听见毫无节奏的胡乱音符,杂乱的有些刺耳。可是三番两次之后,音符开始有了律动,可以穿上舞鞋跳上一小段。凭心而论,她是真的很有天赋,起码我是知道她从未学过这个,最多也就捡了几篇校刊里的世界名曲看。
更让人惊讶的是,没过多长时间,她就可以完整地弹出一章节的曲子了。再后来,店主就开始前来驱逐我们这两个‘老顾客’。若是趁他忙于生意的片刻,我俩还是可以溜上二楼,偷偷弹上一小会儿。虽然结果总是又被轰出来,但她喜欢的事,我也就无所谓了。
这样忙里偷闲的日子并不多见,尤其是到高考倒计时的后半段,也就变得更加珍贵。她跟我说,妈妈希望她可以考个教师或者医生,有保障;可是父亲希望她可以考个会计或者律师,有前途。
“你怎么想?”我问。
“我当然是想做我喜欢做的事,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对于这个问题,她倒是没什么好犹豫的。只不过有时候就是这样,虽然会觉得父母的建议会很古板,思想陈旧,但确实是很务实的方向。而我们所想要追求的喜欢去做的事,往往会伴随着不尽如意和难言的迷茫。
高考前夕,她很慎重地问我:“如果我没有考上,人生会不会就这样黯然失色,然后在平凡的日子里孤独地老去。”
“或许会吧!但是前提是你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傻瓜,对于任何的情感都没有知觉。也就是说除非你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既听不见,也不能说话,更不能思考。”很显然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每个人的人生都值得绚烂多彩。
据我所知,因为她高考的稳定发挥,最终有机会可以在几所一流大学中随意挑选。于是几乎毫不费力的,大学的时光也将到来,一切也都像预想的一样有条不紊地发展着。
之后的日子里,我就没有再见过她。直到几年后的一个午夜里,她突然来电说问我在哪,希望可以找我谈谈,话语中还带着些许的醉意。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马上就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等我到达见到她时,她正斜坐在酒吧的前台边,面前摆着几盏空了的酒杯。
然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又剪了短发,漆黑凌厉的短发遮住了整个脸颊,齐整的尾尖似刀锋一样颤颤发亮。朦胧的双眼被淡淡的醉意所笼罩,但当她看向你时,依旧能辨识出熠熠散发的神采。
我坐到她旁边,她顺手递过来一杯不知是什么颜色的酒,我将酒杯接过来,放到旁边更远处。我对这东西不怎么感冒,而她更是应该和酒八字不合。
“为什么我所爱的却最终要离我而去呢?”边说着,她就不可遏制地哭泣起来。我此刻并不能想出什么有用的建议,只好将肩膀暂时借给她。
她靠过来,靠在我肩膀上,柔弱无骨,像极了因为贪玩而走失的小猫,无依无靠地流落在街头。
后来,我就把她送了回去,也并没有说什么应该怎样做的毫无营养的话。这都是她的选择,自然也都是她的人生。我们总不能因为失去而丢失更多,相反却要因为想要什么而去追求更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只是后来听说毕业之后她去了国外,我是不担心她怎样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因为她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
……
多年以后,二小姐难得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她现在在一座风景宜人的城乡小镇,跟着一个半拉出名的乐队到处演出,赚的钱不是很多,但足够四处旅行走走停停的了,而且这样的日子倒也满心欢喜。
对于我而言,我就像是每一个感性的人背后的一点理性。当你纠结于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可能就会遇到我,有时候会是一些有用的建议,有时候也会是当做借口的搪塞。一旦你真正开始追寻,不再拘泥于麻烦的本身,我就会说一声‘再见’,然后悄悄走开。
再见,二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