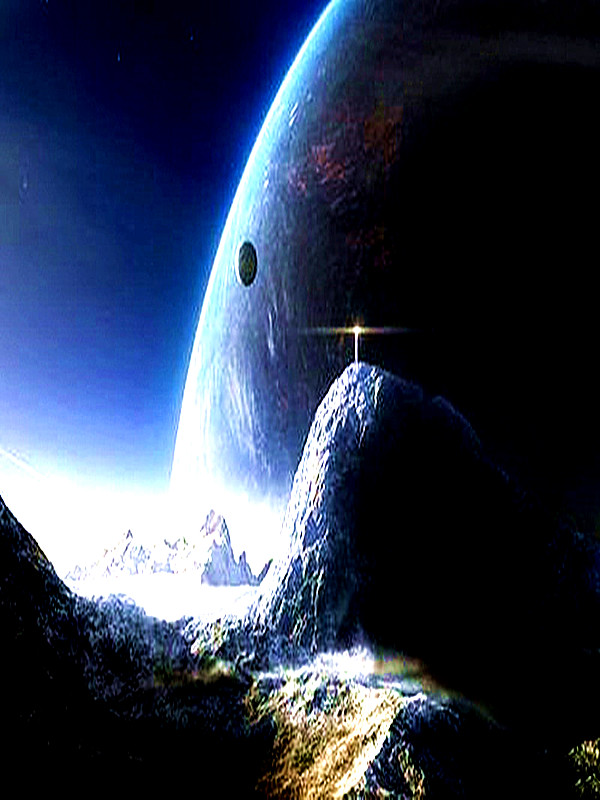大街上行人少的着实可怜,大概被寒冷的大风吹怕了,都一个一个躲进了温暖的家也说不定。我裹着风衣漫无目的地穿过一条又一条街区,这至少能让我冷静下来想想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走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一间咖啡主题酒吧横在我的面前,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停顿了一下,又看了看手腕上的“天梭”,夜光显示时间已是晚上11:20。我最终推门而入,酒吧里的人稀少的就像没有人的存在似得,我环视了好一会儿才在一个靠门口最近的桌子边上坐着。服务员似睡非睡地走上前来,眼睛像永远睁不开似地走到我面前慢慢问到:“先生,几位?喝点什么吗?”语气也显得寡淡无味。
我抬头瞥了一眼他红肿类似金鱼泡一样的眼睛,“来杯摩卡吧!”说完,不再看他。我掏出一盒烟,抽出一颗用ZIPOO打火机点燃。烟雾徐徐从我的口腔和鼻子里冒了出来。
现在我着实对烟已经有了依赖性,一天不抽一盒浑身都特别难受。烟呈环绕状在幽暗的灯光下斜射出一柱蓝色的光。
正如陌生女人所言,我的的确确像是走进了一条没有尽头的胡同里面,糊涂的让我的大脑无法正常思维起来。
咖啡不冷不热冒着汽雾。音乐也不是我惯常爱听的,尽是些国产的可以说是四流水平还没达到的歌手在现场演唱。
吧台右侧坐着一个看不出来年龄到底是二十岁还是四十岁的男歌手,他披着齐肩的长头发,头戴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光着两只胳膊,一幅西部牛仔的邋遢打扮,
在昏暗的灯光中,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待灯光全部打过去时,才能瞧见那个歌手坐在高脚椅子上有节奏地左右摇摆,他发出的颤音如同哀嚎,让人汗毛倒竖,在旁边敲击着乐器的几个助手,干枯的头发染得五颜六色,杂乱的堆成一团。
这样的场合着实让我烦躁不安。
“这哪像咖啡馆呀?整个一个酒吧嘛!瞧你挑的地方?”鄢晓雅一边将背包放在沙发上,一边埋怨到。
…….
满头大汗的鄢晓雅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呵呵。”我点点头又苦笑到,的确如此,我无话可说。
鄢晓雅从手袋里拿出一包纸巾,从里面抽出一张擦了擦额头,擦毕,又从背包里拿出一面化妆镜,面对着我,用粉扑打了打脸,感觉没有疲倦的痕迹了,才张口说到“那个女人又来信了?说来听听?不然你不会这么着急半夜三更的找我?”
“嗯。”我端起咖啡,一饮而尽。
“怎么说的呢,讲讲嘛?”鄢晓雅催促到。
我将陌生女人的第三封来信一字不落地告诉了鄢晓雅,说完,我再次点燃香烟。
“就这些?没了?”鄢晓雅惆怅地问到。
“嗯,也就这些?”我将烟灰磕在烟灰缸中,眼睛看着她。
“想必米粒儿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不然她为什么不亲自给你写信,哪怕就是生病住院也好,也总是会有清醒的时候吧?”鄢晓雅说完将眼睛移开,朝吧台的服务生打了一个手势。
那个长着一对金鱼眼的服务生又慢腾腾地走了过来,手执一份酒水单懒洋洋地看着我们,声音依然如没睡醒般地问到:“小姐喝点什么?”
“来一杯水吧?”鄢晓雅没抬头看他。
服务生睡意仍未消失一样,拖着两只像灌满铅似的大腿一步一步移动,旁人看过去都有想走上前去搀扶一把的意思。
“这样看来,米粒儿确实有如得了不治之症?”我一脸惶恐地看着鄢晓雅,她端起杯子将水一干而尽。
“不好说,反正是件很蹊跷的事情。”鄢晓雅停顿片刻,水似乎还残留在喉管里一样,鄢晓雅咳嗽了一声,又将杯子轻轻放到桌子上,接着说到“像这种状况除非到了不得已的地步,不然她干嘛不直接给你写信呀?”
“嗯。”我紧皱眉头点点头。
米粒儿到底是怎样的“不得已”我目前无法去证实,但经过鄢晓雅这么一分析,我觉得事态的发展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至少目前看来米粒儿的确过的不怎么样。但陌生女人的一句米粒儿“现在她很好!”,也让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到底谁说的更加接近事实。
出得咖啡馆,鄢晓雅执意要步行回家,想想深夜散步也是很惬意的事情,我就依从了她。
冬天的夜晚没来由地呼呼刮起了一阵大风,冷风透过毛衣直逼进来。月亮顶在头上,这样走了几步,我全身如冰块似的冻的僵硬起来。鄢晓雅似乎也感受到了寒流袭来,冷得牙齿也“得得得”发出声响。
“还是打车吧?”我征求她的意见。
鄢晓雅抱紧双臂颤抖地站在风中,或许实在是受不了这般咧咧的寒风,才不得以点了点头。
把鄢晓雅送到家后,我也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公寓。
回到公寓,进浴室洗了个热水澡,随后将衣服一一放进洗衣机里,然后将晚上吃剩的饭菜倒入垃圾桶,如此收拾一番人也累的够呛,一直到凌晨2:00才稍微缓过气来,接着倒头便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