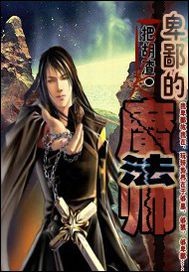“她和她舅舅吵架的那些话,我可是全都记着,那些话,我想想就觉得可怕,更何况我爹,那是已快不行了,素素这丫头偏偏说得出那些话来!我每天听着人家说她大不敬,大不孝,心里那个难受,就想每天打她一顿!”陈来弟,说着说着,这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伏在桌上,拍着桌子哭喊:“我爹啊,本来可以寿终正寝的。”
罗宁照对她这些话已觉得心烦了,也不想安慰她,就对她说实话,让她清醒些:“来弟,你可别忘了,素素当时是在向陈图浩宣泄心里的怒气,是在和陈图浩吵架。这个认,有资格做舅舅吗?他听信道士之言,对我们新元动了杀心。如果不是他的儿子死了,他的杀心不会消除。如果不是素素将新元藏起来,我还真怕新元会遭他毒手,到时,我们罗家,怎么活下去?”
罗宁照用拳头敲着桌面,表达着自己的愤怒,也震动了桌子,敲醒了陈来弟。
他还说了一句,被所有人都漠视掉的事:“你父亲死不瞑目,是因为素素与陈图浩吵架,陈图浩的滔天恶心,也是你爹死不瞑目的原因。陈图浩他逃不了责任!”
陈来弟没有大哭大喊了,坐好了,垂着背,摸着泪,悲戚地说:“是啊,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弟弟呢?居然想对我们新元下毒手。还好,苍天有眼,没让他们甥舅两成为生死冤家。”
陈来弟又双手合十,感谢上苍。
罗宁照觉得妻子还未完全觉醒,就转过脸,喝口热水,说道:“就你想得好。新元虽没事,但他们的甥舅之情也没有了,但是我们新元懂事,有礼貌,对那个陈图浩还是以礼相待,称呼一声‘舅舅’。要是我,可没那么好,我会比素素骂地还要厉害!”
罗宁照想抓碎那个杯子,但抓不碎,就往地上一扔,他的表情和那个碎掉的杯子一样可怕。
陈来弟第一次看到常年抽烟咳嗽的懦弱丈夫这样生气,多年前的那个汉子,回到眼前了。陈来弟被吓到了,不敢多说什么。
罗素素听到他们刚才的对话,心里也回忆了很多,觉得自己确有不是,但这都是陈图浩错在先,没想到父亲的想法和自己一样。
她听到摔杯子的声音,立刻去爹娘的房间,然后拿来扫帚和簸箕,将碎片扫起来,低声说:“爹,娘,等下新元从学堂回来,别再这么吵了。他过了两个多月担惊受怕的日子,让他开心些吧。”
“素素比你明理多了,知道怎样找过这个家,照顾爹娘,照顾新元。”罗定照说道:“素素,别那么不开心了,没什么,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外公的过世,不是你的错,不要老是把责任放在自己心上。如果不是你那个没人性的舅舅做出这样不齿的事,我看,你外公,能多活几年。”
“爹说得让我心里好受些了。谢谢爹能理解我,那次在外公病床前,和舅舅大吵,我真的不是有心的。”罗素素终于有机会和生气的爹娘说话了。
而陈来弟还是那么不肯放过她,不过她看到丈夫这么气愤,一而不敢再大哭闹,就继续摸着泪说:“新元走丢的第一天,就去找你,你把他藏起来,也不告诉我们。害得我整日躺在床上,要死要活的,你知道我有多难受?”
“娘,那是我为了新元着想,知道他藏身之处的人,越少越好。你知道,那可是在保新元的命啊。”罗素素坐在母亲旁边,为她擦泪。
陈来弟让她坐远点。
罗宁照对这件事,也替罗素素说话:“一开始,我也对素素生气,为什么不把新元的藏身之处告诉我们。现在想想,素素做得对,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陈图浩想取新元的性命,如果知道了,反而不好。来弟,要是你知道了,还不第一个跑到陈图浩家里去报告,到时,陈图浩又将新元抓回,新元要逃出陈家就没那么容易了。”
陈来弟无话可说了:自己的弟弟想杀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气死了自己的父亲,这都是什么事啊?该怪谁呢?
罗宁照抽起了烟,思考着以后的日子:“我们罗家就只欠他陈图浩一些碎银,存钱还他就是。他陈图浩想出那样恶毒的主意,想对我的儿子动手,从此以后,我罗家与他陈图浩就没什么亲情可言了。但是礼节上的事,我们会做到。来弟,我只能这么说,我恨陈图浩,别想让我再像以前那样对他毕恭毕敬。”
陈来弟无法劝说丈夫,毕竟这次,陈图浩是犯了滔天大错,也多亏素素想法保护了新元,才没让这错付诸实际,否则,两家真要决裂了。现在,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不错了,自己也别再对女儿使脸色了,她心里也苦啊。
整个冬天,罗家的气氛都不是很好。尽管罗素素姐弟一直在饭桌上说些开心的话,可罗氏夫妇就是无法开心起来。
罗素素也无法在他们面前说出自己的苦:爹娘,你们开心些好吗?陈图浩已在外公的病床前发了毒誓,不再对新元动杀心,你们别再不开心了。
毕竟隔了一辈,罗素素无法完全理解爹娘。
现在的她,只有在钟亦得面前才能发发小脾气,耍耍乖了:“去湖畔吹吹寒风也不错。腊月的湖畔,也是一番景色。”
“你怎么只想到湖畔?我们不是还有两个朋友吗?正需要我们的关照呢。”钟亦得没有直说,想让她自己想起来。
罗素素与他心照不宣,但还是一起说出来了:“去郑婆婆家里。”
路上,罗素素还是念着她外公的死:“我现在成了蔷薇村乃至鄱阳县的罪人了,都说我外公是被我气死的,死不瞑目。”
钟亦得早想到她还会为此事而自责,也准备了安慰的话:“素素,你外公过世那天,你那些亲戚们都确定他在世不久了。却把这罪名扣在你头上,太不公平了。实际是你昏了头,与你舅舅吵架,才让你外公不闭眼。他陈图浩敢说,他父亲的去世,与他一点关系没有吗?如果能让新元多陪着你外公几天,你外公也不会那么快走了。”
“话是这么说,可是,亦得,你知道吗?我常会在梦中惊醒,看到外公临死前死盯着我,不肯闭眼的那双眼睛,似乎要带我走,又似乎要带陈图浩走。我都变得神经兮兮了,晚上一点震动就会让我心惊肉跳。”罗素素的这些恐惧,不愿对伤心的爹娘说,以免增加他们的伤痛,只有对钟亦得说了。
钟亦得一个小小的玩笑,就让她不害怕了:“素素,如果晚上我在你身边,你就不会害怕了,是吗?”
“流氓!”罗素素加快了脚步。但真的,从此以后,罗素素睡前,都会想着钟亦得的样子,这样就不会害怕那些鬼魂了,梦里也不会有她外公死去时,那双怨恨的双眼了。
他们到了山坡上,郑婆婆家里完全没有外界的烦恼,相反,里面是让他们捧腹大笑的场面。
江女笑坐在躺椅上,脚还未痊愈,也不能走路。钱典在给她按摩双腿,装着姑娘的声音说道:“女笑,男女授受不亲,所以钱典派了他的妹妹钱姑娘来给你做丫环。大夫说江小姐久不走路,这双腿怕会麻痹,所以要每日按摩,江小姐,你看奴婢按摩地还好吗?”
江女笑竖起了大拇指,忍不住笑。
这个钱典,也偏他想得出来:头发梳成了丫环装,衣服换成了彩虹色,脸上画的红扑扑的,还不时扭动他的腰,真像个姑娘了,但是:丑的要命。
罗素素和钟亦得笑完之后,就下命令:“丫环,还不赶快倒茶送水。”
钱典对他们则恢复了男人的样子:“自己倒茶去,在厨房。”然后对女笑嬉皮笑脸。
钟亦得拉着钱典出去谈话。素素就和女笑聊了起来:“没想到在和大雪天,这山坡上,也是每日欢笑,从不寂寞吧?告诉我,每天有什么开心事,跟我分享一下。”
女笑蒙住了脸,罗素素去拉开她的手:“在我面前还装害羞,说嘛。我和亦得有什么事,从不瞒你。”
女笑就将这段日子的话笼统地比划着告诉罗素素“他对我照顾地无微不至,情愿做小丑,做各种动物,唱各种各样的歌曲给我听,还教会我好多字。在郑婆婆家里,我没有一天是不开心的。”
罗素素就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女笑,比之三定哥,钱典待你如何?”
江女笑是个犹豫的姑娘,她想了很久,其实钱典为她做的,远超过了赵三定,但她想了很久,才说“钱典对我,更好”。
“那你就找到这辈子的归宿了,是吗?”罗素素充满了希望,希望成就一对有情人。
可女笑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罗素素已看到她偷偷的笑了:已定下来了,不用多想。
但罗素素忽然想到许伟真,那个与钱典有了错误的一夜之缘的死丫头,现在都怀孕几个月了,那个孩子该怎么办呢?
罗素素看着屋外,不让女笑看到自己忧虑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