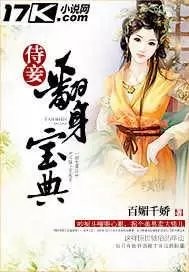江女笑向后退了,害怕了,钱典也怕:“大夫,这刺拔出来后,她能恢复吗?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顾得好当然能恢复。照顾地不好,顶多就是瘸了,也还能干活。”大夫是外伤大夫,说话也粗。
这让江女笑更害怕了,不肯拔刺,钱典在一边劝她:“女笑,你不想变成瘸子是吗?你答应过我,以后只要我说一句,你就会跳舞给我看。这样怎么跳舞?听话,忍着,就一会痛,来,咬着我的手。”
江女笑咬着钱典的手,大夫看着想说什么,但还是趁此先拔刺,他说:“本来应该从脚底拔刺。可这刺是倒刺,要从脚背拔出,会更痛,姑娘你忍住了。”
这大夫也不会说句好听的话,让患者镇定一下,这下,江女笑又不愿拔刺了。
钱典抓住她的双手,让素素抓住她的另一只脚,对女笑说:“女笑,今日我不会依着你。你要听话,听我的话,听大夫的话,为了这一生,不能落下个瘸子的残疾。快,要紧我的手,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拔刺,就早点脱离痛苦。”
江女笑照他所说。
大夫手劲也狠,一手按着脚,一手猛地就拔了刺,江女笑还来不及哭,就晕了过去。
“大夫,你看。”钱典指着女笑说。
大夫说:“她是痛晕过去了。那个丫头,给她抹点生姜水在鼻子上,按摩一下太阳穴。”
“好,我这就去。”罗素素答应着。
大夫又对钱典说:“你这手,被咬得那么深,去包扎一下吧。”
“我皮粗肉厚,不要紧,大夫,女笑她醒来之后,还会觉得痛吗?要是还那么痛,就让她多睡一会吧。”钱典一心念着江女笑。
大夫是个脾气粗狂的人:“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她要痊愈就必须忍着这痛,况且,刺拔出来了,也没那么痛了。”
“哦,是这样,那就麻烦大夫了。”钱典对大夫点头哈腰。
涂药之际,江女笑慢慢醒了,钱典连忙过去搂着她:“女笑,还疼吗?要是疼,就再咬我。可怜的女笑,疼的时候,都无法说出来,不懂手语的人都不知你在说什么。也不知你刚从山上,是怎么爬下来的。”
江女笑忍着痛,做着手势“没那么疼了,你别担心”。
“可是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很疼。怎样才能让我为你担当掉这疼呢?”钱典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像样了。
罗素素一直说着“钱典,你注意些”。
可他已听不进去了。
还是大夫的话有用:“痊愈之前不能下地。还有就是,身边照顾的人,不要哭丧着脸,对她多笑笑,她才会开心,不会感觉难受。记住要让她保持心情舒畅。”
这下,钱典立刻摸干了眼泪:“大夫,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发挥了他哄人的长项,让江女笑在疼痛中哭笑不得。
江女笑午睡时,罗素素和钱典去给女笑的鸡鸭猪喂食。
罗素素问钱典:“你打算一直住在女笑家里,陪她疗伤,帮她照顾鸡鸭猪吗?”
“那是当然,要不然女笑的脚不能痊愈,瘸了怎么办?这么一个好姑娘,喉咙哑了,我可不能让她再有什么缺憾了。”钱典觉得那是他的责任,说得义无反顾。
此刻他沉浸在爱中,无法全面考虑问题,罗素素帮他想到了:“钱典,你今日可看到许伟真缠着你不放的样子,还有许家,我舅舅对你的态度,都是让你非娶许伟真不可。你父亲的态度也不明朗,不过我看他是肯定不会让你娶女笑的。所以现在女笑很危险。我猜他们肯定在找你,若是知道你,发现你对女笑情深意重,那女笑怎么办?”
“对啊,我的心全放在女笑身上了,把那些人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行,这里不安全。”钱典想着,该转移地点了。
罗素素继续提醒他:“他们还以为我是你的意中人,骂了我一顿。我辩解之后,他们还是骂我。好在我是他们的亲戚,才没有什么大事,但女笑就不同了。对了,她们肯定回来蔷薇村找我,到时,可能会找到女笑。”
“去郑婆婆家!”钱典态度坚决:“晚上,待无人看见时,我带女笑去郑婆婆家养伤,住在那里,一直到女笑的伤完全好为止。”
“这是个办法,不过要立刻才好。”罗素素也同意了。
然后她去对醒来的江女笑说:“你家的鸡鸭猪很多,而且这里潮湿,怕你的伤发炎,那就更难痊愈。我和钱典都觉得让你去郑婆婆家疗伤比较好。”
江女笑答应了,可她担心这些鸡鸭猪。
罗素素着急了:“现在都快立冬了,它们都可以拿去卖了。我会帮你卖掉它们。然后明年你的伤好了,就再去买些鸡仔,鸭仔,猪仔来养,那样不更好?”
江女笑觉得也对。
于是,晚上了,快戌时了,钱典出去看看外面,发现已无人迹,就进来背起女笑。罗素素已经帮女笑收拾好衣物等用品。他们悄悄地走着,不敢出声。做好事弄得像做贼一样。
但还是出现一个“人迹”,不过完全不用担心,那是来找钱典算账的钟亦得。
钱典看钟亦得脾气不小,就低声说:“亦得,你看女笑都这样了,求你小声点,我会向你解释的。”
钟亦得就暂时忍住了火。罗素素慢他们一步,把女笑受重伤的事告诉钟亦得,还有钱典的错误是不得已,也是因钟亦得而起。
这下钟亦得开始慢慢原谅钱典了:错误的根本是许伟真,而莞香斋的酒,还有我,是钱典犯错的导火线。那么娘对钱典的看法有误,我回去后就向她解释,不能放弃钱典这个有情有义的朋友。
到了郑婆婆家,钱典已是满头大汗。
他们敲开郑婆婆家的门,这大晚上的,把老人家吓了一跳。
不过,看到是这几个熟悉的面孔,郑婆婆就开心了:自己这些天有人说话了。
安排好江女笑和郑婆婆睡一间,钱典一人睡一间。离开前,罗素素安慰女笑:“我和亦得会常来的,钱典会每天在这里守着你,你不会孤单,会很快好起来的。”
罗素素和钟亦得暂时离开了。
“又是一件麻烦事。钱典麻烦了,我也麻烦了。许家和钱家找不到钱典,就会来找我。要是我不在家,肯定会像上次找新元那样,把我家摔个乱糟糟的。那我这些天就不能去教堂学习了,必须守着家里,不能让那些人进我家半步。”罗素素愁眉苦脸。
钟亦得想到个办法:“老办法。既然钱典要长期‘失踪’,他们总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你身上啊。钱典时成人,他逃走,也不能怪你。我就用上次的方法,让钱典写一封信,盖上邮戳,扔到钱家门口。我也不会出面,免得遭臭骂。”
“嗯,也就这个办法了。”罗素素和钟亦得叹口气,各自回家:钱典和女笑的路,恐怕很难走啊。
钟亦得回到家,向母亲叙述了钱典和江女笑的爱情,这样,钱典的至死不屈,对女笑的忠贞,都让钟惋心里放下了对钱典的愤怒,她恢复了平素的温婉:“亦得,你别跪着了,起来。娘今日是太冲动了,只是因为这莞香斋是娘为你爹而建,是娘心中与你爹共享的圣地,容不得污渍,所以才会那么生气。现在想想,那都是许家姑娘的错,想用这种方法强嫁给你,让你对她负责,我都不好再说下去。亦得,这个钱典,也是个钟情的人,娘收回今日的话,你们愿意做朋友就继续做朋友吧。还有那个女笑姑娘,也是个不错的姑娘,就是命苦了些。”
钟惋说完,就想去休息了,她有些伤感,因为今日一天都想到莞香斋,想到钟亦得的父亲。
而钟亦得趁此,就想问父亲的事:“娘,你刚才说到爹了,是不是爹和这莞香有什么关系?”
“亦得,去休息吧。娘不想说了,娘累了。”钟惋实际是伤心了。
钟亦得再一次失望:每次问道关于父亲的事,娘总是回避,我现在都成年了,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到底我爹是谁,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让娘如此瞒着我呢?
钟亦得带着这些疑问入睡,这也不是第一次,他常这样想着,就睡了。
几日后,傍晚,钟亦得和罗素素忙完各自的事,就去郑婆婆家看望江女笑。
看见后,又让罗素素嫉妒了。
钱典把江女笑当皇后一样供着:一会儿背着跑,一会儿抱着转,一会儿坐在凳子上唱歌给她听,一会儿跳一段“贵妃醉酒”逗她开心,还手把手教她练字。
钟亦得看罗素素的表情有变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就先预防:“素素,你别羡慕女笑,刚才钱典对她的好,我都会,我会照着他做的,那样对你。你可别眼红女笑啊。”
罗素素烦他:“算了,你还要刻意去学钱典怎样对人家好,那就不用学了,继续做以前的亦得也好啊。刻意学来的,有什么意思?我不会因这些事发脾气了。你看女笑都伤成这样了,我还眼红她什么?”
钟亦得听到这才放下心来,跟着罗素素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