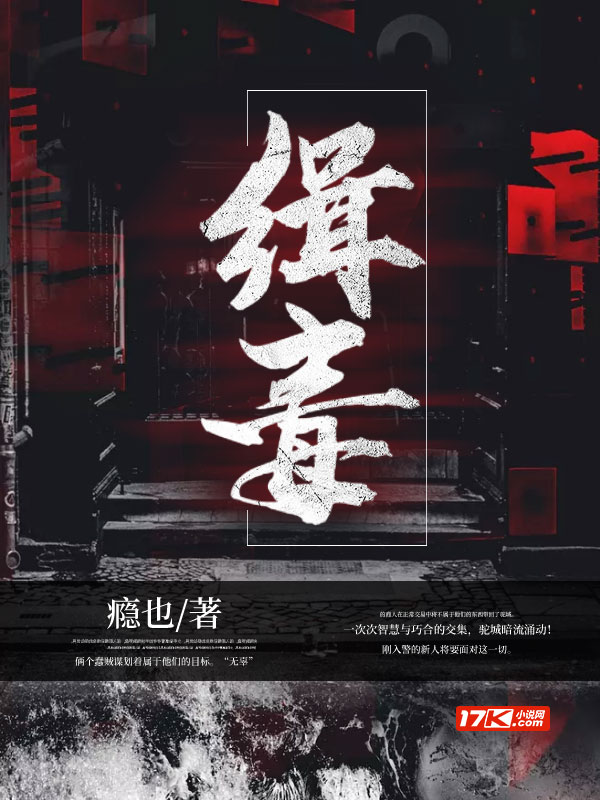“我只是猜测。”萧邦说,“我记得在地道里,张船长说过一句‘我这条瘸腿,就是拜神刀社所赐’!那么,张船长在马六甲海峡遭遇了海盗,实际上这海盗就是神刀社,或与之密切相关;费教授又加入了神刀社,而你与费教授却成了朋友。联系种种因由,我就作了以上猜测。”
“唉——”张耳东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接着说道:“事已至此,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将事情原委告诉你们吧。”他低头喝了一口水,目露茫然之色,开始讲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油轮公司当船长。你们也知道,马六甲海峡是黄金水道,是通往东亚的必经之路。但在九十年代初期,这条长约800公里的航道是相对安宁的,极少有商船被劫持。或许是我运气不好吧,当了近二十年的船长,还是第一次碰到海盗。这些海盗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分乘两只小船,两船之间用粗绳相连。我们的船往前行驶,船头顶住了绳子,两只小船就贴到油船两侧。海盗向甲板抛出铁爪,顺着绳子爬上甲板。当时我正在驾驶台,两名海盗用枪将我们控制,迅速把我劫持到小船上,蒙了黑布,带到一处民居,然后开出八万美金的价格,要求船公司交赎金。
“八万美金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我们的船公司是国营的,考虑到政治影响,事情就难办了。公司党委开了几次会,意见极不统一。反正被劫持的就我一人,船舶本身无损,便决定隐瞒此事,决不向海盗屈服。这下可苦了我了。那些海盗见我方不出赎金,便打断了我的腿,将照片寄到船公司。然而船公司不为所动,只是给了我老婆一笔钱,就说我因公殉职了……在民居肮脏的地下室,我被整整关押了三个月,伤口都化脓了……最后,海盗决定将我处死……”
说到这里,张耳东嘴唇颤抖,又喝了口水。
萧邦和一姝静静听着,没有插话。
“正在这个当口,费教授突然出现了。那时我已经很虚弱,处于半昏迷状态,是费教授将我带到宾馆,让我好生休养。后来我才知道,费教授个人出了两万美金,交给了海盗。海盗们拿不到赎金,本就想杀了我,但经过费教授一番游说,他们觉得两万美金也比什么都没有强,就把我放了。
“也许你们会问,这费教授怎么会来得这么巧?他又怎么知道我被劫持了?刚才小萧也说了,费教授是神刀社的成员,而这伙海盗,背后的力量实际上就是神刀社,当然比较好通融。但在当时,费教授并没有告诉我这些。
“我回国几年后,迫于生计,干上了雕刻这一行,费教授也常常资助我。后来随着我们交往日深,费教授在一次酒后才向我说明原委。我当时心情极其复杂,因为是海盗毁了我的一生,但我的救命恩人居然与海盗有瓜葛!
“费教授叹息了几声,才将原委和盘托出。他对我说,他加入这个组织,目的是寻找林道乾宝藏,并非出自真心;而救我,亦非图什么回报,只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他还说,救我这件事,是他个人行为,与神刀社无关。
“当时我是怎么也想不通。但后来我通过接触,才发现费教授是一位爱国人士。因为痴迷于学问,他不得不出此下策——打入神刀社以求获取林道乾宝藏线索。他常常跟我讲,寻找宝藏是他毕生的愿望。如果找到林道乾宝藏,他会全部捐给国家,只求能让他参与考古和研究……未曾想,教授壮志未酬,竟遭毒手。唉,真是苍天无眼啊!”
张耳东讲完,又喝了口水。
房间里陷入沉默。
突然,萧邦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骂道:“柳静茹这个贱人!”
桌上的茶杯晃了一下,有茶水溅出。张耳东似乎吓了一跳,脸色微变:“小萧,你怎么骂人?”
一姝也觉得蹊跷。虽然她接触萧邦时间不长,但交谈甚多,从未见他出过粗口。
“难道柳静茹不该骂?”萧邦哼了一声,“教授被她杀了,我与一姝也差点遇害,当真是可恨之极!”
“是可恨。”张耳东附和道,“不过现在她已逃逸,骂她又有何用?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老船长认为该怎么办?”萧邦双手一摊,“研究林道乾宝藏最深的费教授死了,又冒出来一个神刀社,这宝藏还怎么找?”
张耳东沉吟了一下,说道:“教授死了,宝藏仍在。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藏宝图在哪里?”
一姝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张耳东说了半天,原来是为了这个而来。他既然与费教授过从甚密,简直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萧邦却说:“一姝,你将宝图和漆盒拿出来吧。”
一姝一愣。但她对萧邦绝对放心,便从怀中取出二物,放在桌上。
张耳东看了一眼,叹了口气道:“小萧,难得你对我如此信任。其实,你心中还有几个问题没有问我,只是碍于情面,不好开口。”
“老船长不想说的话,我又何必问?况且,我对老船长一直很敬重。”萧邦真诚地说,“萧邦不才,但心中所敬之人,一是爱国之人,二是饱学之士,三是仁义君子,四是热血男儿。老船长虽年过花甲,不幸残疾,但潜心学问,壮心不已,是我敬重之人。刚才,又救了我和一姝和性命,萧邦是知道好歹的人,怎么能不信任老船长?”
“萧兄弟别说了,再说下去,老头子无地自容!”张耳东一摆手,对萧邦改了称呼。“既然你推心置腹,如若我再有隐瞒,真算是白活一世了。你不问,我也要回答:其实费教授和我,都知道你是警方人员,是受命调查林道乾宝藏一事;当然我们也知道,一姝姑娘就是林道乾的后人,且身负道乾公藏宝线索。”
虽然一姝早就疑心张耳东,但他这么一坦白,还是令她暗吃一惊。
“谢谢张船长的坦白。能与张船长推心置腹,萧邦深感荣幸。”萧邦十指交扣,两肘撑于桌上,托住了下巴,以便身子前倾。“那么现在看来,昨晚张船长指点我们去泉州珍木山,亦是教授的意思了?”
“是的。”张耳东叹了口气,“此事头绪繁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看这样吧,萧兄弟你问,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多谢老船长。”萧邦站起身来,为他加了杯热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首先,我想知道,费教授前天下午在他的院子里给我们讲了林道乾的故事,还顺便提到了‘珍木山’;而昨夜到贵处拜访,老船长又从一姝拓印的纸上破解出‘海上有珍木’几个关键字。我想知道,费教授在给我们讲林道乾宝藏时,并未看到过张九龄的诗,何以会暗示我们珍木山的存在?”
“萧兄弟,珍木山的确存在。”张耳东正色道,“费教授先前根本不知道除了藏宝图外还有一个漆盒的事情。前天晚上,大概十一点钟,教授突然打电话给我,声音里充满惊喜。他说:‘老张,我又有了新的发现。看来,我们以前谈过的珍木山真的存在,林道乾的宝藏就在珍木山!’我当时没明白过来,便连忙追问。教授说,从美国来的林道乾后人,也就是一姝,带了一个漆盒来,上面阴刻了张九龄的《感遇》。我当时是兴奋极了,要连夜过来一观。但费教授却说,现在刚有了一点眉目,等天明后再约我一同研究。我正要挂电话,他突然问我最近跟萧邦联系过没有。我说,昨天刚给萧邦打过电话。他便对我说,要设法将珍木山就在福建泉州的消息告诉萧邦和林一姝。”
“是费教授要你告诉我们的?”萧邦奇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萧兄弟,说来你也许不信,教授深知他和我毕竟已年迈,就算找到林道乾宝藏,对我们这些半截都埋在土里的人,并无多大用处。他是著名学者,无非是想得到郑和资料,为国家进军海洋略尽绵薄之力罢了。这里再补充一点,费教授具有双重身份,他利用神刀社的眼线,了解到你将介入道乾公宝藏调查,但又不好明说。你想想,他花了半个下午给你讲此事的来龙去脉,哪里是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分明是要帮你和一姝完成使命呀。”
“张船长所言极是。”萧邦点点头,“费教授在讲述那段海盗历史时,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让我热血沸腾,好生敬仰。可是,萧邦还有一个疑问:为何昨天下午我们碰到他的外甥阮凌宵时,阮先生拿出手机录音,内容是一句话:凌宵,注意萧邦和林一姝。如果教授真的想与我们沟通,为何要对他的外甥讲这句话?”
“有这种事?”张耳东挠了挠蓬乱的头发,“应该不会呀。教授在电话里说得明白,要我设法告诉你们珍木山的事,他怎么会给阮凌宵说这种话?”
一姝心想,是萧邦问你,还是你问萧邦?但她见萧邦没有说话,也不便开口。
张耳东掏出了哈德门烟,点了一根,狠狠地吸了几口。突然,他一拍桌子,说道:“阮凌宵放这段录音时,是不是只有这一句?”
萧邦点头。
“他放了录音后有什么说法?”老人继续问。
“他放录音,意在说明我们与教授的死有关。”萧邦说,“据阮凌宵说,教授被杀当晚一点多钟,也就是教授临死前三个小时左右,给他打过电话。内容他没说,只是提到教授怀疑我和一姝动机不良。此外,阮凌宵还说要将手机录音提交警方作为证据。”
“原来是这样。”张耳东舒了口气,“依我看,这是阮凌宵在吓唬你们。”
“何以见得?”一姝问。
“因为‘凌宵,注意萧邦和林一姝’这句话,并不说明教授对你们有何成见,是比较中性的。教授在十一点左右打电话给我,要我设法让你们相信珍木山的存在,而在两个小时后让外甥注意你们,再在三个小时后被柳静茹杀害。联系起前因后果,我觉得教授有可能是让阮凌宵注意你们的动向,以便在你们找到珍木山后,好让他第一时间知晓。”
“老船长,如果按您所说,费教授既然知道了珍木山,何必要让我们去找?”一姝忍不住问道,“教授和你,还有阮凌宵和柳静茹,以及教授以前的手下,都可以完成找到珍木山的任务,有必要拱手让外人去找吗?”
张耳东一怔,随即平静地反问:“那么请问一姝姑娘:珍木山在哪里?”
一姝一时语塞。
萧邦摆了摆手,打了个圆场:“一姝,老船长的话是有道理的。费教授和老船长,甚至柳静茹和阮凌宵,都知道道乾公藏宝之地就在珍木山,而且在泉州的珍木山,但谁也不知道泉州海域哪个小岛才是珍木山。进一步说,就算找到了珍木山,那宝藏藏在山上什么地方?怎么才能发现?发现后又怎么发掘?如何善后?都极其复杂。因此,教授想让我和你先行找到珍木山,将范围缩小,也在情理之中。”
一姝心里顿时不快。这个萧邦,居然帮这个死老头说话!然而她对萧邦的信任就如同相信自己一样,只得嘟哝了一句:“看来费教授是将困难留给别人,将希望留给自己。”
张耳东干笑了一声,又喝了口水,道:“无论怎么说,费教授突然死亡,对寻宝都造成了极大障碍。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有两点:一是费教授被杀前,到底有什么新的发现?二是一姝带来的漆盒和藏宝图,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费教授的新发现,普天之下,可能只有柳静茹一个人知道。”萧邦略一沉吟,“我被困在暗室时,柳静茹说费教授背叛了神刀社,又糟蹋小姑娘,所以才动手杀了他。这两个理由看似充分,实际上只有鬼才会相信。因为教授背叛组织决不是在被杀的当晚,糟蹋小姑娘更是由来已久。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当柳静茹得知教授有了新的发现时,迅速掌握了这个秘密,而留着费教授已无用处,便杀了他。”
“萧兄弟之言有理。”张耳东重重地点了一下头,看了一眼桌上的藏宝图和漆盒,若有所思地说:“可是,这两件林家的东西,柳静茹为何没带走?”
“她没有机会。”一姝有些自得地说,“她本来以为,我被控制,对萧大哥是投鼠忌器,要么答应她的条件,要么杀我们灭口。没想到,她会装,我也会装,而且装得决不比她差。”
“原来你也是个鬼精灵!”张耳东哈哈大笑,“幸亏是萧兄弟与你搭档。换作别人,恐怕要吃大亏。”
“我才不与别人搭档呢。”一姝作了个鬼脸。
气氛似乎轻松下来。
萧邦眉头皱起了“川”字。他没理会张林二人的调侃。他在沉思。
“萧兄弟还有什么要问?”张耳东也严肃起来。
“没有了。”萧邦将桌上的藏宝图和漆盒往他面前一推,郑重地说:“老船长,萧邦才疏学浅,对这两样东西,终究是琢磨不透。因此,我恳请老船长将它们带回去好好研究。一旦有什么发现,请通知我。我和一姝,听候你的差遣。”
张耳东一下站了起来,往后退了一步,连连摆手:“萧兄弟别误会,我老头子决无觊觎宝藏的意思。这万万使不得。”
“可是,我还想请老船长与我们合作呢。”萧邦真诚地说,“老船长与费教授,是道义之交;而老船长与我,也是道义之交。道义之交,道为首,义为末。既然道乾公宝藏不限于财宝,更有利国之器,我辈当拼力寻觅,以防落入宵小之手,这是道;再说义,老船长作为费教授至交,诚然无意宝藏,也该为好友报仇雪恨吧?”
“唉——”张耳东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萧兄弟,你我认识已非一日,应该知道,像我这样的残废,又年老力衰,不中用了。但为了道义,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老张都在所不惜。今天,咱们以茶代酒,我在这里立誓:只要萧兄弟差遣,我老张万死不辞!”说罢,双手捧起茶杯,往前一送。
萧邦赶忙端杯,与之相碰。二人各喝了一口茶水。
萧邦放下茶杯,扭头对一姝说道:“既然费教授与张船长都有意让我们去泉州,我看咱们即刻动身吧。”说罢站起身来。
“这……萧兄弟考虑清楚再走。”张耳东的大手往下一招,示意萧邦坐下,“你们此去,怎么找珍木山?”
“到了泉州再想办法吧。”萧邦没有坐下,轻拉了一姝一把,往门外走去。
张耳东拾起藏宝图和漆盒,追了出来,将其塞进萧邦怀里:“萧兄弟,这两件东西,我老头子是万万不能收。说得好听点,我老头子不敢私藏林家的东西;说得难听点,我还想多活两年。”
萧邦只得收下。
告别了张耳东,二人出得门来,穿过小院。一抬眼,就看到了费教授的院子。
两个院子只有一墙之隔。
一姝心想,萧邦可能会在甩开张耳东后,再设法回费家小院看看。然而萧邦拿出电话,致电航空公司。正好有一班北京至泉州的航班,起飞时间是10:40。萧邦看看表,正是8:45。他连行李都不带,领着一姝奔到街口,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首都机场。
下午一点半钟,二人走出泉州晋江机场。
让二人没想到的是,在接站处,居然有一位妙龄女郎手托一块一米见方的纸牌,上面写着两个醒目的名字:萧邦林一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