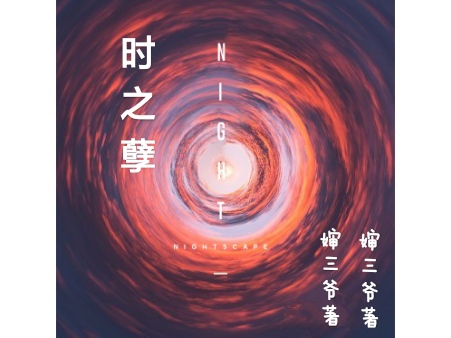每天早晨,我和彩妮匆匆来到胡同口吃上两根油条便背着画夹出发了,穿过北京大学校园,坐320来到工会大楼,再乘地铁来到天安门广场。
当我和彩妮坐在天安门广场的水泥地上,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漫天漫地地扑面而来。一切景物都那般美好。
我瞅着身旁的彩妮说真感谢这里,要不咱们还不会相识呢。
彩妮笑着道还记得那天你的样子么,真可笑。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笑,反正彩妮此时坐在我的身边,我感到踏实。
在没有顾客的时候,我便给彩妮画像。给彩妮画像我不厌其烦,画了一张又一张,我给彩妮画像时,彩妮不望我,望着远处的什么地方,这时的彩妮,目光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清纯得似流淌在我面前的两脉溪水。有时,我忘记了手里的动作,一直望着她的眼睛,恍似我已经顺着她的目光走进了她的心灵。这时我觉得生活灿烂美好。当她发现我在呆定地望她时,她收回那憧憬希望的目光,娇嗔地望着我道:干嘛呢你?我恍然醒悟过来,埋头认真地为她画像。彩妮的像一张又一张平铺在地上,游人们都驻足观望,评头品足。我也不知道给彩妮画像时手里的笔为什么那么流畅,心里充满了自信。我从来没有把人的神态抓得这么准,简直像极了,看得彩妮也一遍遍地说:我真的这么漂亮么?我笑而不答。
彩妮无疑成了我的活广告,顾客们纷纷络绎不绝地来找我画像,彩妮负责照顾顾客,有时身旁会聚起挺多等着画像的,彩妮怕他们寂寞便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北京的名胜古迹,还热情地为他们指出坐车路线。
那些日子,我的生意不错,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几十元钱的收入了。那时我们就收起画夹胜利而归。回到圆明园18号那间小房里。
彩妮住在我这里后,我便把那张床让给了她。我在屋脚用木板搭了一张床。第一天,我这么安顿好了之后。心里隐隐的有些不安,我冲彩妮解释,等日后有点积蓄了,给你另租一间。
彩妮不说话,有些惆怅和为难地看着我。
我又说你放心,我是个君子。
临睡前,我想把几幅画好的画搭在我们中间的空地上,彩妮说你不是君子么,干嘛要这样?
我望着那几幅画,想想也是,便又把它们放回到原处。我关掉灯之后说:脱衣睡觉吧。
我听见彩妮好久没动静,我不好说什么,动作很轻地先躺下了,这时我听到彩妮轻轻的抽泣声。我不知怎么了,忙翻身坐起来,拉亮灯问你怎么了?
彩妮不看我,低着头说:我没事,我是高兴呢。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彩妮一直这样平安相处。这些天,我一直在为彩妮画一幅油画,油画的题目我都想好了,叫《少女》。画布上彩妮的形象已有了一个轮廓,画中我把彩妮放到一个有山有水的草地上,彩妮坐在草地上眺望着远方,远方是一缕袅袅飘逝的炊烟,整个调子是一幅乡村情趣,我喜欢这种静谧安宁,或许这就是藏在我骨子里的情结。
一回到18号那间小房间里,首先是彩妮生火做饭,屋子外面有一个烧煤球的炉子,以前我除在炉子上烧些水外,它没有任何用场。自从彩妮来了以后,我结束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彩妮会做许多种味道香美的菜肴。几天下来,我合算了一下开销,这种吃法要比我在外面小馆子里吃便宜几倍。我从心里感激彩妮,有时我觉得,不是我收留了彩妮,而是彩妮收留了我。
回到小屋之后,彩妮便忙进忙出地准备做饭,我则为等一会儿的创作做准备,把不同颜色的油彩挤到调色板上,调出我需要的那种颜色,做完这些,我闲下来一边吸着烟一边端详那幅尚未完成的画。听着锅碗瓢盆的撞击声,嗅着饭菜的阵阵香味,一种久违的温馨从心底里升起。有几次,我差一点流出眼泪。心里感叹地道:生活就是生活。
那一天,我正在和彩妮吃饭,林肯一头闯了进来。林肯吃惊地望着眼前的景象,张大嘴巴,半晌说:你小子搞什么名堂。
林肯是个作家,也是从外地闯荡到北京的无业作家。林肯年长我几岁,已经三十出头了,留着大胡子,头却剃得根毛不剩,说话粗声大气。林肯同时给几个小报和青年刊物专栏写稿,也当掮客,帮助剧组拉广告,为涉外婚姻牵线搭桥,林肯于是就很忙,半个月为这样或那样的专栏写稿,另外半个月外出为诸多事物牵线搭桥。林肯租的房子就在我隔壁。半个月在
家的日子里,林肯很少出门,买一箱方便面回来,便不再出门了。关起门来闭门造车。林肯似乎整夜不睡,通宵达旦,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篇篇专栏稿子便写出来了。写完这些稿子,林肯就瘦了一圈,两只眼睛红肿着,骑上那辆破自行车把那些烟熏火燎的稿子送往各个编辑部。送完稿子,林肯回来时,会买一大兜子猪耳朵鸡脖子什么的,每到这时,他总是把我喊过去,陪他喝酒。林肯极能喝酒,一瓶二锅头转眼便喝光了,把吃剩下的猪耳朵什么的,往地下一划拉,倒头便睡。这一睡能睡上两天两夜。
刚开始,我总以为他死过去了,便胆战心惊地推门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鼾声如雷,震得两腮的连须胡子也一抖一颤。大约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醒了,夹着腿,跑到墙角处撒上一泡又长又黄的老尿,然后呵气连天地走回来。
我冲他说老林你真能睡。
他说操,还有挺多事等着我呢,要不我还能睡上三天。
林肯讲完话果真便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歪一扭急匆匆地走了。剩下的时间,很难再见到他的影子。林肯写的那些文章我曾看过,大都是一些少男少女失恋该怎么办,安乐死和试管婴儿什么的。我不知道林肯怎么有那么多耸人听闻的故事可编。但一想到林肯通宵达旦烟熏火燎编这些故事的情景,想必他也并不轻松。
林肯是我来北京见到的惟一一个够意思的朋友。刚来北京那几日,我无处藏身,天天背着个画夹子在建国门立交桥一带转悠,晚上买一张站台票到火车站里凑合一夜。那一天我在大街上碰到了林肯,他便把我带到这里来,帮我租下了这间小屋。
把我安顿好后,林肯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年轻人搞**艺术干啥,净自己搞自己。
我刚见林肯面时,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年纪,当知道他叫林肯时,我想起了前美国总统。我就笑着说:你莫不是美国总统吧?
他说我是美国总统他爹。
后来我知道,林肯是东北人,只比我大几岁,老家在农村,已有老婆和孩子了。我不知道林肯还要在北京这么闯荡多久。
彩妮的事我不想隐瞒林肯,我便简单地把彩妮的事和他说了。他听完眨巴几下眼睛说:你们等一下。说完便出去了。
不一会儿提回一堆吃的来,不由分说把一瓶酒打开,把我和彩妮面前的碗里倒满酒。然后举起酒瓶子说:喝,欢迎又有个女哥儿们加入到我们流浪的行列。
没多一会儿,林肯就喝光了瓶里的酒,满嘴酒气地冲彩妮说你不就是想当明星么,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我刚给一个剧组拉了一份广告,导演是我哥儿们,明天我就去说这事。
我和彩妮都呆呆地看着他。他在我们的视线里摇晃着走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