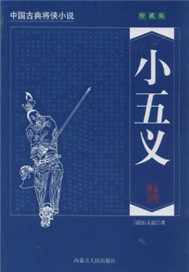许多年过去之后,王三顺仍不能忘记起事前新洪城里的那一派肃杀恐怖气氛。他和边义夫是从老北门进的城,在回龙桥上就远远地看见,把守城门的巡防营兵勇不少,对进城出城的可疑者都搜身抄检。
城门楼上还挂着革命党的首级,记不得是三个还是五个。
首级是装在木栅笼里的,都风干了,仍未取下来。
木栅笼下有一排告示,书着被斩首者的罪状。
到了城里,在皇恩街上又见着几个官府的衙役用铁绳锁着两个白面书生在往大狱里押。
四下的街巷里巡防营和绿营的官兵随处可见,时而还可看到奋蹄驰过的马队。
王三顺心里怯了,下了皇恩街,一钻进小巷里便试探着问边义夫:“边爷,你……你看这阵势,咱还真去运动钱管带呀?”
边义夫怔了一下,说:“当然要去运动的,咱们为啥来的呀?”
王三顺觉得边义夫有些呆,又俯着边义夫的耳朵道:“人家现在正满城抓革命党,咱……咱这不是往人家刀口上撞么?”
边义夫不做声了。
王三顺进一步道:“边爷,你想呀,倘或你是钱管带,你会放着好生生的管带不当,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去和挨杀头的革命党私通么?”
边义夫心里没了底,叹了口气说:“叫你这么一讲,我也拿不准主意了。”
王三顺道:“边爷,主意好拿着呢!咱早回家就是!回去也别说咱就没运动,只说运动了,人家钱管带不干。”
边义夫想了想说:“形势……形势如此的严重,也……也只好这样了。”
遂即又很认真地说:“这倒不是我们存心要骗霞姑奶奶他们,而是……而是钱管带十有八九不会跟咱干的。”
王三顺道:“对,对,这是不用说的,钱管带要是有一丝革命的意思,还会这么杀革命党么?你看看城门口挂的那些人头!”
因着城中的恐怖,王三顺一心想着要早点回去。
边义夫却不同意,说是半个多月没进城了,今儿个难得进一回城总得会会朋友,再找个能销魂的地方耍耍才好。
王三顺马上想到汉府街“闺香阁”的那帮姐妹,心就痒痒的,于是,赞同了边义夫的主张,很快乐地跟着边义夫往汉府街走。
革命前夜,“闺香阁”仍像往常一样热闹,院里灯红酒绿,笑声一片,琴瑟之声不绝于耳。
二人熟门熟路进了院子,就被倚在回廊里的两个姐妹拖住了。
胖的说要他们请酒。
瘦的说要为他们烧烟。
两个姐妹浓妆艳抹,不论胖的抑或瘦的都很老相。
王三顺看了都不中意,边义夫自然就更不中意了。
可又不好说,就被人家硬拖到了楼梯口。
这当儿,老鸨母毕刘氏托着水烟袋过来了,救了他们的驾。
毕刘氏对那两个姐妹说:“你们拉啥呀?这二位大人是找荣姑娘和梅姑娘的,我知道。”
又对边义夫说:“边爷可是有一阵子没来了吧?昨天荣姑娘还在我向前哭呢,说是想你想得不行。”
边义夫问:“荣姑娘在么?”
毕刘氏说:“在的,在的,像似知道你要来,今日便没出条子。”
边义夫谢了毕刘氏,就要往楼上荣姑娘房里去。
王三顺忙追着边义夫走了两步,小声问:“边爷,你不管我了?我……我这边的花账咋办?”
边义夫说:“老规矩,我一起结。”
王三顺又道:“赏钱我总得有两个吧?”
边义夫这才掏了两把碎银子给了王三顺。
王三顺把碎银子揣好,毕刘氏又走过来说:“你那要好的小梅姑娘也在哩!只是房换了,在楼下南屋,我领你去……”
这让王三顺有点为难,他不想去找小梅姑娘,小梅姑娘太土气,又不会唱唱,他想新找个会唱唱,并且漂亮有浪味的姑娘好一回,就说:“我自己去吧!”
毕刘氏非要带他去,这一来,就把他送进了小梅姑娘的怀里。
小梅姑娘正来着月经,王三顺开初并不知道,待得知道,啥都晚了。
看着倒在床上的那一堆诱人的白肉,王三顺什么晦气不晦气的都顾不得想了,直弄得满床的血水,仍是捣个不停。
到后来才发现,自己身上也满是污血,大腿、肚皮都红湿一片。
王三顺后悔起来,一把抓过小梅姑娘的衣裙在自己大腿、肚皮上擦,一边骂小梅姑娘坑人,故意用撞红的晦气来毁他。
小梅姑娘说:“不是我要毁你,却是你要毁我。你这人太粗,没一丝一毫怜香惜玉的心,一见面没说上几句话,就要弄我,你可问过我身上舒服不舒服?”
王三顺眼一瞪说:“什么怜香惜玉?我不懂!我花钱到这儿来就是为着玩**的!”
小梅姑娘很气,揩着身上床上的血迹说:“那好,那好,你已弄完了,你走吧!”
王三顺却不知该往哪走。
王三顺知道,边义夫不是他,和荣姑娘不泡上三五个钟点是断不会离开“闺香阁”的,他除了在小梅姑娘房里呆着,哪里也去不成。
于是,王三顺便恶毒的笑着走到小梅姑娘身旁,用粗大的手掌拍着小梅姑娘的光屁股说:“老子才不走呢!老子歇过乏,过一会儿还操你的臭X!”
小梅姑娘讥讽说:“有本事,你现在就来!”
王三顺惭愧了,说:“我歇歇,也让你歇歇……”
因为要“歇歇”,王三顺便借着小解的由头,到院中看风景。
不料,没看到别个做那事的好风景,抬眼竟看到了巡防营的钱管带。
钱管带穿一身团花缎夹袍,正站在回廊上和两个年少俊俏的姐妹笑闹,一手搂着一个,两手竟插到了两个姐妹的抹胸里。
见了王三顺,钱管带先一愣,后就笑着走过来问:“哎,你家老爷呢?”
王三顺指着楼上说:“在上面呢!”
钱管带笑道:“在荣姑娘那里听琴是不是?你告诉他,回头我也去听,我还有桩事要和他商量呢。”
王三顺说:“行,我现在就去和边爷说。”
上楼到了荣姑娘房门口,果然听得房里有阵阵琴声传出,趴在门缝中一看,身材纤细的荣姑娘正坐在边义夫怀里抚弄琴弦,还时不时地回首去亲边义夫的脸。
这益发让王三顺觉得吃了大亏,梅姑娘说他不知怜香惜玉,可梅姑娘有人家荣姑娘俊么?有人家那缠绵的滋味么?
因着心里的那份委屈,一恼之下就敲了门。
边义夫开了门问:“干啥呀,你?”
王三顺心里不愉快,便与自己的主子开了玩笑,说:“边爷,你不是要找钱管带么?现在钱管带来了,就在楼下等你。我看……我看运动一下钱管带或许能行,人家钱管带还说要找你商量呢。”
边义夫不信,眼睁得很大:“真的?钱管带真来了?”
王三顺说:“我还会骗你么?不信我现在就给你喊来”
边义夫忙道:“别,别……”
然而,已经晚了。
王三顺存心不让边义夫好过,扭头冲着楼下叫将起来。钱管带应声上了楼。
麻烦就这样惹下了。
钱管带那日原只想强卖些新到的大烟给边义夫,敲边义夫一点小小的竹杠,根本没想到革命党的问题,边义夫偏试探着扯起了革命党。
钱管带倒也会装。
白日里,钱管带还在四处捉拿着革命党,现刻儿却做出一副同情革命党的样子,说什么:如今这里独立,那里独立,大清天朝已是风雨飘摇,不知哪日一觉醒来,就会变了朝代。
边义夫上了当,真以为钱管带可以运动,当下便把革命党的帖子掏了出来,拿给钱管带去看。
钱管带看过帖子,很认真地问:“边先生,你可是革命党?”
这关键的时候,边义夫倒多了个心眼,只摇头,不点头。
钱管带又问:“你既不是革命党,哪会有革命党的帖子?”
边义夫说:“这你就别问了……”
钱管带偏要问:“你把它给我看是啥意思?”
王三顺这时已觉出情况不对,未待边义夫答话,便插上来道:“边爷那意思您老还不明白么?我们是报告呀,报告给官府,把革命党全抓住杀头!”
钱管带冷冷一笑,莫测高深地说:“倘若我他妈的就是革命党呢?”
也不知这话是真是假。
边义夫和王三顺都不敢作声了。
钱管带又盯着他们看,看了好半天才说:“咱都别玩戏法了,这戏法不好玩哩!不论咱过去关系如何,这会儿,你们都得跟我走一趟。这一来,兄弟就得罪二位了”
钱管带冲着边义夫和王三顺一抱拳:“兄弟先给二位把情赔在前面了。”
当下,钱管带把带来的兵勇唤上了楼,两人扭一个,把边义夫和王三顺扭下了楼,拉拉扯扯出了闺香阁。
直到梦也似的成了钱管带的俘虏,边义夫和王三顺还不知道钱管带到底是哪一路的?
是革命党?
是官府的爪牙?
往哪边想都像。
去的地方也不清楚。
不是大狱方向,也不是巡防营住的三牌楼,却是一路奔西,下了汉府街,又过了状元巷,最后竟到了一座门口有一对石狮子的大宅院里。
进了大宅院,钱管带让他们和押解他们的兵勇们在门房候着,说是先要去禀报一声,径自走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回来。
边义夫知道大事不好。
趁着兵勇不备,边义夫对王三顺说了句:“咱……咱啥都不能认……”
王三顺点了点头,很坚定地“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