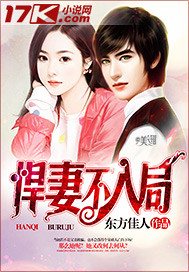从水库大坝下来,他们就到了汪霞家里。汪霞向母亲介绍了李彬和刘林。这位老太太眼窝深陷,瘦骨嶙峋,手背上的青筋根根暴露,就象是菜叶上的青虫一条条爬在上面,但头上稀疏的白发却疏理得十分干净整齐。老太太并没有见到大干部时的那种惶恐和窘迫,她落落大方地说:“不管是厅长也好,厂长也好,看得起我们农民家,就坐下来喝茶吃酒,看不起就走人。”李彬说:“婶娘,我和老刘都是宁州人,我是保和墟人,老刘是清泉溪人,我们都是农民家的孩子。”老太太吃惊地望着刘林:“你是清泉溪的?”她眯着眼睛端详了一会,立刻一拍大腿:“你是刘忠祥家的老三吧?”刘林正在疑惑间,老太太上前一把抓住刘林的手:“想不到我老了还能见到你们家的人。” 刘林问:“婶娘,你是……?”,老太太说:“我是吕云秀!”。这时,刘林终于打开了记忆的阀门,在漫长的记忆画卷中闪出了一位年轻俊俏的身影:“您是云秀姐?”,“是啊,是啊!”,老太太激动地抓着刘林的手直摇晃。“云秀姐,几十年了,您怎么一下就认出了我?”老太太说:“你跟你老子长得太象了,也是这么高高大大,这么壮实气派!对了,你姐姐还好吗?她可是我的大恩人啦,当年要不是她出面,我可走不出那个狼窝呀!”
李彬和汪霞都在旁边愣了。刘林望了望他们俩,欲言又止。老太太看出了他的心思,又一拍大腿说:“哎!有什么不好说,我过去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用电视里现在时髦的话来讲,我那叫争取妇女的合法权益。”刘林见从老太太嘴里冒出这么一个时髦的词儿,不禁笑了。刘林对李彬说:“这位云秀姐当年嫁到我们村的时候,是我们家的邻居。云秀姐年轻的时候,那可是周围百里挑一的美女,村里的年轻人对她的丈夫可真是羡慕得不得了。云秀姐当时的丈夫,是大队支部书记的侄儿,这个人相貌长得很不错,而且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力士,二百斤的担子挑上就走,但就是一个酒鬼,每次喝酒非要醉个死去活来,不然不肯罢手,喝醉了就回去打云秀姐,我那时正开始上学了,经常听见他们两口子吵架。”老太太叹了口气接过去:“刘石祥那个死鬼,老是怀疑我跟这个好了,跟那个好了,有一次他又打我的时候,我就抄起了一根扁担对他吼:刘石祥,我是你的老婆,不是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的丫环,你再敢打我,我就跟你拼了!那一次,我真把他给镇住了。但这个刘石祥,天生的一副牛脾气,又仗着他叔叔是大队书记,以后照样一喝醉就打人。我就跑回娘家,提出要跟他离婚。他叔叔出面威胁我,说如果我敢离婚,就要把我捆起来游街,还要把二百块钱的彩礼退回来。多亏你姐姐那时候是大队妇女主任,很同情我,支持我跟刘石祥离婚。那时候我们那个谢区长也很和气,他听了你姐姐的汇报,还找我谈了话,觉得我的离婚要求是合理的。就这样,我就到区里办了离婚手续。唉!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姐姐现在她好吗?”
刘林说:“我姐姐身体好着呢,前几年我姐夫过世了,外甥要接她到县城里住,她死活不肯,还说,在村里乡里乡亲们住惯了,讲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城里人一个个小气得很,就是住在隔壁的邻居,一年到头也从不往来,她跟城里人合不来。”
老太太说:“你姐姐那个脾气,跟我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去年汪霞她姐要我到县城里住一段时间,我才住了三天,就觉得吃不下睡不着,象掉了魂魄似的。”
“三伢子”, 老太太又说:“我走的时候,你还没有上学吧,算起来你今年也该有五十了。”
“五十二了,”刘林不经意地瞟了一眼汪霞,轻轻地叹了口气,脸竟然红了。
“你们老刘家的人,个个都长得威武俊俏。”老太太又十分感慨:“看看你,白白嫩嫩的,哪象个五十多岁的人,倒象个三十多岁的后生仔。唉,对了,你怎么不把你爱人带回宁州来看一看?”
“我爱人已经过世了。”刘林在老太太面前规矩得象一个小学生:“到如今已经两年了。”
“啧啧,”老太太叹息了一声:“你爱人也是个命薄的人,孩子大了,一身轻松了,她就走了。唉!”老太太又满怀深情地叹息了一声,还摇了摇头。
汪霞给客人们倒上茶后,就一直靠在老太太的身后,这时,她有些撒娇地摇了摇老太太的肩膀:“妈,别唠叨了,快准备晚饭吧!”
老太太笑了笑,回身慈爱地拍了拍汪霞的手背:“今天贵客临门,快去把那只老西鸭给杀了。”
刘林忙说:“云秀姐,千万别兴师动众的,一会李厅长马上要到县里找领导们有事。我们就这样坐着说说话比什么都开心。”
李彬趁机把话题拉到了与郑春光有关的话题上。“婶娘,春光出事前跟你说过一些什么吗?”
一提起郑春光,老太太就流起泪来,她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说:“春光这孩子,是我害了他呀!多好的一个后生子,是我害了他呀!”
李彬说:“春光已经走了,您老人家也不要太悲伤了。春光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希望您老人家把春光出事前讲的话,做的事仔仔细细地告诉我们,越仔细越好。”
老太太仍然不能自制,她悲伤地摇着头,用苍老的青筋毕露的双手拍着大腿:“算命的跟我说,是我这个老不死的命太硬了,把春光给克死了!我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最后只剩下霞妹子和她的大姐,老头子被我克死了,两个儿子也被我克死了。春光到我们家这些年,别提我有多喜欢了,可是这么好的后生子,也被我这个老不死的克死了,作孽啊!”
“春光是哪一天从省城回到家里的?”李彬只好从具体问题入手。
“三月初五。”老太太终于稳定了情绪,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洗得很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睛。她说的显然是农历,李彬心里计算了一下,应该是四月十二日。
“春光那天天黑了才进的家门,”老太太说:“他刚一落脚,他汪叔就跟着进屋来了。他汪叔说,刚才接到镇里王书记的电话,要他们俩明天到县里去,县委书记要亲自找他们谈话。他汪叔对春光说,你今天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跟县委书记谈话,肯定轻松不了。晚上,春光问我:妈,你说我们应该把那么好的稻田卖给他们盖别墅吗?我说:别墅是什么东西呀?春光说:别墅就是一栋一栋的小洋楼,是专门卖给有钱人住的,这些房子,说不定有钱人一年只来住一个月或两个月。我说:那不是造孽吗?那么好的稻田,毁掉了给有钱人盖房子,那我们将来吃什么呀!春光叹了口气说:是呀,现在县里的领导们,一天到晚只想着盖房子呀,搞工程呀,至于怎么把粮食种好把蔬菜种好,就没有人感兴趣了。原因很简单,房子盖得多,工程搞得多,说明领导们的工作成绩大,上级就会表扬他们,提拔他们。更要命的是,现在那些专门盖房子赚钱的开发商同政府在利益上抱成了一团,谁要是挡了他们发财的路,他们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嚇了一跳,说:春光,你不同意把地卖给他们,他们不会对你下手吧?春光笑着对我说:妈,你放心,我们这块地处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对他们没有那么重要。”
“第二天,春光同他汪叔从县里回来,黑着脸,看样子很不开心。我问他:县里头领导给你们讲些什么呀?春光说:县委书记对他们发火了。批评他们只看到鼻子尖下面的利益,看不到全县发展的大局。我说:春光,你别怕,政府总是会讲道理的。我是从三年苦日子里过来的,我知道没有粮食吃的那个味道。把那么好的稻田给毁了,还叫大局吗?别怕,妈支持你。春光摇着头说:一个县委书记,为这个事发那么大的火,拍桌子摔茶杯的,不理解,不理解。”
“听说有人到家里给春光送礼了?”李彬问。
“这事也怪我。”老太太说:“那是春光从县里回来的第二天上午,一辆小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那辆车呀,贼亮贼亮地显得好气派,比你们这辆车还长出来不少。从车里下来俩个年轻人,长得又秀气又文静的,穿戴得也很体面,进屋后,俩人一口一个地叫我‘婶娘’,又和气又嘴甜,他们说是春光的朋友,多年不见了,特地从深圳来看望春光。我要他们留下来吃中饭,他们说公司催着要赶回去。临走留下了两个装着烟酒的礼物袋。春光回来后打开一看,装烟的袋子里还有一个大信封,里面满满地装着钱,全是一百元一张的。春光一看就明白了,他立该就把他汪叔叫来了。他汪叔说,准是那个什么凯园公司的老板送的,他家里也有人送了,他俩商量好,当天下午就把东西和钱都送到县里头去了。”
“婶娘,你知道那个凯园公司的老板的情况吗?”
“唉,我一个农村老太婆,哪知道他们的事情。不过听霞妹他大姐说,那个什么凯园公司的老板在县里头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人物。县里头凡是大一点的工程,只有他能接,别人就是接了也干不成。”老太太突然一拍脑袋,又想起了什么:“我听霞妹她大姐讲过,那个老板是太平湾人,你们知道太平湾那个地方吧?”老太太望望李彬和刘林,俩人都点了点头。“国民党那会,太平湾出了个军长,可凶了。太平湾和平田湾的人打架,那个军长派兵帮忙,把平田湾的人杀了不少。事后,听说那个军长还被上头表扬剿匪有功。”
老太太的活只不过是进一步印证了李彬之前掌握的情况。他朝刘林使了一个眼色,刘林站了起来向老太太告辞,老太太着急地拉着刘林的手不放:“怎么这么急?怎么这么急?”刘林说:“云秀姐,下次我一定专门来看你。”
这时,汪霞急匆匆地从里屋出来,满脸怒容地对老太太喊:“妈!屋里的东西是谁送的呀?”
老太太放开了刘林的手说:“那是李云送的。你出去后,云伢子可是来过好多趟了,他对过去的事连肠子都悔青了,他说,他好想找你谈谈。”
汪霞满脸涨得通红的大喊:“妈!你理他干嘛呀!”
李彬望了刘林一眼,便笑着问老太太:“婶娘,李云是谁呀?”
老太太说:“这云伢子呀,是跟我家霞妹穿开挡裤一起长大的伙伴,现在可是什么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啦。”
李彬又对老太太说:“我们要到城里找汪叔了解情况,还是麻烦汪霞给带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