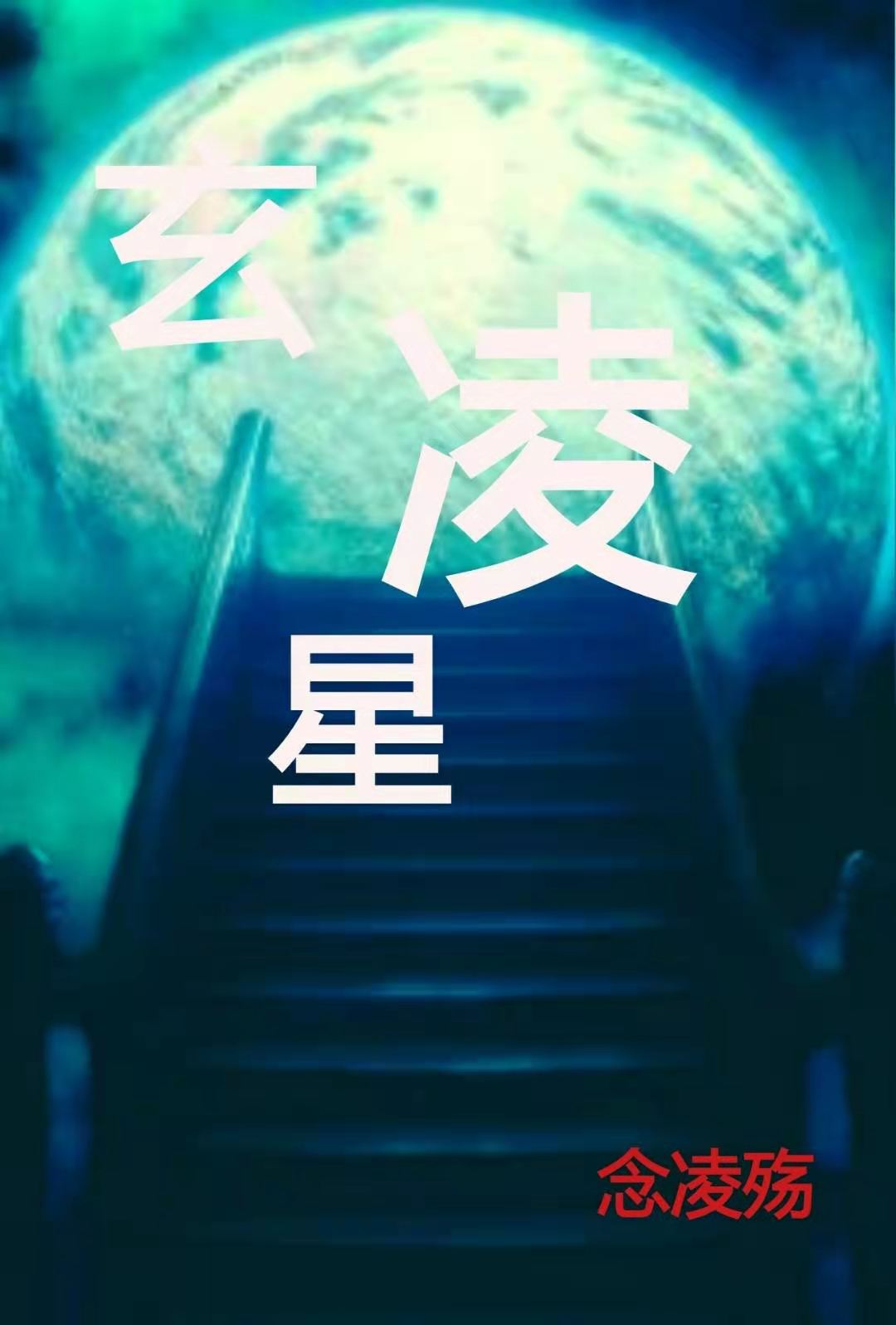张武住进了医院,他在这场冒顶事故中,侥幸躲过了一劫。
现在,张武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头上包着白色的纱布,就连眼也被厚厚的纱布蒙住了。
“我的眼,我的眼怎么了?”张武喊。
昏迷了一天后,张武醒了,他用手摸摸自己的眼睛,只感觉眼前黑黑的一片。
“我的眼瞎了吗?”张武又喊。
“眼没事,”一个甜甜的声音在床边说,“是被煤尘糊住了,你的眼有些发炎,大夫已给你上了眼药,很快就会好的。”
“你是谁?”张武问。
“护士。”
“护士?”
“嗯,我是护士,你现在是在医院里。”
张武听她说是护士,而且那护士说自己的眼没事儿,心情一下就放松了下来。
放松了下来,张武就在心里判断开了,他觉得刚才跟自己说话的护士一定很漂亮,她说话的声音多好听!她说话的声音有多轻、多揉、多甜!甜得甚至有些稚嫩,弄不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
为了确认自己对这女护士的判断,张武问:“你刚从学校毕业吗?”
“哪里,你真逗!”女护士咯咯地笑着。
张武听到女护士的话,知道自己判断错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听你的声音感觉你不大。”
“年龄哪能听出来?”女护士说。
张武说:“我的眼前黑乎乎的一片,啥也看不见!”
“很快你就能看见了。”女护士很有把握地说。
张武问:“我家里有人在吗?”
“这是重病房,家属是不能陪床的。”女护士解释道。又说,“不过你哥嫂来看过你了,再过两天你转到普通病房家属就可以陪床了。”
张武听着女护士甜美的声音,一下想起了自己的对象向梅。向梅现在在干什么?她知道我出工伤了吗?
他这样想着,突然脑子一阵撕心裂肺地疼,好像有人用钉子在剜,他咬紧牙关挺着,大粒的汗珠从脸上滚了下来,顷刻,他又昏了过去。
昏迷中他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巷道里,他就那么摸着黑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发现走到了自己工作的掘进头,看见半截儿正坐在地上等着放炮。他才要叫班长,就听“嘟,嘟”两声口哨声,随后“轰”的一声炮响了。
这时,半截儿站起来大喊:“肉们,日娘的放完炮了,往前头干活啦!”
张武听到班长的喊声,用手捂着嘴,顶着浓浓的炮烟往前头走。两个大工和一个小工有些不情愿地跟在自己的身后。
当快走到前头时,只听“轰、轰”的两声巨响,张武扭头就往回跑,刚转身就被震趴下了。他觉得怎么刚放完炮,这炮又响了?正这样想着,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压住了自己,还有一股气流裹着煤尘从下糊到了脸上,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张武好像又醒了过来。但他一动不能动,眼睛也睁不开。他在心里狠狠地骂道:“李半截儿你个老疯子,这炮刚放响,炮烟还没散,你就撵着大伙往头上去干活,看看,看把我们都埋住了吧!”
张武被大砟块压着不能动,但他心里很清楚,他在心里一遍遍地数叨着班长李半截儿:“半截儿啊,我知道你积极,不就是想当队长么?不就是为多进几米窑脸上光彩么?你每天这么不要命的干,光你积极表现也就算了,把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也给搭上了……”
一会儿,张武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觉得脑子很疼,那疼一阵阵的,疼得他直咧嘴。
女护士过来见张武咧着嘴,脸上不住地往下淌汗,问:“头疼得很吗?”
张武只是咧着嘴不说话。女护士笑笑,用一块白纱布给他擦了擦脸上的汗出去了。
停了会儿,张武的疼劲儿过去了,他觉得刚才女护士给他擦汗的手好轻、好揉、也好香,可惜自己看不见。要是能看见的话,他再一次确信她长得一定很好看,一定是那种柳叶眉、大眼睛、鹅蛋脸、小嘴唇,那叫什么型来着?对,小鸟依人!是那种小鸟依人型的。
此刻,他感到刚给他擦过汗的脸上,还留有一丝好闻的余香,那余香正侵入他的心脾,停留在他的心里。
正这样想着,忽然张武的脑子又一阵剧烈地疼痛,他又昏了过去。
冥冥之中,张武觉得自己好像脱离了身体,慢慢地飘了出去。他还觉得自己能看见东西了,屋外的天好蓝,云好白。他这样轻悠悠地飘着,好自由、好自在,感觉想往哪里去就能往哪里去。
他高兴极了,他刚想见自己的对象向梅,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向梅家门口。
向梅家的院墙有一人多高,大概在一米五六的高度,变成了花格墙。透过花格墙往里看,能看到小院里的两棵石榴树,看到石榴树上开得红艳艳的石榴花。
张武站在向梅家的院门前,院门紧闭着,可他觉得很神奇,不知怎么,门没开他就直接进到了院子里。
向梅家的院子很大,院子的地是用浅红色大理石铺的,平整而光洁。挨着院墙的那两棵石榴树下,放着一张好看的汉白玉园桌和四把白色的塑料靠背椅。
屋门大开着,好像有人在说话,张武飘忽忽地进了屋。
客厅里向梅的爸妈坐在沙发上,向梅坐在他们的对面,他们好像正讨论着向梅的婚事。
“梅啊,”向梅爸很认真地说,“我看你和张武的婚事还是算了,你们俩一开始我就不太同意,你是个老师,他是个下井的,工作不般配不说,还很危险。这不,井下冒顶一下砸死三个,据说他也差一点儿,现在还在医院抢救,这以后要是落下个什么后遗症,你可咋办?”
向梅爸说完,看了看向梅,又说:“梅啊,爸妈就你这一个女儿,他的工作好赖且不说,就是退一万步,哪怕是一个井上的工作也行,你说,爸要求的条件算高吗?”
“我说小梅,”向梅妈接话说,“你爸说得对,张武他好赖是个井上工,你爸妈也就不说啥了。可,可他是个下井的,你也看见了,多危险!要是万一有个好歹,你这辈子可咋过?!”
向梅低头坐着,没有说话,两眼只是噗噗地往下掉泪。
客厅里的气氛很沉闷,停了会儿,向梅妈说:“小梅,你和张武的这婚事我看算了,叫你爸从学校年轻的老师中再给你介绍一个,就这么定了!”
“我看行,”向梅爸说,“有几个老师都要给咱小梅介绍对象呢。”
“正好,反正小梅跟张武还没订婚,”向梅妈说完,又问向梅,“梅,你说呢?”
向梅默默地坐着,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张武傻傻地站在屋门口,瞪着两眼看着向梅,他想听向梅怎么表态,可向梅至始至终也没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