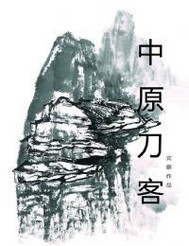二人对视了一会,石远在擂台上左右移动几步,心想要和佛手金刚项飞打只能智取,不然会输得很惨。
对面的项飞从头到脚往那一站,毫无任何破绽,石远因观察到刚刚项飞与史公子的比试,心想项飞上身是一副铜皮铁骨,下身定会有些软处,于是便决定主攻腰部以下。
石远一个飞身冲了上去,突又侧身栽倒在地,单手拄地双腿交替成旋风般,猛地向项飞踢去。
项飞在那还是稳如泰山,因为他体型笨重弯腰自然也难,石远直接攻击下方腿部他无可奈何,只能任凭石远攻击,石远连续踢了十多下项飞并无任何反应,还是稳稳站在那里。
石远心想,这腿上既然无弱点不如去身后看一看,石远身轻灵活瞬间又单腿钩住项飞脚脖处,来个一百八十度瞬间漂移,项飞还没反应过来,石远已到项飞身后伸出重拳向后背打去。
项飞只能任凭石远攻击毫无还手防御的能力,石远伸出重拳狠狠地打在项飞背上,项飞被狠狠击中一拳后,是否感到疼痛,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所有人看来任何攻击对项飞都是无用的。
项飞似乎略感到些疼痛,只见他长臂一伸抓住石远的拳头,狠狠地把石远从身后经过头顶又摔在项飞面前,石远被摔了个措手不及重重的摔倒在地,那可不是一般的疼,差点大叫出来可是他忍住了。
石远一个起身后又开始快速向项飞攻过去,石远每一拳又快又狠,万箭齐发同时向项飞打去,项飞丝毫未动只是伸出双掌,上下左右一阵乱串,就像有几百只手一样一同抵挡,都是虚影看不清实掌。
二人打了二三十回合未见胜负,石远有些累了,重重一脚后弹回到擂台一边。
石远心想先歇一歇,他清楚项飞是不会主动攻击的,若是项飞主动攻上来,或许随便换做一个人都可以打得过项飞,项飞只有一动不动才是最无懈可击的。
没有任何破绽,一旦动了就会漏洞百出,可是单凭石远的力道还不足以打得动项飞,石远其实上来之前就想好了,要与项飞打个持久战。即使不能赢也不会输,大不了二人都不动坐等太阳落山也好。
石远还是想找到方法可以赢得这场比赛,因为这样就可以顺利入军做个精兵。
项飞也在想,对面这小子也有些手段,自己想赢也要费些气力,若是弄不好让他转了空子没准还会输了比试,所以他面对石远时也比平常更加小心一些。
石远已经歇得差不多了,只听台下群众大喊道:“快打啊,再不快点太阳都要落山了!”
石远心想,也不能总这样耗着,台下那些人可等不起,不如再来几回合慢慢找机会吧。
石远冲了上去又是一阵拳脚,二三十回合过去了未见高低,石远又退下,呼吸明显急促了些。
石远小歇息一会又冲了上去,二三十回合又过去了,还是未见胜负。
石远又回到擂台一边,见对面的项飞也开始气喘起来,想必这么大的身躯,耗费的气力绝不少于自己,自己体力恢复的又快些,在这样下去,坚持几十回合后自己定可以找到机会,一击制敌。
台下的观众还在高声喊着,石远又随着高喊声冲了上去。
太阳已经从正上空滑落到很远的斜下方,斜下方那丝丝光线看着虽有些刺眼,可所有的观众都不顾阳光刺眼,一同看向了远处,眼神好点的大喊道:“是薛公子,薛公子来了!”
这薛公子城中百姓都认识,因薛公子是个大善人,每次遇到一些有困难的百姓都会赏些银两,所以百姓们也都喜欢薛公子,史家的二公子却没有几个百姓喜欢,刚刚擂台上的二公子虽不是十恶不赦之人,但也绝不是善类。
薛公子身穿白色铠甲空手从远处走来,那擂台不远处摆了一张木桌,旁边坐着两个武试考官,应该就是负责招精兵的。
二人见薛公子来了连忙起身迎接行礼,薛公子对二人问道:“怎么样了,今年何人胜出?”
其中一人道:“今年情况特殊,台上还有两个打了许久未见分晓。”
薛公子向擂台方向看去,见那二人还在一阵拳脚,仔细一看原来是他们,便又对那两人说:“去告诉他们别打了,今年破例他们两个都要了,说完转身便离开了人群。”
那人听后连忙跑到擂台前大声说道:“你们两个别打了,薛公子发话了破一次例,你们两个都可以入护国军精兵营了。”二人听后都停了下来。
众人见不打了也都慢慢散去,石远总算如愿当上了精兵。
石远与项飞二人来到台下,项飞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说道:“你小子还真是厉害,听他们说你叫石远吧,以后多多关照。”
从话语声中便可听出,这项飞平时是个心直爽快的热心肠。
石远也连忙回道:“没想到你还真是厉害,今日得见十分有幸。”
项飞接着又爽快的说道:“兄弟,我是个粗人不太会言语,以后咱们可就朝夕相处了,我若有什么说错做错的,还望兄弟多多担待。”二人边走边聊随着考官一同去了。
在看那边的文试区早已人散物空,也不知道赵厚德赵庸今年命运如何?
那西方的残阳,无论你身在何处都无处躲逃,微弱的光线穿过城墙,毫无情面的打在那人的脸上,此人是个情种,多情的种子遇上无情的光,自然心生伤感。
站在城中花园中央的湖水旁,泛黄的残阳倒影在湖面,让他不由得想起多年前,同是在这里此时却又是一番别的景象,那时心中空闷,此时心情复杂。
只见他脱口而道:
青叶有一妖,入身便难瞧。
思之若即现,挥何挥不掉。
此人正是国主福亥,这么多年他还在思念李夫人,李夫人死后,其实不仅对薛岳打击很大,这福亥也是一连多日茶饭无味,经常到这花园之中,对着明月寄托相思之情。
十四年过去了福亥的容颜渐改,但对李夫人的思念之情却丝毫未减。
一旁的圆画明白了国主心中所想急忙说道:“国主,这青叶一妖怕是李夫人吧,李夫人已过世多年,这倾国倾城之容非李夫人莫属,但还有那闭月沉鱼之貌啊!国主不可为了一个女子而放弃天下啊,好女子此刻或许就在城外!”
这么多年过去,圆画除了还是那么圆滑有心计以外,没有改变,其他的变化可就太大了,就说这容貌吧,真是岁月不饶人,脸上松弛的皮肤早已不比当年,两鬓灰白的发丝也略显沧桑了几分,连声音也多了许多线条,苍白而又无力,想必他这么多年也是操碎了心。
国主福亥听到这话收回心中所想,又问道圆画:“你可是又有眉目了?”
圆画微微一笑回答道:“禀国主,城外黄土镇有一女子,虽无李夫人之容貌但却不输于李夫人,国主若想见我明日便安排出城。”
福亥一听心中一喜心想,这么多年冬画也从未在他面前如此夸一女子,想必这女子也定有过人之处,后接着问道:“此女子既无容貌,为何说好?”
圆画鬼笑道:“国主见了定会不舍,此女子不比李夫人难得,若是想要随时都是国主您的,您还可接她到城内让其常伴国主左右。”
福亥听了这话有些迫不及待想见到此人,便急忙问道:“这黄土镇快马加鞭多久可到?”
圆画道:“若是骑马不出一个时辰便可到达。”
福亥急忙命令道:“快去备马,你我这就出发。”
圆画听了没想到国主这么着急,又忙说道:“国主,今日天色已晚,若出城去被史夫人知道,怕是不会饶了奴才的,不如暂忍一日明早再去也不迟啊。”
福亥大怒道:“你这奴才,有我呢你怕什么,我们悄悄便装出城不带一随从,你快去准备天黑之前我若见不到那女子,小心你脑袋搬家。”圆画听后吓得连忙叫人备马。
那一梦楼又来了一位面熟之人,孟掌柜正在那算着一天的收成,最后的几桌客人也都离开的离开,上楼休息的休息,店小二孟中仁也在忙着打扫。
那面熟之人情绪低落,进来后自己随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掌柜的一看此人,正是黑面书生赵厚德。
后连忙放下手中算盘走了过来,又对孟中仁说道:“快去给赵官人煮碗面。”
赵厚德今日举止反常说道:“今日不吃面,好酒好肉尽管拿上来。”
孟掌柜一听这话连忙吩咐下去,心中也是明白了大概,想必今年又未能成功后安慰道:“赵官人莫要灰心,这人的命运谁也说不准,今日不幸落下来,吃完这顿酒肉没准明日幸事便来了。”
赵厚德知道掌柜的不过是奉承之语,便恭敬地回他道:“多谢掌柜的吉言,我一个人呆会就好了。”
说完掌柜的便又回到门口柜台,不一会孟中仁上来了酒肉,赵厚德拿起坛中美酒,倒了满满一大碗并一饮而尽,又接连喝了几碗心中很是不痛快。
赵庸心想如今这是什么世道?前两年因考官见他面相不善,便把他赶了出去,今年又遇到考官,只是远远看了他一眼便派人拦下了他,连考场都未得进,想到这里满肚子火气无处散发,接着又是一碗酒下了肚。
赵厚德已有些醉意,脱口而出自言道:“想我赵厚德,一生光明磊落、饱读诗书,励志报国安家,从小修身克己专研治世之道,如今二十有八却落个一事无成,真是苍天无眼、国之不幸啊!”
这大声叹息正被刚刚进门的福亥和圆画听见,孟掌柜见门口来了两人,其中一个正是城中圆画大总管,另一个却不曾见过。
孟掌柜急忙跑出来刚要跪下请安,圆画连忙对孟掌柜说道:“不必了,我此次私服而来不为公事,你只当普通客人就好,把你们这的五姑娘叫来我们爷要见她。”
孟掌柜见圆画大总管对福亥低三下四的,心想此人定也是个城中大官,可不敢得罪了,但又一想小月姑娘此时不在该如何是好?想了想又连忙低声回道:“二位爷真不巧,五姑娘家住胃土镇,今日已回了,怕是要等明早才能得见。”
福亥听后见天色已晚,心想不如就多等一日吧,他又想到刚才那一旁的醉汉自言自语的话,心中有些疑虑想去问个究竟,便对一旁的圆画说道:“你在这等我,去拿些好酒好肉到那桌。”说完手指向了赵厚德。
圆画连忙照办又吩咐孟掌柜快去准备,同时回道福亥:“不过一个醉汉爷何必上心?”
福亥见身边无旁人便小声道:“此人方才几句话道出了对国家的不满,我身为一国之主岂能不管?你去一旁等我,没我吩咐不许过来。”
圆画到一旁找个地方坐下候着,店小二又上来几道好菜和一坛美酒,赵厚德虽有些醉意但也知道这不是他要的,店小二连忙解释道:“这酒菜是这位爷给您加的。”
赵厚德抬头一看,是一位年长他几岁的人,一身华丽装扮气度不凡的立在眼前。
福亥开口道:“我陪阁下饮几杯如何?何苦一个人如此伤感!”
赵厚德连忙道:“您若不嫌弃快快坐下!”
福亥见眼前之人一脸黑相身材矮小,但听他刚说那几句话却话中另有深意,便好奇的问道:“方才进来时见阁下独自饮酒,话中却带有怀才不遇之感,不知遇了何事?”
赵厚德拿起坛中酒满了两碗,一手高举说道:“来,喝酒!”
福亥拿起大碗强忍着喝下,福亥平时可没有这么喝过酒,都是用城中精致的小玉杯来饮酒,且酒也没有这么烈,所以表情显得有些痛苦。
赵厚德见福亥喝光了碗中酒,叹了口气说道:“若说如何使得百姓安居、城中太平全存我心,若说如何上报国家、下抚黎民,百姓有余粮、城中无闲兵也全存我心。若说如何寻一栖息之所,遇一识才之人,却非我能左右也。”
福亥听后问道:“城中每年招贤纳士,阁下何不去一展才华?”
赵厚德无奈道:“我已连续三载皆因面相不善,未得施展便被赶了出来,早已心灰意冷。”
福亥惊讶道:“有这等事?今年试官何人?”
赵厚德道:“只听说是城中史家主管文试。”
福亥气得用力拍桌大声道:“岂有此理。”后又举起碗中酒二人一饮而尽。
两人都有些醉了福亥接着又问道:“阁下说使得百姓安居、城中太平都在你心里,可否说一说要怎样做才能办到?”
赵厚德已经醉了随口道:“百姓归附仁德之主,就如同水流向下入深渊,野兽藏于山林间,百姓若是安居不乱需遇到仁德之主,天之根本在国,国之根本在家,家之根本在人,这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安了城中才可太平无事。”
福亥听了反驳道:“如果真有那样的一国之主,只为百姓而活,那他的人生有何意义?”
赵厚德道:“人生的意义,就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是只为一己私欲而活着。”
福亥醉说道:“这样的一生真的有意义吗?我反倒不认为,人活一世不过是过眼云烟,在短短的瞬间里,只有抓住那一丝美好才不负此生,正如那天上的美月,你只有懂得欣赏它才有意义,天下是你的百姓敬仰你,万物都依附你,你为万物万事而存在,到头来你却丢了自己?倒不如学会去发现这世间的美好,懂得欣赏、懂得珍惜才更有意义。”
赵厚德无言以对,因为两人本就不在一个轨道上,此时两人都醉了,或许到了明日早就忘了今日所说的话。
圆画见国主喝多了连忙跑过来搀扶,一旁的赵厚德还醉着说道:“别走......再与我喝上几碗!”
福亥有些不胜酒力,已经站着睡着了,圆画连忙叫掌柜的道:“掌柜的,快去找一间最好的房我们爷要休息了。”
孟掌柜早就已经准备好,因为圆画经常来他这里,也知道圆画是城中办事的不敢得罪,故特意和其他客人调换了房间,把最好的一号房间腾出。
随后自己亲自带二人到了一号房间,又吩咐孟中仁把赵厚德扶上楼,就住在孟中仁平时睡的十四号房间。
这一号到十四号房间正好绕楼上一圈,一号和十四号又正好左右挨着,一号是这里最好的一间,有钱有势的官人来了都住一号房。
而十四号房间是最不好的又小又破,平时也就留给孟中仁住,房间不够时才腾出来给客人住。
这一夜只有圆画一夜未眠,他就站在一号房门外守着,万一国主夜里起来唤他不到,轻则总管位置不保,重则关进青牢甚是脑袋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