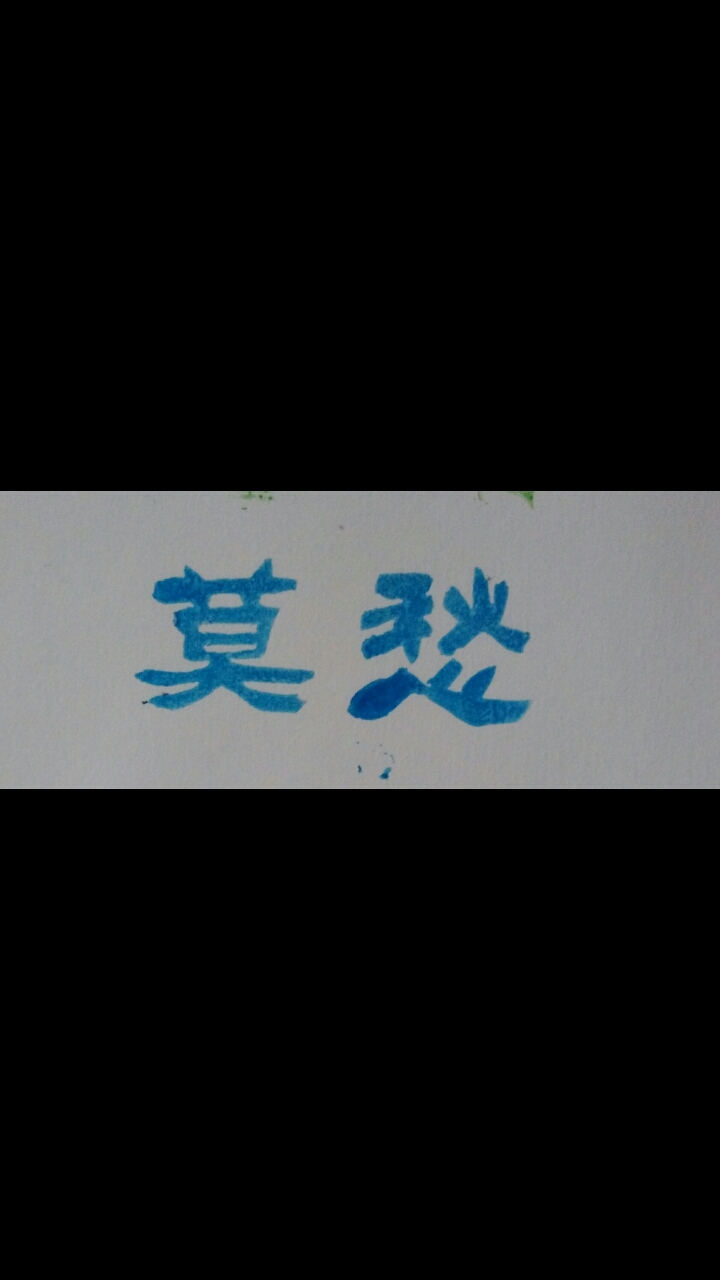老何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东北角的蜡烛,那火苗就象被风吹过,又象是被重击的人一样痛苦地扭动着身躯,抖了两下,倏地灭了!
老何惊惧不已,暗叫一声:“不好,鬼吹灯!”转脸又见马建设左手紧抓剑鞘,右手握住剑柄,正要将宝剑抽出,便厉声大喝到:“赶快放进去!鬼吹灯了,都不要命了?!”
被老何一声断喝,马建设惊得浑身一哆嗦,虽然很是舍不得,但还是乖乖地把剑放进棺内。
老何又说:“快把棺盖盖好。”
四人又忙不迭地一起使劲,把棺盖推回原处。我把那才得到的上半截圣旨卷住塞进包里,跟着丁志坚赶紧按原路往回跑去。
老何冲在最前面,马建设和丁志坚紧跟着,我跑在最后。穿过甬道,跨过金刚墙,跑过墓道,老何三两步跨上几级台阶,已经到了地洞的洞口。在石壁上的一个凹坑中摸到一个铁环,使劲一拉,发出一阵金属撞击岩石的巨大声响。洞口打开,竟有细小的沙粒不断流下来!
老何虽然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看见有细沙从上面的大厅流下来,知道这绝非好事,赶紧转头对着后面的三个人大喊:“赶快上,时间不多了!”
老何跟马建设、丁志坚三人连摸带爬地出了洞口,爬上了大厅的地面。等我往上爬时,细沙已经流到了脚下。从洞里通向上面大厅的这段坡道是上坡,脚踩在已经流淌着细沙的地面上,稍一用力,脚便随着沙子向后滑去,整个身体失去了平衡,重重地向前,狠狠地摔在地上,下巴猛磕在地上,只听见“当”的一声响,上下牙就以千钧之力,重重地撞击在一起,脑袋被震的“嗡”的一声,眼前一黑,眼看就要晕厥过去!
随即传来的钻心的疼痛刺激了将要晕厥过去的神经,我想大叫一声,可嘴却张不开,口腔内一股巨大的压力冲入鼻腔,两个鼻孔同时喷出滚烫的鲜血,眼前开始变得模糊。在失去意识之前,我用十根手指死死地抠进地面,指甲断裂的疼痛已经觉察不到了。恍惚中好像又看见已经上到地面的马建设跳了下来!
……
等我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大厅的地面上,老何和马建设、丁志坚围在我身边,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似乎想起了什么,看看马建设,问到:“我是怎么上来的?”
没等马建设开口,一旁的丁志坚就回答到:“是建设腰上拴了绳子跳下去抱起你,我跟何大哥在上面拉,这才上来的。”
我感激地看着马建设,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即又疼得呲牙咧嘴。
清醒的好处不太清楚,但坏处却显而易见:来自十根手指和一个下巴的钻心疼痛,一波又一波、没有丝毫间隙地冲击着大脑,就象是整个脑袋被塞进了火炉里。庆幸的是满嘴的牙齿和中间那根柔软的舌头还在。老何见我已经清醒过来,就对我说:“腿和脚没事就站起来,赶快离开这里。这里马上就要被沙子埋了。”
听老何说这里要被沙子埋了,我才打起精神,耳边传来沙子流淌的声音。循着声音我用眼睛搜索着,终于发现这声音来自大厅顶部正中的一个大洞。洞口直径不到两尺,正有细沙从洞里源源不断地流下来,在地面上堆起一个小山丘,再向周围流淌。通往底下墓葬的洞口还没关上,估计是流沙的机关被打开后,那个洞口就注定关不上了。
我抬头看了看那个往下流沙子的洞口,想起那里原先是有个圆形的图案,样子有点象太阳,还有点象葵花。原来这是整个流沙机关的塞子啊!是马建设拿起石棺里的宝剑时触发了机关,那骷髅头两个眼窝里冒出的绿光和突然熄灭的蜡烛便是信号。那脚下的震动其实来自头顶,和头顶传来的低声闷响一样,都是这塞子掉下来砸在地面上引起的。
流沙就是这地下藏兵洞和藏兵洞下面墓穴的防盗机关吧。但准确的说,这机关不是用来防盗的,因为人从外面进来时它并没有启动,而是有人在墓室内已经得手了才启动,这分明就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自杀装置!想到此,我不由得为这位蕲侯谷大成的阴狠毒辣所折服!
在马建设和丁志坚的搀扶下,我艰难地站起身。马建设又掏出纸巾把我脸上和手上的血迹擦了擦,现在也顾不上消毒、包扎了,能活着出去再慢慢来,先离开这里要紧。此时流沙已经快要流满整个大厅的地面了。
四人跑到出口那里,找到下来时放下的绳子,丁志坚打头,我第二,马建设第三,老何殿后,开始抓住绳子,一步步向上攀爬。
抓着绳子往上爬的时候,手指必须攥紧才能使上劲,所以每一次换手攥紧时,我都必须忍着剧痛,咬紧牙关。可是即便如此,每一次都疼得我浑身冒汗。等爬出洞口,丁志坚把我拉上去的时候,我的十指指尖已经血肉模糊,双手双臂也满是血污,身上的衣服早都被汗水浸透。抬头看看天空,月亮已经西沉,东方隐隐发白。
天快亮了。
一下一上,短短几个小时,现在想来却恍如经历两个世界。又呼吸到了带着青草气息的空气,这感觉真是太幸福了!此时我已经忘记了疼痛,展开双臂,躺在地上,昏昏入睡。
……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三件上衣。起身看时,已经天光大亮,但太阳还未升起。几步之外,老何、马建设和丁志坚生起了一堆火,三人围着火堆坐着。
马建设见我醒了,便过来搀着我坐到火堆边上。又用水壶里的水擦洗了我脸上和手臂上的血污,给十个手指都包上创可贴。下巴上的伤幸好没有大碍,只是皮肉伤,伤口也已经结痂了。
一转脸又看见那两只鬼魈,正倒在地上呼呼大睡,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赶忙问老何:“这俩鬼东西不会醒吧?”
老何也看了看两只鬼魈,说到:“每一只都被马兄弟扎了三支麻醉针,明天这时候能醒就算快的了。”
……
休息好了,又吃了点随身带着的干粮,四人便浇灭了火堆,一同下山。
由于我的形象过于狼狈,怕这个样子进城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就在城外不远处的一座废弃的民宅里暂时停留,马建设带着老何跟丁志坚进城给我买了衣服、碘伏酒精等药品,又转回来接我进城休整。
进了乐山城,不着急走,多逗留几天,我也好养伤。顺便把这次探墓的收获总结一下,再确定下一步怎么做。
这次共有四人探墓,有一人受伤,只是皮外伤,休息半个月就可以了。收获只有一件,就是那半张上半截的圣旨。其中的信息等回到北京后找到江教授再仔细研究。
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大家都听从了我的建议:先去北京,拜访江教授,把这一次探墓的过程向他汇报一下,看能从这张圣旨和其他信息中得出什么结论。争取让江教授启动早就已经立项的“明末清初大顺政权宝藏遗存情况的调查研究活动”,成立项目组,把老何、马建设和丁志坚吸纳加入项目组,用项目经费来保证每个人的经济收入和后续开展各项活动的开销。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在北京期间,带上老何的儿子好好玩一玩。下一步行动之前,先回一趟兰州,把孩子交给我父亲,让我父亲想办法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
半个月后,我的伤全部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四个大人和一个孩子,都胖了不少。看来,四川的水土养人,这话是真的。
……
去北京之前,我先给江教授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已经找到了圣旨的上半截。我准备带着完整的圣旨去北京,随行的还有几个伙伴。江教授在电话那头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
一行人到了北京,直接奔江教授家而去。我给江教授和同行的三位伙伴做了相互介绍,江教授让师母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招待我们。
吃完饭,来到江教授的书房。我把我们四人在霸王岭的探墓过程,给江教授做了详细的讲述。江教授听完之后连连称奇,并关切地询问了我的伤情。我笑着对江教授说:“年轻人,一点皮外伤不算什么。”
江教授听了感慨道:“真羡慕你们年轻人,那么重的伤,休息了半个月就自己好了。还可以跋山涉水,亲临实地,掌握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最真实的资料。不像我,只能钻在资料堆里,从史料中寻找答案。可史料也有真有假。就好比这个蕲侯谷大成,史料上记载,他死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大顺的永昌元年,是在山海关大战中战死的。可谁知道他的墓却在四川,并且至少活到了永昌十年,还是大顺永昌皇帝托以重任的六侯之一。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你们亲身犯险、亲下古墓的探险历程。所以说做学问不光要能够坐下来,还要能够走出去。只可惜我走不出去喽。”
我听了赶忙说道:“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长处,身体好,精力充沛。但也有不足,知识积累的少,经验不足,无法协调和统领大局。这时候就显示出您这样的老前辈的珍贵了。”
江教授摇摇头说:“什么珍贵不珍贵的,都是一些又老又朽的老朽罢了,充其量只能给年轻人提供点建议和意见,而且还是仅供参考的。”
我听出江教授似乎有隐退之意,便连忙说道:“您可一点都不朽,而且也不算老,好多重大课题还等着你主持呢。”
江教授听了笑笑说:“多谢你的夸奖:既不老也不朽。这几天我一直有个想法,想把几年前已经通过立项的那个项目重新启动起来,明面上由我牵头,实际工作由你来主持。”
我听了心中大喜,便假装糊涂地问道:“您说的是什么项目?”
“就是那个‘明末清初大顺政权宝藏遗存情况的调查研究活动’的项目。”
我也不推辞,反而向江教授提出要求:“是这个项目啊。我跑跑腿、干干力气活可以,大方向还得您来掌握,具体方案也得由您来制定。”
江教授摆摆手说到:“大方向我来掌握,可以。但具体的行动方案就由你来制定,毕竟你是做具体工作的。”
说罢,江教授看看我的眼睛问道:“你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见江教授如此问我,估计他也猜到了我的用意,便不再遮遮掩掩,直截了当的说道:“那能不能把我这三个伙伴吸纳进项目组?”
江教授反问道:“以什么身分进入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就以野外调查小组成员的身份进入。”
江教授沉思了片刻,郑重的答复我到:“可以,但你我之间必须有个君子协议,口头协议就行。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
“您说。”
江教授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可辨:“这个项目的工作性质是调查研究,而不是考古挖掘,更不是盗墓。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进入古墓。即便非要进入古墓不可,也不得破坏古迹、文物,更不许私藏文物。”
我点点头答道:“保证做到。”
江教授继续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最终调研报告形成之前,所有行动都悄悄地进行,不得声张。”
我点点头答道:“保证做到。”
江教授又继续说道:“为了规避风险,也是为了少惹麻烦,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暂时全部由你保管,等最终的调查研究报告形成之后再全部上交。”
我点点头答道:“保证做到。”
江教授如释重负般的拍了拍手说:“那就这样定了,我明天给学校打报告,申请正式启动项目。我是项目组的组长,你是项目组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
江教授说着,又问向了老何:“请问老何同志的全名是……?”
“我叫何林,何必的何,森林的林。”
江教授继续接着说:“设两个小组,一个是文史研究小组,我兼小组长;一个是野外调查小组,小组长是何林同志,马建设同志和丁志坚同志是组员。应该没什么问题,报告最多一周就会批下来。”
我真的没想到,事情办的竟如此顺利,既高兴又激动。于是站起身来,向江教授深鞠一躬:“谢谢教授,我们一定把工作做好,不辜负您和组织的信任与托付!”
老何、马建设和丁志坚也都站起身,向江教授鞠躬答谢:“谢谢江教授。”
江教授也高兴的站起来,笑着说道:“不要客气,不用谢,大家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嘛。”
坐下后,江教授看看我说道:“光顾着说这事了,居然忘了还有一件大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