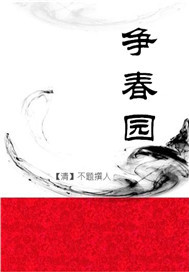长安到底是长安。
熹微晨雾之中,卢子岳还只远远看见长安城雄壮的城墙若隐若现,在略显阴郁的天空下,如一璧突兀而起的巨大山岩,就已难掩胸口的狂跳。
他老家在关内道安定郡,距长安数百里,父亲早年间从军时,曾到过长安数次,卢子岳却是呱呱坠地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巍峨的长安,准确的说,这也是他初次离家远行。
长安金光门城楼下,城墙高大,墙体斑驳陆离,年深日久风雨剥蚀的痕迹历历在目,却依旧厚重,稳若磐石。见得大唐虽已颓然,到底还有自己的根基在。
站在城墙下,卢子岳举首仰望,城楼廊柱硕壮,重檐深长,屋脊翘然,如一只蹲伏的巨鸟,羽翼舒张,俯首盯着进进出出的人群。
卢子岳仰头之际,只觉心胸为之一阔。暗念:如此宏大的长安,日后自己也要从这里起步,建功立业,成就心中壮志雄图。
他却没注意到,朱白相间的城楼和城墙的古貌颇为不同,彩绘簇新,瓦脊齐整,显是刚刚修葺过。他不知道,几年前,安禄山叛军退出长安时,曾焚毁了这座城楼,如今的城楼是依着旧样,刚刚修葺完毕的。
进到城门之内,街道平坦如砥,宽度竟达百余丈,两侧坊墙高耸,眼见得屋连瓦接,广厦千万,高楼如林。长安的繁盛虽远不及开元盛世之时,但到底是天下第一城,仍旧喧闹得令卢子岳目眩。人群熙攘,各色人等,衣饰各异,神采迥然,或步行,或乘马,或坐车,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乃至远域他国,各揣目的,各依自己命运的指引,汇聚到这大唐之都,天子之所,塞街填衢,令宽敞的路面,也变得拥挤不堪。
卢子岳的目光总被一些高头大马之上的人吸引,这些人中,有些人衣锦着绣,气度雍容,一派贵胄做派。尤其其中常有一些艳丽女子,肤色胜雪,眉目如画,簪金插翠,衣袂飘香,缓辔而驰,飘然如霞光,耀人眼目,让一个初入长安的僻地少年,禁不住神驰魂迷。
卢子岳满心满目都被长安城的五色之光眩惑,却怎么也想到,两日之后,他却成了万年县大狱中的阶下囚。
卢子岳跪在地上,眼前一个眼神尖利、神态冷漠的人,高坐在正中,服色显然是一个官员,与与之前审问他的人皆不相若。卢子岳无法根据服色分辨官府中人身份,在家乡,他从未进过衙门。一则,卢家自高祖皇帝时,就代代为府兵,戍守陇右。府兵与地方官长,互不统属,难得打交道;二则,家中长居军镇,到州县要翻山过岭,去一次倒比一年一度过的元日还要稀罕;三则,卢子岳幼年常住在崆峒山,随一位道士师父学文习武,下山时也多是回家探省,两三年也进不得一次城市,怎能晓得官府中人如何行事。况且他家乡深处僻地,官府中人服色也驳杂邋遢,原不如长安城中的公差如此服饰鲜明,这两天忽然看到这么多不同服色的观察,卢子岳也一时分辨不清。但此时坐在堂上这个人,卢子岳却看得出,绝非一般差役,所着是官服,品级颇高。
男人盯着卢子岳,手里举着一件小小的东西:“嘴挺硬啊。“随即语带轻蔑地说:”不过,你进错门了。进了这里,再硬,也熬不过去。说说,东西哪里来的?“
卢子岳说:“大人,我早已和各位老爷说过,我不知道,我是冤枉的。”
那人说:“你不招,不过是多受苦,别想着熬下去,就出得了这个门。 “
卢子岳只顾哀诉说:“小人句句是实,绝无虚言,求大人明鉴!”
“你冤枉,那为什么这东西在你身上?”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东西,是深夜之中,在路上捡到的。”
“呵呵,”那人冷笑着:“捡的?深夜之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怎么这么巧,就让你捡了来。我劝你你还是说实话,免受皮肉之苦。我看你这少年,年龄尚小,相貌忠厚,大约也是受了坏人指使,误入歧途。只要你如实招来,供出同伙,本官自可法外施恩,若能帮我们抓住元凶,我保证放你出去,如何?”
卢子岳低头沉默。他的确没有说实话,他知道这个东西的主人是谁,那是两日前他刚刚认识的一个女子,然而,他却不愿说出她的名字。
遇到那女子时,卢子岳正在西市行人中目不暇给,忽听得一阵争吵叫嚷之声传来。循声望去,只见一群人围做一团,卢子岳好奇心起,挤进人堆。
人圈之中,却只见八九个人站在一处,最前面一个衣着华贵的中年男子,站在一位女子面前,听他正说道:“今天爷没了面子,你要是陪爷喝一杯,看你乖不乖,爷一高兴,没准就放你走。否则,今儿你哪也别想去。”
那女子面若井水,沉静无波,只淡淡地说:“爹爹还在家中等我,恕小女子难以相陪,还请让我过去。”
卢子岳此时站在女子侧后,只能看到她的本张侧脸,目光却已全被女子吸引过去。这女子衣着淡雅,一件素花长裙,简简单单梳着椎髻,服饰打扮虽平平无奇,却自有一种意态,若春日柳丝,微风轻拂间,摇曳出尘。面对一群嬉皮笑脸的男人挡在面前,并不见仓皇恐惧之态,只沉穆以对。卢子岳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女子,竟如中酒般仿佛有了几分醉意,一时迷离恍惚起来。
一个跟着中年男子后的人,此时帮腔道:“你撞了我们爷,要是别人,早打个半死了。稀罕你,让你喝个酒,赔个罪就过去了,怎么这么不识抬举!”
围观人众,有的对恶徒街头调戏女子颇为不忿,却敢怒不敢言,只远远围观,有的摇头叹口气,远远走开,眼不见为净。有人却乐得看热闹,瞧着娇弱女子的窘态,一副津津有味,幸灾乐祸的嘴脸。
卢子岳虽不了解来龙去脉,也看出几个人是市井泼皮,在故意骚扰为难这女子,忍不住越过人群,向前踏出。
此时,围在中年汉子身边帮闲的人中,一人走到女子身前,伸手抓住女子胳膊:“走吧,别扭手扭脚的。”
话音未落,一只手已搭在此人肩膀上,一个声音道:“放尊重点!”
那帮闲泼皮转过头来,看着卢子岳正站在身边,眼见是一个打扮颇为土气的乡间少年模样,气不打一处来,喝道:“哪来的乡巴佬,跑这里来出头!”
那衣着华贵的中年男子笑嘻嘻地问女子:“你相好的?这粗苯的货色哪配得上你。”
女子一言不发,卢子岳倒感觉脸上略略发烫,说:“我……我不认识她。你们不该欺负她,这天子脚下,总要有王法。”
几个泼皮大笑起来,那华衣中年汉子笑道:“王法,要王法是吧。长安到处都是王法,你算来对地方了!”
话音未落,那人一脚踢出,腿法凌厉之极。
一般人抬腿踹人,不过是小腿发力,踢人小腹,扫人下盘,此人却腿高劲猛,左腿直踢卢子岳太阳穴,全身劲力丝已灌注腿上,如一根粗壮的棍棒,猛挥而至。这一下若被踢到,只怕轻则昏厥,重则伤人性命。
卢子岳却比他更快一步,腿未到,已抢身向前,对那条攻来的腿不躲、不隔,一拳挥出,“嘭”的一声,拳头正中面门,此人腿尚在半空,人已仰面跌倒。
又是“嘭”的一声,那人已跌落尘土,砸得灰尘四扬。
旁边七八个泼皮发一声喊,攘臂挥拳,一起向卢子岳身上招呼。
仿佛片刻间的事,卢子岳左拨右打,腿盘肘撞,七八人已纷纷倒地,哀叫之声此起彼伏,尘土扬起一人多高。看热闹的人慌得到处退避,有的慌不择路地奔窜,前面人撞到后边的,几个人摔在一处,叠压推搡,场面更加混乱。一条街上,瞬间人喊马嘶,乱做一团,各个纷纷远避。只剩下几个胆大的,站在墙角、檐下,远远张望。
忽听得人大喊:“谁敢跑到西市来闹事,全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