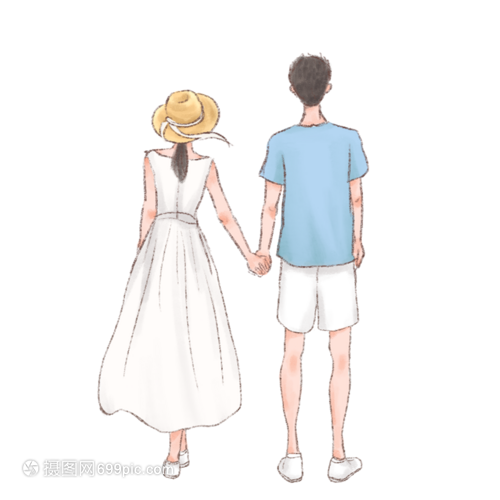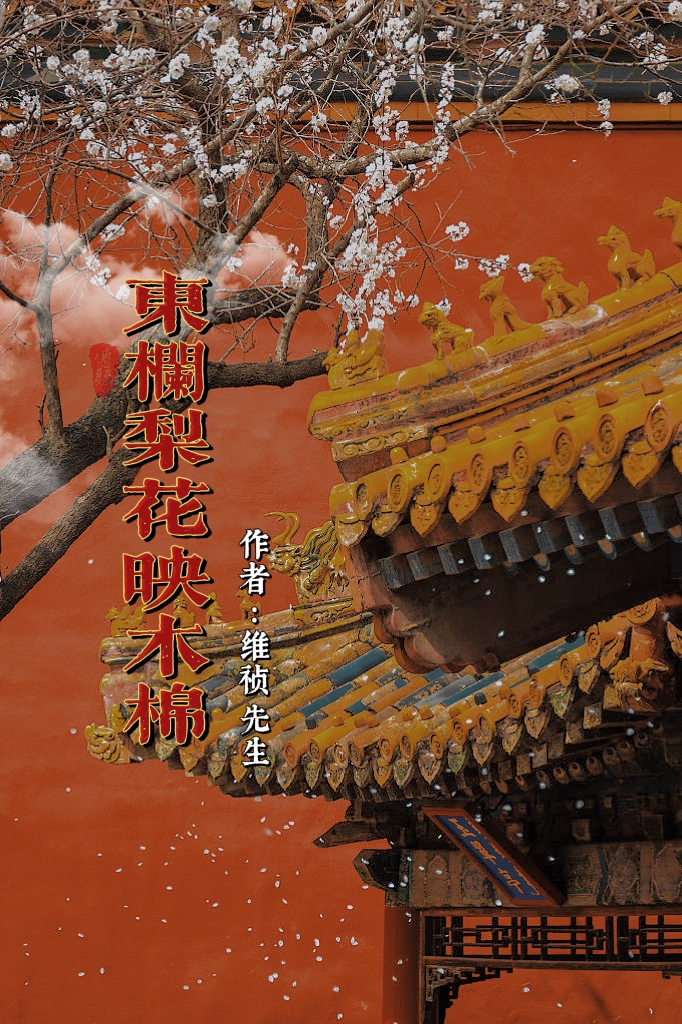几天之后小琼一人来到了沈阳,我和姜恒、秦青到火车站接的他。
我对小琼说:“就一个人来了?小瑶呢?”
小琼说:“她不打算考外省的学校了,准备在省内念。”
我说:“哦。”同时在心里松了口气。
小琼来后的第二天,沈阳就下起了大雪,那场雪下的真的很大,至少在我的记忆里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后来听新闻说,那是建国以来沈阳最大的一场雪。
那天房间里只有我和母亲,其他人都去考央美了,我没有报考,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考上。呆在房里看着窗外飘落的大雪花,我忽然想起韩絮说过,她希望我每年都能陪她在下雪的时候去看海。我激动的拿出手机想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沈阳这边下大雪了,但是我忘了,沈阳没有海,韩絮的手机号码也早已经换掉了。
我拿出速写板,在纸上试图画出韩絮的样子,但是怎么画都不像,脑海中她那动人的面容,让我难以捕捉。这时我才发现,对于韩絮的样子,我已经开始模糊了。我翻看手机里韩絮的照片,每一个微笑都让我心旷神怡,觉得她就在身边,一想到这,我就觉得自己有了动力,一时间仿佛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我可以成为拯救世界英雄,我变成了内裤外穿的Superman,但当我正视现实,发现我和韩絮没有未来的时候,我这个大英雄的心又忽然脆弱起来。我清醒的认识到,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一个前途未卜的穷小子,在这个世界上挣扎的活着,盲从的来到沈阳,盲从的报考着中国由南至北的各种学校,以为自己正在挑选理想的大学,其实我们都不是在对大学进行挑选,而只是在被各个招生院校调戏。
当小琼看到我一摞准考证的时候,他吃惊的说了一句:“我靠……”
我问小琼怎么了。
小琼反问我:“这一摞都是准考证?”
我点点头。
“都是你的?”
“是啊,怎么了?”
小琼叹了口气说:“我疏忽了,我应该嘱咐你的,不要报考太多的学校。”
我说:“是啊,我都考恶心了,每天来回的折腾,身心疲累啊。”
小琼说:“不只因为这样的考试耗费体力,你知不知道,其实来招考的大部分学校都是为圈钱而来的,他们有一些学校只给辽宁省考生三四个录取名额,然后招了很多人去考,其实能考上的只有三四个,其他上千人全都是炮灰,说白了这些学校就是来赚报考费的。”
让小琼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一群傻逼,并且傻的让人发自肺腑的怜悯。
小琼接着说:“就这一摞准考证,以你长期考试而导致的糟糕状态,能有两个学校给你下证就不错了。”小琼的话让我又觉得“前途无亮”了,我当时真的好想哭,似乎生活都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晚上我问我妈,有没有想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
她说:“现在不要想这些,等你真的考不上的时候再说吧。”
时间消耗着我的战斗力,在沈阳接下来的日子对我来已经没有意义,我如同一具行尸走肉,每天提着画箱画板进出于考场内外,我对我妈说,我不想再考了。她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回答。在经历频繁的考试之后,不只是我的身心俱疲,我妈也跟着消耗了很多精力和体力,在我们的身心都疲惫的时候,情绪非常容易激动,所以在沈阳的后半段日子,我和我妈的关系一度很紧张。她爆发了强大的控制欲,而我疲于奔命,烦躁至极。所以当她问我为什么不想再考了的时候,我已经预料到任何说辞,最后只能演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口水战,消耗我更多的战斗力,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有说。那时我妈就是我的最高指挥官,她每天负责给我报考,计划我的将来,而我要做的就是按她的要求去做,至于我的承受能力,则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终于在我即将要崩溃的时候,鲁迅美术学院的考试结束了,它是最后一个招考的学校。考试一结束我就从考场里冲了出来,我用力握着手中的画板和画箱,我想把他们统统捏碎、摔碎、砸碎,但最后我没有那么做,毕竟是陪我征战多场考试的兄弟,我打心底舍不得。正当我在思考该如何发泄的时候,在我身边冲出了一个兄台,只见他昂着头朝着天一顿叫骂,然后他把画箱“轰隆”一声摔在了地上,画箱里的画笔,调色盒全都掉了出来,这位兄台毫不犹豫双手握拳,高高跳起,然后双脚重重的落在这些美术用具上,多次重复这组动作后,他变成了单脚跺,嘴里仍然念念有词地不闲着。一箱子工具在短短的几十秒内,被踩的稀巴烂。
我在一旁看着,小声嘀咕了一句:“真他妈爽。”
姜恒也从考场里出来了,看见我就跑过来撞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他大爷!他二大爷!他三大爷的!终于考完了!啊……!!”他用力捶着胸,“啊啊啊啊……”的怪叫着,我笑着看着他兴奋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姜恒这么狂野的行为。
这时我发现一个提着画箱和画板的女生哭着扑进了一位母亲的怀里,她的母亲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那一刻,我突然也有种想哭的冲动。
专业考试终于结束了,但重头戏还没有上演,在经历了专业考试的一段磨砺后,还有高考在不怀好意的等着我们,等到高考结束后,等到那一天,我们才可以彻底放声地嘶吼,大声地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