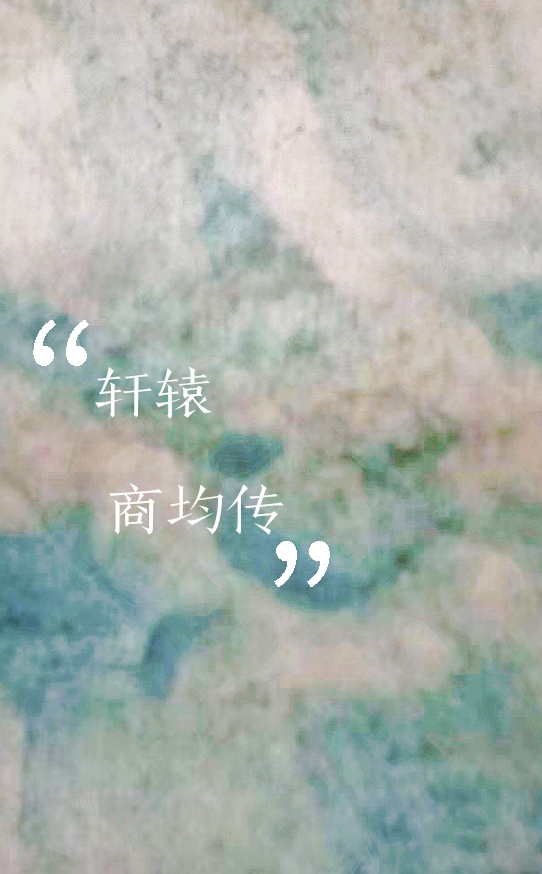那天下课后我们四个人在画室里迟迟未走,整个教学楼里除了看门的大爷,就只有我们几个。大家搬来凳子围坐在一起,二爷掏出了一盒中南海点8,帮大家都点上,画室里立刻烟雾弥漫。天色开始变暗,大海刚把日光灯打开,就被二爷制止了。
“把大灯关了,咱们这聊事儿呢,点这个。”二爷说着把静物灯拖了过来,开关一按开,一束又粗又亮的灯柱就把我们几个人都罩住了,在这束灯光下,我们的面目和烟雾瞬间变得清晰。
“我操,有点热啊。”二爷说着把静物灯又推远了一些,接着说:“这事儿,绝不能这么算了,郝乐,我知道这事儿和你关系不大,但是今天让你下课留下来,是因为我很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能不能用最小的代价还能帮咱把这仇给报了!”
我说:“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啊,这怎么能说和我关系不大呢?撬我哥们儿的媳妇就是撬我的媳妇,盗我哥们儿的账号就是盗我的账号,这事儿咱几个绝对要把他办了。秦青,你怎么看?”
秦青眯着眼睛吐出一个烟圈说:“我还能怎么看啊?必须办他们啊,他妈的这帮人太过分了,那可是我们的劳动果实啊,我们逃课,花钱打了那么久的装备,绝对不能就这么便宜那几个小子了,大海,你说呢?
大海直了下腰,拍了拍他那微微颤抖的大胸脯肉说:“我觉得郝乐说的对,就按他说的办吧!”
大家都说:“成,那就这么定了!”
我有点蒙:“等会儿,我说什么了啊?”
大海说:“你不是说办他们吗?”
我说:“是啊。”
大海说:“那就办啊。”
我说:“我是说要办啊,可怎么办啊?”
大海说:“办就是办啊,都要办了,怎么还怎么办啊?”
我说:“是要办啊,但不能就这么办啊,这么办咱办完以后怎么办啊?”
大海说:“要办就办啊,哪还管办完以后怎么办啊,没听说过办人还考虑办完以后怎么办的。”
这时二爷插话了:“行了,行了。我看你们也没什么主意啊,一点建设性的意见都没有,平时就玩游戏,也不看点书长长见识,这点事儿都办不了,传出去都让人笑话。”
秦青说:“得了,别卖关子了,你说那么欢,有什么主意啊?
二爷故作神秘的沉默了一下,随即猛吸一口烟,把烟雾吐向我们,眼睛环视了我们三个一遍,再把烟蒂丢到地上用脚踩灭,然后说:“我他妈哪有什么主意,我有主意还用问你们有什么想法啊。”
二爷话音刚落,我们三个同时“操”了一声。
“要不这样,”二爷接着说:“咱今晚都回家琢磨琢磨,把自己的计划都写纸上,明天还是这个时候,咱还是这个老地方,再讨论,怎么样?接头暗号,记住了:‘青山不改,绿水长……”
还没等二爷说完,秦青就站起来把烟掐灭了,说:“得,得,得,赶紧撤吧,还有一妞约我吃饭呢,明天再说。”大海的肚子随即发出了巨大的咕噜声。
十秒钟后,画室里恢复了先前的安静,教学楼里唯一的光亮消失了,夜幕降临,只剩一片烟雾在画室里慢慢消散。
第二天放学后,我们四个人心照不宣的留了下来,又是此时,又是此地,我们面面相觑。二爷又掏出一盒点8,帮大家都点上。
“把计划书都拿出来吧。”二爷说。
我们把各自的计划书都掏了出来,递给了二爷。
“你们这字写得可真够累眼的,不能大点写啊。”二爷嘀咕道。
我说:“瞅你那眼神吧,给我吧,我看看。”于是二爷把几张褶皱的纸递到我的手上。
“先看二爷的。”我说:“二爷的计划是,咱弄两箱麻油,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咱就去把胡同给点了。”
话音刚落,秦青就说:“咱先说好了啊,杀人放火的事儿我可不干,再说,买麻油放火,你倒够有创意的,卖麻油的给了你多少钱啊?那玩意儿倒多少能点着啊?”
大海说:“是啊,这事儿绝对不成,买汽油还靠点谱,但油价可不便宜啊,听说今晚过了12点又得涨呢。”
于是二爷的这个计划因为太黄太暴力和造价的原因搁浅了。
我说:“那接下来看看秦青的计划吧。”我翻了一页,接着说道:“秦青的计划是,给公安局写封匿名举报信,举报这个网吧完全不符合营业标准,常年接待未成年人上网。大家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
没等大家发表看法,秦青就抢着说:“我跟你们说,我这个计划是最稳妥的,只要这封举报信一捅上去,绝对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不用一个礼拜,‘胡同’肯定会在群众的强烈谴责和社会媒体的大肆曝光中自己歇业的。”
二爷说:“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情书收多了啊,弄个计划都像写情书一样。”
我说:“这个计划,我看也不行,你想啊,‘胡同网吧’既然能长期的生存于黑暗的胡同里而不被人查封,那一定是有人罩着啊,有人罩着它才会黑的,所以可以看出‘胡同’的后台很硬,举报信这种废纸一样的东西是办不倒‘胡同’的,搞不好还会被‘跨省’,这个风险太大了。”
于是秦青不说话了,我翻到大海的计划,可大海的那张纸上只有一个字:办他!
我把纸翻过去,背面什么都没有,又翻过来,瞅瞅大海说:“没了?”
大海回:“是啊,没了。废他妈什么话,我觉得咱就找个机会,给那几个网管套上麻袋,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踹,这是最解恨的。”大海边说边比量着,看他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大海的这个计划倒是很干脆,至少相比秦青的计划是这样的,但这个计划最后还是搁浅了,搁浅的原因也很干脆——我们谁都不敢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