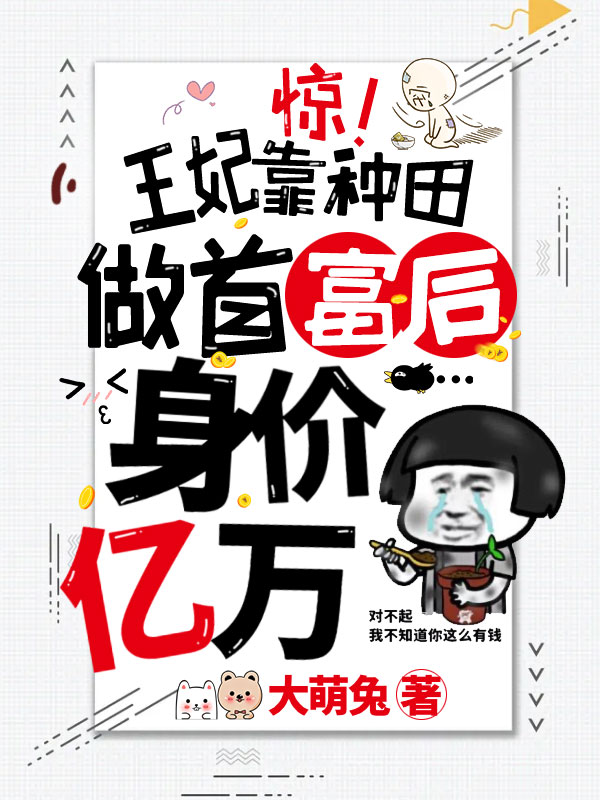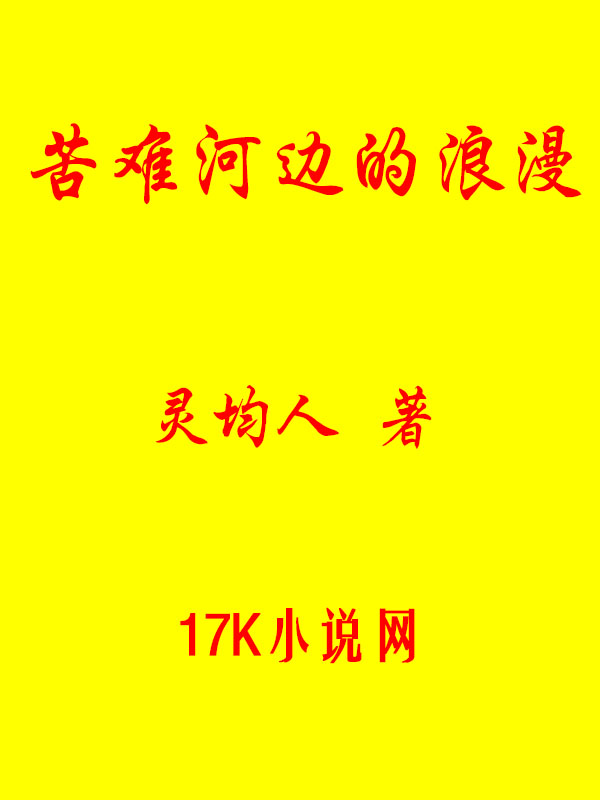天微微亮,柳念真就起了。
厨房里鸡鸭鱼肉都准备好了,只等她亲自动手。
柳念真是娇养的姑娘,平时并不下厨,但作为家里的长女,父亲生病妹妹不舒服时,柳念真都会亲自下厨做几道小菜孝敬父亲照顾妹妹,渐渐地就练了一手好厨艺。每年逢年过节,还有祭祀用的菜肴,都是她掌厨的。
酱鸭最费功夫,得先做这个,柳念真熟练地切好姜蒜放进锅中,再将焯过水的鸭子加进去,沥入红曲米水,跟着加入绍兴酒酱油并盐糖,添水淹没。
小丫鬟旺火烧沸,之后改成文火慢煨。
柳念真再去做白斩鸡,因厨房里热,她鼻尖额头冒出了细汗,俏脸红润,看得帮她打下手的嬷嬷挪不开眼睛,心里唏嘘。大姑娘出落得越来越像夫人了,貌美贤惠,读书习字能上厅堂,厨艺娴熟绣活精湛,夫人在天有灵,就保佑准姑爷这次高中举人吧,将来姑娘做个举人娘子,甚至当上官夫人,才不白搭这副好品貌啊。
“小点火,别让水开了。”鸡肉进锅,慢火烫两刻钟就差不多了,柳念真轻声叮嘱小丫鬟,再去准备走油肉。
柳汐音顺着饭香凑过来时,柳念真正在煎鲫鱼。
“好香啊,姐姐。”柳汐音站在门口,闻着里面浓浓的香味儿,口水快要流出来了。
柳念真一边给鱼翻身一边擦汗,扭头叮嘱妹妹,“这里烟重,汐音先去堂屋等着,姐姐多做了一条,一会儿给你吃。”
妹妹嘴馋,闻着味儿了,若是不给她,这一路妹妹都得惦记着食盒。
马上就能吃到姐姐亲手做的东西了,柳汐音心满意足地去了堂屋。
柳鸣九已经在走廊里站了许久了。
明天便是中秋,县学放假三日,倒省了他特意告假。
看着长女在厨房里忙碌,小女儿贪嘴地跑过去,柳鸣九不由记起妻子在世时,她系着围裙在厨房做菜,五岁的柳念真眼巴巴趴在门口,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娘亲。他抱她进去,小丫头目光就落到了锅里的煎鱼上,吸着口水要吃。妻子疼女儿,做好了先不装盘,专拣没刺儿的地方夹一块儿,吹凉了再喂女儿,眉眼温柔……
他想她,想快点下去找她。
可是他不能,他得努力活着,至少要撑到长女出嫁。
用过饭,柳念真戴上帷帽,牵着妹妹跟在父亲身后出了门,柳汐音还小,还用不上帷帽。
柳家有两辆骡车,柳鸣九先将一对儿爱女扶上车,他再拎着食盒上了前面那辆,坐稳了,两辆骡车稳稳地朝城西的翠屏山驶去。
翠屏山不高,绵延数里,山脚有条三丈来宽的溪流。两辆骡车停在溪边,柳鸣九扶了女儿们下来,命秦风在这边守着车,他与柳念真柳汐音走在前头率先踏上石桥,秦叔提着食盒与绿珠跟在后头。
秦风站在骡车前目送他们,等几人进了山看不见身影了,他才将一头骡子栓到树上,另一头拴在车后,这样万一有人趁他打盹时来偷骡子,都会惊动他。栓好了,秦风瞅瞅两个姑娘的骡车,挑开帘子闻了闻味儿,这才回到前面那辆,躺在车帘外头打盹。
老爷这一去得晌午用完饭才出来,不睡觉做什么?
躺着躺着,骡车突然一阵晃动,秦风揉揉眼睛坐了起来,下去瞅瞅,见周围没人,打着哈欠拍拍后面的骡子,“老实点,再乱动回去不喂你,饿你两顿你就好受了。”
骡子甩了甩脑袋。
秦风继续去前面躺着。
半晌过后,后面那辆骡车里,一只修长白皙的手飞快探出,悄无声息将外面藏青色的垫子翻转过去,遮掩了上面一块儿血迹。换好了,那手又迅速收回,一片死寂,仿佛车里根本没有人。
山上,柳家父女已经到了地方。
郁郁葱葱的林木丛中,一片空地被人建成了石墓,外头罩着四角凉亭,遮风挡雨。
江南树叶黄的晚,此时山里依然一片碧绿,但绿叶也会掉落,被风吹到凉亭里,一地斑驳。
柳鸣九接过绿珠手中的笤帚,亲自为妻子扫墓。
柳念真领着妹妹去拔草,因为身边都是自家人,她将帷帽摘了下去。
不远处的一片土包后,王介休眼睛一亮。
亭子里两个姑娘,小的还是孩子,没什么好看的,大的那个虽然才十三,个头却比寻常女子高挑些,一袭素白裙子,弯腰起身间,现出双手可握的小腰,等她站直了,山风迎面吹来,吹得她衣裙贴身,胸前竟也颇为壮观,瞧着比他那个十五岁的通房还要丰润。
再看她的模样,黛眉轻簇含愁,清泉般的眸子仿佛会说话,看向石墓时让人疼惜,柔声细语与妹妹说话时又有解语花般的温柔,特别是那口酥软的娇柔声音,真是不用看人,只要听她喊声好哥哥,他身子都得酥半边。
这样的美人,既然遇见了,他若不想办法弄到院中,岂不是辜负了这一番良缘?
王介休越看越痒痒,忽的听到身后有动静,却是贴身长随也伸着脖子望呢。王介休已经将美人看成囊中之物,又岂会纵容下人窥视,一个冷厉的眼神递过去,那长随顿时缩了脖子,不敢再看。
柳念真并不知道山里有恶狼,她跪在母亲的墓前,泪如雨下。
母亲生妹妹时怀的是双胎,妹妹生下来了,弟弟没能……
那时她才六岁,七年下来,柳念真已经记不得母亲的样子了,忆起母亲时的思念也一年比一年淡,但每次过来祭拜母亲,每次看到父亲对着墓碑发呆,她都忍不住哭。
柳汐音跪在她旁边,看看姐姐,再看向墓碑,想到旁的伙伴家里都有娘亲疼,眼眶也湿了。
洒酒上香,磕头祭拜,焚烧纸钱。
日头不知不觉升到了正中间。
柳汐音肚子叫了起来。
柳鸣九视线终于从墓碑上移开,咳了咳,对姐妹俩道:“摆饭吧,咱们陪你们娘一起用。”
绿珠将食盒提了过来。
饭菜还是温的。
柳汐音人小,因为从小就没有母亲,悲伤来得快去得也快,端着碗吃得饱饱。柳念真与柳鸣九都只是勉强动了几筷子。吃完了,柳鸣九让柳念真领着妹妹先随秦叔绿珠下去,他一会儿再跟上来。
柳念真知道父亲有话要同母亲说,戴好帷帽,牵着妹妹走出亭子,停在下面一片竹林前等父亲。
柳鸣九并没让女儿们等太久,也就一盏茶的功夫就下来了,走几步咳嗽一声,在山林里传荡。
一行人很快就消失在了王介休的视野内。
“大人,咱们也走吧?”长随拍拍膝盖,试探着问。
王介休摇摇头,“他们病的病小的小,走不快,咱们多等会儿,别叫人看到。”
看到了,这荒山野岭的,他没法解释。
长随望望山下,好奇问道:“那大人准备如何纳江姑娘啊?我昨天打听过了,柳鸣九在县学教书十年了,不少子弟都得过他指点,因此柳鸣九在县里名望极高,江姑娘定了亲,大人若是用强,恐怕会影响大人的名声啊。”
王介休笑笑,没有回他。
他当然不会坏自己的名声,但他有的是办法,让美人心甘情愿从了他。
“回去再仔细打听骆家的事情,晚饭前回我,事无巨细,我都要知道。”
长随连忙应下。
柳念真等人则走到了溪边。
秦风陪着来过好几次了,时间估摸的极好,提前下了车,解开骡子,精神抖擞地迎接老爷。
柳鸣九先将小女儿抱到车上。
柳汐音掀开帘子,视线还没从父亲身上收回来,人已经被一股大力扯了进去。
柳念真捂住了嘴,绿珠惊叫出声。
“再敢出声,我马上杀了她!”
车厢里面,一个男人浑身是血歪靠着车窗,双眼紧闭,仿佛死了,又好像只是昏了过去。抓着柳汐音的男子看起来与那人年岁相近,二十左右,一身黑衣,冷峻脸庞却面如冠玉,一双星眸冷冽危险,平静又毫无商量余地地看着柳鸣九,“照我说的做,事成后我们悄然离开,不会给你们添任何麻烦,否则我现在就杀了她!”
柳汐音头回遇到坏人,吓得呜呜挣扎,眼泪流下来,晕开男人手上的血,平添狰狞。
柳鸣九与他对视片刻,冷静应道:“好,我听你的,只是小女年幼怕事,可否换我上去?”
黑衣男人冷笑,无声拒绝。
柳鸣九皱眉,看着车里浑身发抖的小女儿,心如刀绞。
“换我行吗?”柳念真白着脸上前。
“念真!”柳鸣九剧烈地咳嗽,拦住女儿不许她犯傻。
柳念真摇头,泪眼模糊地对着车里的人哀求:“换我上去,你放我妹妹下来?她太小,不懂事,哭闹起来可能会引人怀疑,只要你放了她,我不哭不闹,求你了……”
她头上戴着帷帽,黑衣男人看不清她模样,不过看身段听声音,也知道是个娇弱姑娘。他低头,见怀里的小女娃哭得都发抽了,心中厌烦,便命柳念真上车:“你先上来。”
柳念真作势就要上去。
柳鸣九本能地拽住女儿胳膊。
“爹爹放心,我听他们的,他们不会伤我的。”怕父亲担心,柳念真尽量收住泪,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些。其实她哪里敢确定对方不会伤她?但妹妹在他们手中,柳念真宁可自己受伤,也不忍看妹妹受苦。
柳鸣九心里天人交战,最终还是松了手,咬牙看向车里的人,“你若敢伤我女儿半根头发,我拼了命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黑衣男人懒得多做解释,看看身后同伴,冷声催道:“动作快些,若他出事,我要你们一家陪葬!”
柳鸣九不敢耽搁,将瑟瑟发抖的长女扶上了车。
“不许哭,哭一声我就杀了你姐姐!”黑衣男人先威胁怀里的小姑娘。
柳汐音依然哭个不停。
柳念真心疼死了,凑过去安抚妹妹:“汐音不哭,你不哭了,他就放你下去找爹爹。”
姐姐温柔的声音近在耳边,柳汐音终于平静了些,抽泣着点头,可怜极了。
她们姐俩商量好了,黑衣男人试探着松开柳汐音的嘴,确定她是真的不哭了,他才粗鲁地将柳念真扯到怀里,松开柳汐音对柳鸣九道:“马上去你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若露出半点异样……”
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把匕首,扯开柳念真头上碍事的帷帽,看也没看柳念真,先将匕首抵住她脖子。
柳念真垂眸看那匕首,感受着隐隐碰到自己的锋利刀刃,大气都不敢出。
柳鸣九看得心都悬了起来,还想再叮嘱女儿两句,黑衣男子又催了一遍,他不敢再流连,抱着小女儿,示意秦叔赶后面的车,他匆匆去了前头。
前面骡车动了,黑衣男子才放下车帘,收起匕首,猛地推开柳念真,“老老实实坐着,敢……”
说到一半,忽的没了声音。
柳念真歪倒在车板上,心里怕得不行,听男人顿住,她不由抬头,却见男人直勾勾地盯着她……
柳念真心头一跳,她知道自己生的好,难道他……
念头一起,柳念真越发怕了,抢过掉在一旁的帷帽戴上,低着脑袋瑟缩在车厢一角。
但她能感觉到,黑衣男人依然在看着她。
柳念真浑身发抖,手不安地攥紧袖口。
黑衣男人目光扫到她手上,停顿片刻,移开,撩开衣摆。
“你做什么?”柳念真吓得魂飞天外,警惕又绝望地问,若他动了不轨之心,她宁可死!
黑衣男人没理她,径自割下干净的里衣,转身去为同伴包扎。
柳念真身体一松,背后冷汗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