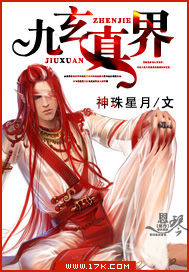那天我抱着小娃娃刚到枣树下,就看见一群五大三粗的男人推攘着以北,将他扔到牛车上。
以北也不说话,也不挣扎,怀里的陶笛掉落在地上,被人一脚踩得碎成了好几片。
驾车人一鞭子甩到老黄牛的背上,“哞——”的一声直奔向祭坛,扬起的尘土凝成一片云,好久才散开。
“男生女相,指不定什么妖物,这下好了,白送也没人要!”阿爹啐了一口痰,骂骂咧咧地给了我的头一巴掌,招呼着我带着不周去打猪草。
那个男人不要不周,要将她扔到路口给牛车碾死。阿姊哭着喊着,跪坐在地上抱着他的腿死死地哀求,他也不肯松口,只是嘴里骂着“都是赔钱货”,一脚接着一脚更大力气地踹上阿姊的肚子。
最后还是阿娘看不过去了,拿了一袋子米把她买了回家,让我带着。
不周在我的背上听话的很,时不时地会用小小的手指戳我的脖子,然后见我扭头看她,傻呵呵地咧开嘴笑。
还是小娃娃好,什么也不用想。可我不是小娃娃,我在想着以北。
不只是阿爹,镇上的人都说他是妖物,就是因为他来到镇子上,才导致阿姊生不出男娃娃。有人说要找来白胡子的大祭祀祈祷,然后烧死这个妖物来祈求神灵保佑。
保佑人丁兴旺。
我偷偷去找了白胡子大祭司,他很好说话,笑眯眯地在我脸上身上摸了一把,就放我去见了以北。
以北被钉在木架子上,垂着脑袋跪坐着,乌黑油亮的头发就轻飘飘地悬浮在空中。
这里很黑,木架子上有一扇小窗,阳光便会带着灰尘从那里挤进来,落在以北的身上。
他还是穿着那一身麻布衣裳,干干净净的,一点灰尘都没沾上。只是被绑着的手腕上,错错落落的都是血,还在淅淅沥沥地往下流,落在地上“吧嗒吧嗒”的,清脆入耳,像极了他吹的陶笛。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看着就想哭。
他不该这样的,他明明那么温柔,他合该吹着陶笛,悠悠然走过小镇。
“含山,别哭,我要走了。”以北抬起头,我第一次看见他那双藏在头发后的眼睛。
一片白,分不清眼珠子在哪里,我却偏偏能看见,那里面荡漾着温柔。
澄澈分明。
好似那日正午阳光穿过树梢,我打完猪草匆匆忙赶来,他细心地为我挑开扎在手心的刺。
回到家里就被阿爹发现了,他骂我丢人现眼,不知羞耻,小小年纪就和妖物鬼混。然后提着我的后衣领,脱了鞋就往我身上打。
阿爹下了死手,当初拉车的牛将他拉偏到了荒地时,他也是这样打的。
阿娘跪坐在一边抱着不周,一边扯着阿爹的裤腿,央求不要再打了,再打就死了。
不周便哇哇哇地一直哭,很乱,很吵。
我忘了阿爹打了多久,醒来时阿娘正跪坐在我面前,端着一碗米汤小心翼翼地喂我。
她的眼眶红彤彤的,阿娘告诉我,阿姐死了。
阿姐死了,除了阿娘和我,没人会难过。
其实我也不会的。
我只是遗憾没等到阿姊送我的大片蔷薇。
阿娘还告诉我,以北也被火烧死了。除了我,没人会难过。
可其实我也不难过。
我只是会在正午抱着不周蹲坐在墙角,这里有个小土堆,下面埋的是我偷捡回来陶笛的碎片。边上的蔷薇已经枯了,连花骨朵都被风吹落在地上,叶子杂七零八地躺在地上,任由来来往往的人踩过去。
我固执地在旁边又挖了一个坑,将它们全都埋进去。
阿娘只会不停地叹着气,跟我说着什么,我却一点也听不见。
只有一句,她让我老老实实在家里干活,等来年十八了,再寻个不嫌弃我的人家嫁了。
十八吗?原来我也快要十八了。
不周已经长大了很多,她会咿咿呀呀地张着嘴,想说话,但是等了半天却又什么也蹦不出来。我还学会了写诗,扭扭捏捏的半点不成气候,写在黄土地上像狗爪子扒拉。但是不周好像能看懂,学着我的样子握着树枝在地上乱画。
很久也没人来上门跟我提亲,我走在路上,镇上的人只会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阿爹越来越焦躁,酒喝的也越来越多,常常喝多了逮到谁就打谁,不周也不能幸免。
一直到那天阿爹再次喝多了酒,扯过阿娘的头发就往墙上撞,不管阿娘怎么哭怎么喊也不肯松手。
阿娘哭得厉害,挥舞着手要去抓住阿爹的胳膊,但是没用的。阿爹力气很大,很快阿娘便头破血流,跌坐在墙角翻着白眼。血从她的额头爬下,抚平一道道褶皱,一路流到地上。
我只能紧紧抱着不周,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阿娘也死了,阿爹消停了,第二天只去镇长那里交了两袋子米当作罚款。
有人上门说要求娶我,是那个白胡子大祭司,他用两麻袋米做彩礼,要娶我回家。
阿爹喜笑颜开,应了这门亲事。
吉日定在三月三,桃花盛开的日子。
那天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外面是灰蒙蒙的一片,应该又是个阴雨绵绵的日子。
而我的床头放着一只蔷薇,小小的一朵,洁白无暇,还流动着露水,花枝上还带着刺。
不周抓着我的衣襟,小小的脑袋贴着我的胸口,睡得很甜。似乎做了什么美梦,嘴角流着哈喇子。
我盯着那只蔷薇看了好久,一把握在手里,然后迅速换上衣服抱着不周冲出家门。
身后传来狗叫声,很快就有人追出来。
我不回头,只是咬着牙拼命往前跑。
跑出镇子,一直跑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自己跑到了哪里,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清风送来陶笛的声音,有人在我的耳边轻轻说着:“含山,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