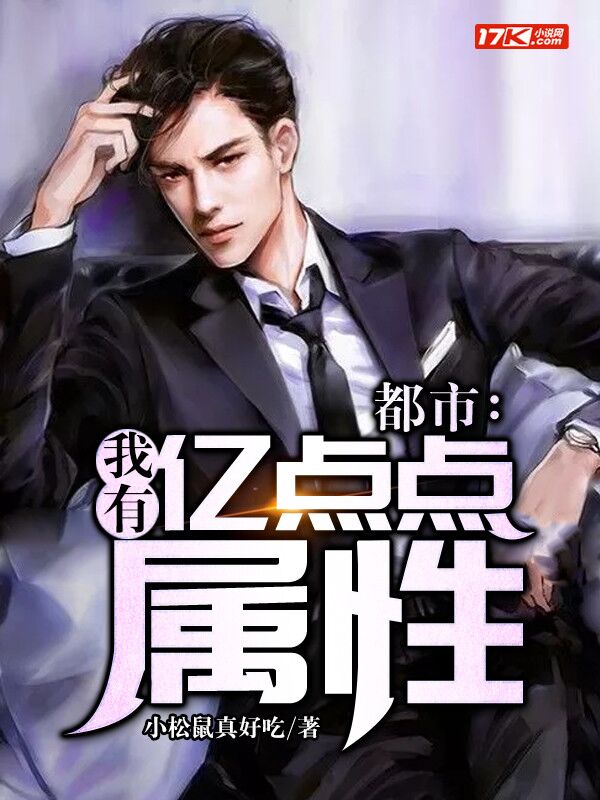“公主莫急,容本王细细道来。”吕禄正了正身子,甚至连眼都未抬一下,不屑地语气漫不经心说道。
“喔…王爷打算从何问起?”婉絮正面憋见他那不可一世的表情,她知道在对方心底从未将她这位公主放在眼里。但她仍旧礼貌性地问道。
吕禄转身看了一眼身后的曹晖,只一眼这位老太监便快速从身旁的女仆手中取得一盏热茶放到他面前的案上,随后,立刻退回原处站着候命…吕禄端起案上的茶盏,轻抿一小口,润了润咽喉,不紧不慢道:“本王所问有三,其一:吕产那日在宫中见了公主之后,与公主发生了一点点不愉快的口舌之争,之后他便得了怪病,太医诊断是中了毒所致!于是他便想起那日与公主的不快之事,公主恰巧精通医术,为了泄愤,不经意间给他下了毒也不无可能,故而他猜测出此番会不会是公主一时间的恶作剧。为了证实此事是非对错,他不得不去了相国府将您请到太后跟前对质,谁知公主仗着自己的身份,乃至相国府的庇佑公然对抗他这一小小的要求……以至于他死于非命!其二:吕产中毒致死毒药名为:箭毒木,此毒产至南越,是否是南越派了细作安插在我大汉,伺机刺杀我皇亲贵胄。 至于这其三吗……”吕禄顿了顿,回过身去,看了眼身后的曹总管。
曹晖得见主子的示意,清了下喉咙,对着堂下吏卒大声喊道:“将证物呈上!”
婉絮听闻与冬雪主仆二人相视而望,冬雪在她耳旁小声道:“莫非…是他们捏造的证物,故意陷害公主。”
“吕禄三问,此案字字句句都与南越脱不了干系,此番你我二人困于此地,怕是不那么容易脱身了。”婉絮小声回了句。
两人说话间,一名吏卒手提一木制笼子,笼中有一鸟,吏卒见过鸟笼呈于堂前,快步退下。
“公主,看来他们已经搜查过您的房间了,信鸽被搜出您不觉得蹊跷吗?”冬雪在她耳旁小声问道。
“信鸽藏得隐蔽乃内室墙壁夹缝中,只留得一小孔便于它吸气用,旁人很难察觉。除非是…有人故意惊了此鸟,鸟叫声引得外人寻得它的藏身之处!”婉絮轻声回道。
“公主还相信凌香是清白无辜的吗?”冬雪坚定她的怀疑对象,小声问道。
“堂下二人怎得如此聒噪,小王爷在此,岂敢这等傲慢无礼!”曹总管娘里娘气的叫声,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王爷,是要本公主如何作答?”婉絮将思绪拉回,对于这位仰仗人势的太监呵斥她不屑理睬,直接大声反问他的主子。
吕禄轻轻摇摆手中的折扇,听闻婉絮的责问,他慢步走下堂去,脚步在婉絮的身前停下,他微微低下头看了她一眼,这一眼正巧遇她四目相对,吕禄这才注视到她,只见得她这一双明艳的双眸,透露出一种飘飘欲仙的神气,美的好似一池清澈、柔静的湖水。他不难想象出她藏在面纱下的面容,定是倾国倾城之资。这是他第一次甚至不敢多看一眼面前的女子,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小步,深怕这迷人的眼睛看久了会勾了他的魂似的。他将手中的折扇合上,已佯装他内心的不镇定。
“小王爷,您快回堂上坐着,站这可别累坏了身子……”曹总管见状赶忙快步走到堂下,双手搀扶他的主子回去坐着。
曹总管一个眼神,身后的仆人便即刻端来茶水,他将一盏温热的水放至吕禄面前的案上。
吕禄随手端起茶盏,并未饮茶只是闻了闻茶香便将茶盏放回案上。他坐直了身子,目光正好与婉絮正视,这一回他不再闪躲,而是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气若悬河回道:“本王方才便说道,对公主有三问,一问:公主为何要对吕产下毒?二问:公主何故指使他人刺杀吕产?三问:公主将这信鸽藏于房中隐蔽处,是否用它向南越传送情报?”
婉絮听闻他的言语,心中想到:这哪是审案,分明就是坐实自己的嫌疑。她丝毫未作停顿,大声分析道:“本主便要回了王爷的三问,其一:出事前吕侯爷来相国府寻本主,本主看过他的病情并非中毒所致,实乃血虚风燥所致。其二:本主从未指使过他人刺杀吕侯爷。其三:本主房内的信鸽的确是本主所饲养,但从未使它向外传送任何信件!王爷此番言语,在没有任何证据、证人的指控之下,将这些杀头的大罪轻而易举地愈加在本主之身……这竟是太后之意还是你赵王之意?”
一旁的冬雪实在气不过,接着她的话大声道:“你们太后请我们公主来为你们的相国医病,公主不远千里而来,我们主仆谨遵与你们大汉的礼仪邦交,从未越矩。你们死了侯爷,就要拉我们公主去陪葬这又是何礼数?”
“放肆!一个贱婢!也敢在这大堂之上大声喧哗!眼里还有小王爷吗!来人!按照大汉律法:言语以下犯上,掌嘴二十!“曹总管听闻冬雪的言语,立刻站出来大声喝止,并命令下人说道。
这边曹总管话音刚落,那边走过两个吏卒一左一右将冬雪按倒在地。
曹总管朝着一旁的仆人使了个眼色,一名男仆急忙大步冲到冬雪的面前,抬起一只手欲要掌掴她的脸庞……
“住手!”婉絮见状即刻制止了那名仆人的行为。
那名仆人闻声转头看了一眼曹总管,那边给的眼神示意他暂且停下,他便退后两步,躲闪到一旁……以免双方这波情绪激动伤着自己。
“公主的下人言语对小王爷大不敬,老奴只是代王爷训诫一下!”曹总管一副恃势凌人的口气,丝毫未将他面前的这位公主放在眼里。
“你们放开我!”冬雪试着挣脱,但以她的身手绝不是她身旁这两位酷吏的对手,折腾片刻,仍旧被对方按到在地,动弹不得。她也只好作罢,为了她效忠的主子也只能甘愿受着皮肉之痛…
“婢女方才字字句句属实,不知是哪里冒犯了王爷,要受此大刑!”婉絮朝着吕禄的面前走近两步,大声逼问他。
吕禄不动深色,将手中折扇合上放至案上。惩戒一个下人这种极其小的场面,他连眼都未抬一下,随手端起案上的茶盏轻抿一小口,慢悠悠说道:“公主即不愿招认桩桩件件之罪行,又在这公然袒护不懂礼数的下人。此等不合乎我大汉之律法制度,让本王很难顾全公主的颜面。”
婉絮转过身来,蹲倒在冬雪的跟前,伸手想要将她扶起。哪知那两名吏卒死死将她按倒在地,以她之力根本无力与之对抗。
“王爷此番作为倒是跟先前的吕侯爷如出一辙,遇事从不问明缘由,直接给人安些个莫须有的罪名,逼迫她人认罪!此举又是你们大汉的哪条律法规定!”婉絮据理力争说道。
“王爷,此二人气焰嚣张,完全不将您放在眼里,今日若不惩戒她二人,您日后在朝中威信何存!”曹总管在吕禄耳旁煽风点火小声说道。
“把这婢女拖出去杖责二十!”吕禄果然听进了这位老太监的言语。
堂下的吏卒得令急忙都围了上来,那两名吏卒驾着冬雪强行将她带往堂外的方向…
“住手!本公主的人若是冒犯了王爷自由本公主亲自管教,还请王爷顾及两国多年邦交之情宜,网开一面,放了婢女。“婉絮一个快步挡在了冬雪三人面前。
“王爷…老奴看来这位公主是公然对抗王法,就该连她一起惩戒!以彰显您不可触犯的威严!”曹总管继续在吕禄耳旁火上浇油,表情像极了毒妇嘴脸。
“毕竟是一国公主,没有认罪之前罚了怕是不好与姑母交代。”吕禄小声回道。
“没有人能扛得住廷尉的酷刑,动了刑自然也就招认了。到时候,太后跟前交差只道她们主仆是此案件幕后操纵之人…在她房中搜出的信鸽再定她个南越细作。至于…这过程吗……自是不会过问。”曹总管一脸奸笑道,这就是他这些年受宠于吕禄的地方。成就之路是通过杀戮得来的,所以他绝不会放过每一次能够令他得到太后赏赐高升的机遇。即便是枉死再多的人,他亦无动于衷。
“此等壮汉对一弱小女子杖责二十,岂不是要把人给打残了不成!”这是婉絮入汉以来第一回怒声说道。
她的声音打断了吕禄主仆的对话,吕禄与曹总管对视一眼,对他轻轻点了下头,以示同意了他的说法。他心中所想;这种费时费力的查案,不如直接找个替罪羊订了这罪,太后跟前又有了立功的表现,恩赏自不会少。再者说,吕产本就是他在吕氏一族强有力的竞争者,现有人在他之前除了这个绊脚石,他心中大快,日后,太后便将独宠他一人,无限的权利都将属于他。此刻,被权力欲望蒙蔽了心智的他哪还管真凶是谁,想到此,他的嘴角不禁露出一丝浅浅的邪笑。随后大声命令吏卒道:“南越公主涉嫌谋杀当朝侯爷,又在房中私藏信鸽与南越传送情报,此乃杀头之罪,但因此二人拒不认罪,故先将此二人带下每人杖责二十,拖回狱中,择日再审。”
“退堂……”曹总管大声喊道,并眼神示意吏卒将二人带下去。
“你们尽敢对公主动刑!我们要进宫面见太后!”冬雪听闻公主也要受罚,气急败坏道。
“带下去!”曹总管根本就不理会她的话语,接着在吕禄跟前奉承道:“还要面见太后,殊不知太后她老人家跟王爷您是一家人。在大汉,无人敢公然反驳吕氏族人的权威!否则,她将是自寻死路!”
“小小南越国不过是我大汉足下一只蝼蚁罢了,本王何惧之有!”吕禄听了他此番恭维的话,更是开眉展眼,长久以来吕后给予他的权利令他不得不狂悖无道!他吕氏族人之狂傲自然也就不会将小小南越国介于心中,惩戒甚至污蔑他们的公主也就无任何后顾之忧。
婉絮深知此刻任何的争论都无济于事,这位赵王是铁了心的要整死她们。她也只能暂且忍下这皮肉之痛,她在心中许下誓言:只要不死她必将寻得机会绊倒吕氏一族!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吏卒手下的棍棒一下一下打在主仆二人的身体之上,婉絮未吭一声,忍着剧痛,狠狠地攥紧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