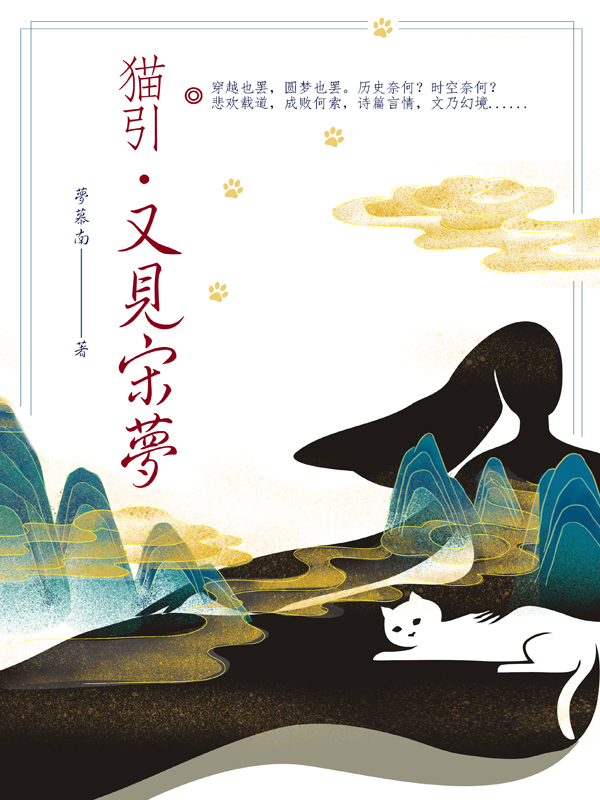明黄色的长袍上绣着沧海龙腾的图案,新做的衣裳分外合身,祁宴抬手整理袖口。
何舒明站在一边,望着镜子中的人。
男人沉着的姿态,冥冥中让他也安定了下来。不就是成王败寇,有什么好慌的。
赌了那么多回,再赌一次就是了,他暗暗握手为自己鼓气。
镜子中的人抬眸,勾唇似乎在嘲笑他如负鼠的模样。
何舒明挠了挠鼻子,避开他的视线。
黑眸深沉吞噬,不是棱角分明的面容带给他的难以亲近,是那对眸子,见过血的眸子。
孑然独立间散发着傲然的绝对强势。
从前只要小将军带他们出去,就有本事能带他们都回来,大家全是这么相信的。
“陛下,”这一段就不能用步辇了,跟在祁宴身后何舒明小声提醒,“掷杯为号。”
往上走,随着祁宴的脚步一节节台阶上的人跪下,高喊的万岁震耳。
在巨大的空地上荡出回声,敲击鼓面的声音更是令人烦躁的吵闹。
衣袍翻涌,男人冷漠的容颜在华衣下更显得矜贵,倨傲。
祁宴抬眼,望着顶上祭祀所用的器具,突兀想起了她。
走了吧,应该。
送去什么地方了?十五会保证她的安全,等他回来会告诉他人去哪了吗?
不知道就不会抱有期许,所以他没允许自己问。
如今他连自己的项上人头都在刀尖上,不如早早将她送走。
继续向上,百节台阶走了不到一半,他开始有些烦躁了。
不信这种神叨之事,又不得不费事应付。
耳边突然响起父亲的声音,那日站在草原的山顶上,傻乐的拍手,“多好的江山,多美啊小宴。多荣幸你我能保卫它。”
父亲的志向只在马背上,长剑戎装,马蹄声和那铿锵的鼓点,还有母亲亲手做的奶糕。
男儿许国,实属幸事。
突然好像不怨父亲当年的不争了,因为坐这个位置的确烦。
手中的手刀被他玩弄的发烫,祁宴慢悠的勾唇。
可不重要了,他对这个大好江山不热衷,也对黎明百姓的安危不感兴趣,更对后世的指点不介意。
唯望这天下人与他一般痛苦。
剩余几节台阶,祁宴回过神,坐到上面,孤身俯视着下头
“平身。”
“谢陛下。”
大陈崇尚萨满,几乎到将祭司当成神的地步,住在高台上,作为神的使者,传递命令。
何舒明没有办法控制祭司,这是唯一不定的棋子,
祁宴不动声色的看着留着长胡子的男人绕着鼎转圈,唱着旧时传统的祈福歌谣。
一声高吼后,祭司点燃了火把,高举过头顶,一左一右的落脚,跳着顺时针围绕着鼎。
祁宴静静的看着,等到他绕到身前。
火把一瞬熄灭,唯余一缕黑烟迎风飘远。
乐声鼓声刹那间消失,场地静寂。
祭司虽然一副慌慌张张想要告罪,又重新点起火把的样子,可眼里却没有半分。
祁宴勾唇,抚手像是在看一场廉价的闹剧。
一旁站着的何舒明双手在袖口中紧握,戒备的像是即将离弦的箭。
不出祁宴所料,第二次点燃的火把,在刚刚即将绕到他面前的时候又开始摇曳,正正好面对他的时候才猛的熄灭。
焦炭的味道飘散在空气中。
“这,...........这这是何意啊?”
“以往可从未有过这种。”
“是啊,这可如何是好。”
祭司像是彻底慌了,扑通一下跪下,拼命的磕头,“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
他还一句话未说,男人就祈求饶命,祁宴眼底的笑意更浓了。
不知道空地上跪着的人中,是谁高喊了声,“天意啊!这是上天的指示!”
回声还未结束,手刀划破空气,来人只觉脖子上一痛,目眦尽裂。一句话说不出的倒在地上,抽搐几下就不再动弹。
周围人慌慌张张的惊叫,退散,一时间乱作一团。
何舒明猛的转头,望向上头的人。
他淡漠的神色未改,但黑眸中像是燃烧着一团火焰似的,烧灼吞噬。
跪的近的都能感觉到手刀是何处射出,不该啊,陛下一贯沉着,审时度势,怎会?
他蓦然觉得陛下今日的本意就不是奔着和睦的将春祭度过。
有种屠杀当年参加那件事的所有人的时候,暴戾疯狂,令人胆寒的兴奋。
双手合十如同慈悲的佛子,下一刻手起刀落,鲜血四溅。
“陛,陛下..........”
祁宴摊手,扬了下眉,似乎无辜。
“恶畜,恶畜啊,天要亡我,派下你这等鬼魅。”
跪着的人中跌跌撞撞站起一个男人,颤抖的向前走,“那好,你有本事便收了老夫这条性命!”
擦,火苗瞬时起,包裹住男人的身体,吞噬着燃上他恐惧的面容。
在撕裂的惨叫和悲鸣中,化成一具焦尸。
祁宴明了今日有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了,他是恶鬼,前来毁灭的,有人不惜代价的要将这个名号扣在他脑袋上。
何舒明咬牙,袖口中的手不断收紧,迅速的想着解决的法子,断不能再将此事夸大了。
祭司一回头刚准备让好戏连台,对上男人的逼视,手中的粉末差一点洒在地上。
“该你了?”
祁宴啧声,“站远点死。”
“陛下!”何舒明赶紧压低声音开口,“陛下他要是死了,咱们可就真的说不清了,您到底在想什么啊?”
见他二人起分歧,祭司发狠的打算抽刀拼一把。
祁宴毫不费力的挡下了,知晓他的心思,从这个角度看下去只能是他恼羞成怒杀了神的使者。
还没等他做出抉择,四下猛的传出马蹄和盔甲碰撞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出,整齐划一。
“刀下留人!”
骑在马上的男人飞速的奔进来,青衣的翩然少年郎疾驰穿过空地,在台阶前勒马。
“是六殿下!”
“殿下!”
“是殿下啊,殿下吉人天相啊!”
陈远泽听着这些声音,忍不住脸上得意的笑容,拱手向地上人示意,“诸位,今日我来便是诛逆贼,夺回我大陈疆土。贼子何敢猖狂,孤才是正统。”
在一边人眼神的恳求下,祁宴收了手,嫌恶的捻过指尖,“就你一人?朕的好兄长没来?”
他完全没有吃惊的样子,陈远泽吞咽了下,压下心底的恐惧。
高声喊道,“逆贼,快快束手就擒,孤留你个全尸。”
刚刚还在叫嚣的,大半都是前朝老臣,闻言更是喜极而泣,跪下的扑通声此起彼伏,“我等誓死追随殿下!”
“若不是有人作保,你早死在朕的剑下了。”
祁宴双手交叠,闲散的像是在叙旧。
不急不慢的神情点燃了陈远泽,他轻蔑的好好两声抬手,“暗卫何在?!”
铁甲声再一次回响,何舒明皱了眉。
刚刚包围此处的人不多,算着还有胜算,没想到陈远泽还有后手。
加上大陈金吾卫的人手,在场他们的人远少。
他焦急的望向祁宴,祁宴也侧了下头,与何舒明不同的是平静,从开始到现在异常诡异的平静。
何舒明心里不定,拼命使眼色示意是否先下手为强。
祁宴抬手,他还在等另一帮早就进了京城的人。
既然来了,又这么热闹,他怎么可能不出现。
陈远泽不足为惧,他等待的是另外两人。
见他无话,四面八方又都是他的人,陈远泽狂傲起来,挺起腰杆清了清嗓子。
“孤今日便替天行道,为父报仇,以汝之鲜血,告慰父皇在天之灵!”
他高高举起右手,半刻却无响动。
远处却传来惊诧的呼喊声和盔甲撞击,互相推搡的声音,“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