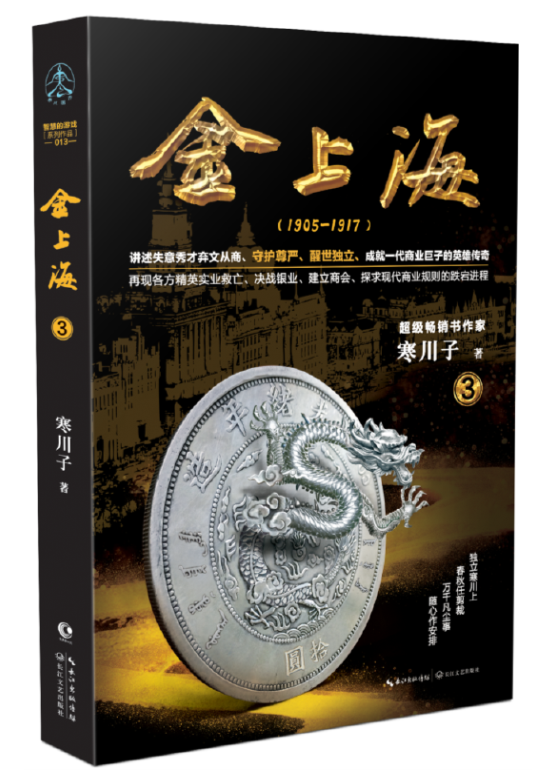徐香媚在煎熬中捱到了晚上,还不见苏菲和徐迁回来,怕是真出事了。她正犹豫是否该去向王妃禀报,正赶上到吃饭的时候王妃不见苏菲,差人来找,她只好硬着头皮来见王妃。
王妃见只有香媚一人来了,她生气地说,“怎么就只你来了?苏菲这丫头也太不像话了,他父王病卧在榻,竟一整天不着边。她到底在干什么?”
徐香媚战战兢兢的回答,“公主她,她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为了让王爷喝上狼肉汤,独自出去捕狼了。”
王妃一听大惊失色,“作死的奴人,你怎么不早禀告?公主若有闪失拿你是问。”她顾不上责罚香媚,“来人,快去把公主给找回来。”
护卫长招集了护卫军,备好了鞍马,正愁夜黑地广不知向何处去寻?忽听到远处有马匹嘶鸣,听声音朝汉忠马圈方向跑去。
徐香媚估计是哥哥骑马跑回来了,和众护卫举火把赶过去,只见一匹马在栅栏外游荡,却不见一人。
护卫长看到马屁股上有几道抓痕正在滴血,他边查看边说,“看这匹马的伤,像是遇到狼群了。那骑马的人必是凶多吉少,定是让狼给叼走了。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公主她或许……”
徐香媚上前抓住马头死劲的摇晃,哭喊着,“哥哥呢?你把哥哥给丢哪了?”
这匹马似乎听懂了什么,原地打了个转后,拖着徐香媚向外走去。她明白了马的意思,跃身上马,没等她骑稳当,马就飞奔而去。众护卫紧随其后,催马追去。
徐香媚经过这几年跟随苏菲骑马锻炼,她如今已是马背上的高手了,她还能在飞奔的马背上左右换位。再加上这匹马是上等良马,让她把众护卫甩在后面老远只看到火把光。她只好放慢马步,等众护卫跟上,她心急,一催马又把他们丢在大后边。就这样一路上几次等护卫赶来,把她急的直骂他们骑的马是只吃草不长劲的大草包。
徐迁和苏菲经过一番翻云倒海后,他累的浑身酥软,舒腰躺下。这是由惊狼鞭拆解的细皮绳攀连韧性好的枝条,在树杈上做的呆床。由于呆床地方有限,她挪动地方让他先躺下。然后,这回又换她趴在他上面。渐渐的都睡着了。
徐迁朦胧中听到马蹄声,她摇醒了苏菲。
徐香媚被马带到树下,先看到了树上一个人,“是哥哥吗,你没事吧!”
徐迁听到是香媚,想不到在自己最危险的时候,竟是弱不禁风的妹妹来相救,“香媚,别为哥哥担心,哥哥没事的。”
“就知道心疼哥哥了,还有我呢!”苏菲探过头,怨香媚没问侯她。
众护卫举火把已赶到树下,仰头向上看,只见苏菲公主正被徐迁从上面扶下来。看她头发散乱,衣衫不整的,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他们回王厅时,老远就见灯火通明的围一堆人,王府的人都没睡,王妃领众人一直就在外焦急的等待着。
王妃见女儿还是囫囵人一个,他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放下了。苏菲跳下马上前抱住王妃就哭,哭的那叫痛呀!只有经历过阴阳间隔的人才能体会到。
“母后,这次多亏徐迁相救,你才能再见到女儿。”苏菲想到已是他的人了,该找机会提高他的身份了。
王妃扭头四处寻找是哪一个,“哪个是徐迁?”
徐迁早以下马和妹妹在一起私语,听到王妃喊他,上前几步在王妃面前亮个相。虽说是牧奴一个,却有不凡的气度,一时看的王妃心里欢喜,“徐迁?是香媚的哥哥吧!也就是那个当年苏菲捡回来的那个,这正是天意,苏菲或许长有天眼,知道收留你兄妹必有大用。你救了公主,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本王妃定会满足你。”
徐迁歉让道,“救公主是我的本分,怎敢邀请赏赐!”
王妃更是喜欢她不居功自傲,要不是他牧奴的身份,把女儿赐给他都行。但精明的王妃还是觉得赏他只烤羊化算,外加十坛马奶酒。西托派几个侍者抬烤羊、抱酒坛,把徐迁送回了马圈帐篷。
几个侍者领了徐迁赠送的一坛酒,道谢后出了帐篷,边走还边议论,“听公主说,那匹马把狼的脑浆都踢出来了。”“护卫都说那匹马跑的真快,怎么都追不上,老汉中一辈子总算养了一匹好马。”“听说他和公主都那个了。”“快别乱说了,小心脑……”
铁锤随徐迁出来相送侍者,听到了几个侍者的议论,他傻乎乎的问,“师弟,你和公主都那个啥了?”
徐迁臊的满脸通红,幸好有夜色遮挡,才没让他想一头撞死。就算白天他也不可能一头撞死,在草原上要找点有硬度的高物还真难,没墙没树的。
“快回去吃烤肉堵你的嘴吧!”徐迁怕铁锤进帐里了还说,会给师父火上浇油。
汉忠一脸严肃的坐在睡铺上,侍者进来的时候,七嘴八舌的夸他养的马好,他是又吃惊又生气。徐迁进到帐里,看师父脸色不好。他赶忙给师父倒了一碗酒,搬过来战战兢兢恭恭敬敬的给师父递上。
汉忠一巴掌打翻了酒碗,“太让我失望了,想不到你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老天爷呀,你睁眼看看吧!我怎么净收些蠢徒弟!”
徐迁忙去给师父擦拭溅在身上的奶酒,“师父,都怪徒儿不该不听你的话。”
汉忠盛怒难消,“谁让你去动用那些良马了?这下可闯下大祸了。你赶快去把那匹马掩藏好,看能不能糊弄过去!”他又把大黑和铁锤都喊近说话,“你两个听好了,到时候一定要保护师弟带出几匹良种马。徐迁你去准备吧!抓紧机会逃出去,以免夜长梦多。”
“师父我和铁锤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师弟带出良种马的,可等徒儿们逃了,你怎么办?”“师父,我铁锤背也要把你背回大汉。”大黑和铁锤围着师父不停地劝师父一起走。徐迁也说,“我不能让师父到百年后还埋葬在匈奴,五十多年了,你无时无刻不想回到大汉。”
“你怎么也说这等蠢话,全靠你养马兴大汉了,师父是回不去了。唉!再也见不到故土了。你们走时把我的白发带回大汉,我已记不得家乡在哪了?只记得家住黄河边,爷爷常带我和哥哥到黄河滩挖胶泥土制埙。这种胶泥做的埙,掌握不好火候就会烧裂,是我家传的独门手艺,叫做黄河泥埙。我记得好像还有个叔叔,有两个兄长,估计他们也已都不在了。若日后凭埙音能找到他们的后人,就把我的白发埋进祖坟里,若实在难找到就把它埋在黄河岸边。”汉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有些体力不支。他老弱体衰,这些天已不能下地走路了。
汉忠让人把他用皮袋装着的埙拿出来,并让割了他一缕白发,一并交给了大黑,交代凭埙找人。徒弟们细瞧这埙底刻着“黄河泥埙”四个字。汉忠太爱惜这埙了,从不许徒弟们碰它,怕不小心摔碎了。这可是当年爷爷送给他的,他被匈奴人抓走时,也是拼了命护着的。这埙就是他的家,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吹一会儿。
徐迁和师兄们常听师父吹埙怀乡,它发出的音,深沉凄凉婉转悠长,宛如一老者站在历史的长河里,述说不尽的兴衰沉浮。
汉忠把埙交给大黑后,便倒头躺下,任凭徒弟们怎么劝说,他也不愿坐起吃东西。
到了早上,由于昨天睡得晚他们起的也晚,师兄弟三人铲完马粪回来后,又开始煮马奶,师父已不能煮马奶了。正吃饭时,苏菲带徐香媚跑过来,叫上徐迁到马圈里找昨晚那匹马。
苏菲边找边说,“咦!到底在哪呢?哥哥快帮我找出来,我昨晚说了父王还不相信,我要牵过去让父王见识见识。让他看看你们师徒也能养出宝马来。”
徐迁找来一匹与昨晚那匹毛色相像的马,“总算是找到了,别把它夸的神乎其神的,也就一般般。”
苏菲看了大笑道,“你呀!怎么连公母都不分了?明明昨晚那匹马是公马。噢!对了,我是看到他屁股上被抓伤了,才注意看它后面,所以知道是匹公马。对,找屁股上有伤的棕色大吗。”有过昨天和他肌肤之交,她在他面前可以不再脸红心跳地说这类话。
这匹马必竟是马群里最出色的马,身高体壮的鹤立鸡群。苏菲没废多大劲就在马群里找到了这匹马,她让徐迁拿来辔头马鞍备好牵出来。她骑上马遛两圈,不管怎么吆喝驱赶,这匹马就是不肯快跑。
“奇怪了,这匹马昨晚上的精神劲头都到哪了?是找错了?不对呀!分明就是它呀!”苏菲狐疑的嘟哝着。
“可能是受了伤的缘故吧!这匹马估计是废了。”徐迁忙解释。
“只是被狼抓破了点皮,这点小伤也不至于吧!”除非弄不明白。
“或许是昨晚他受到了惊吓,要是吓破了胆,就缓不过来了。”徐迁急了,真怕露出马脚来。
这时大黑从帐篷里探出头喊道,“师父让你先过来一下。”
徐迁正被苏菲逼问的不知该怎么应服,借此赶紧走进帐篷里。
“看你昨晚勇武的样子,却也这么胆小。我都缓过了神,噢!我有哥哥陪着才不害怕的。而你却看到同伴的肠子都被狼给掏出来了。是不是给吓坏了,瞧这眼神多无力?”苏菲和马自言自语的说着,爱惜的抚摸着马头,摸到眼睛时揉动了妈的眼皮,从里面掉出来一片鱼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