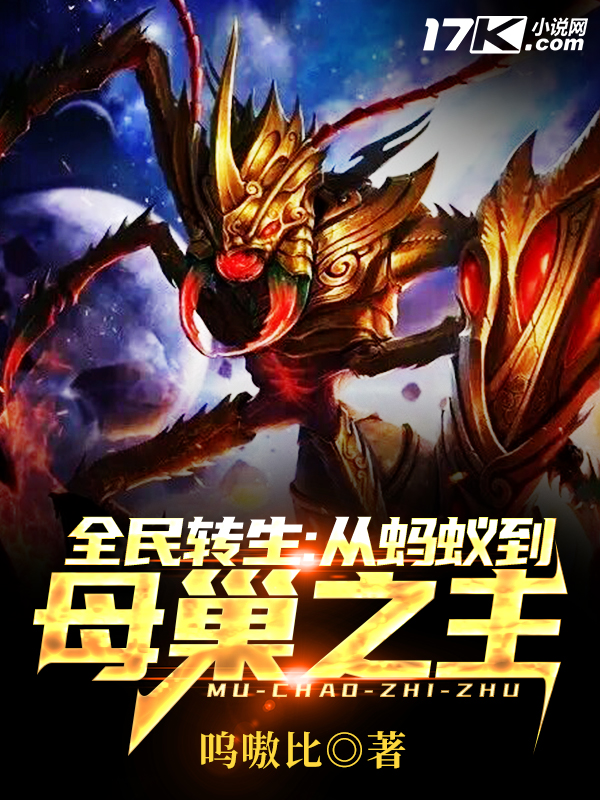那时,我对死亡的看法就是再也见不到了,却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份死亡到底给活下来的人带来了多么致命的打击。
父亲的葬礼办完后,爷爷奶奶吵得更凶了,有一次闹得很严重,奶奶翻出农药就要喝,我当时吓得要命,急忙上前拉住了奶奶,爷爷看在眼里,骂骂咧咧摔东西出了门。
每每想起,我都会感到后怕,如果我当时没拦住她,这个家庭将会变得越发不堪脆弱。
“合张照吧?”
这是程序的末端,令我心下不安。如果只是被资助方收藏起来倒也没什么,可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乎那些孩子的自尊心。
只有将这些照片暴露在公众视野,才能以此为证据,从而为自己的企业起到宣传的作用。商人自是讲究利益,他们这么做无可厚非。我既然选择接受这笔钱,就必须懂得丢弃尊严,成为外人眼中贫穷的代表。
可要论起心甘吗?不甘。
不甘于自己生来就要被折断傲骨,面上再怎么装成风轻云淡,心里都是被外界的言论戳成的窟窿渣子。所以很多时候自我封闭不是真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是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措施,封闭久了,就真的逼迫自己丢去兴趣了。
“来,靠近一点。”
那人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故作亲昵,收起眼底的生疏,我配合得靠过去,露出自然的笑。
我们熟吗?其实只见过那么一两次,谈不上熟,但我对他确实心存感激。
至少他愿意给予我温暖,即便这份温暖可能带有目的。
周日的下午我就要收拾好,准备回普阳了。
我一般会提前站在村口等上那么二三十分钟,毕竟公交车的时间真的不准,错过了最后一班车,可就得麻烦别人送我去五六里路外,等干路上的其他公交车了。
马路的那头地势较高,种了大片的树,成了葱绿的山,风一吹,它们会互相擦碰发出沙沙的声响。路的两端也种了常青大树,树上的纹路斑驳纵横,偶尔还能看到蝉褪的壳。村的上风向还种了不少的桃树和梨树,春天那会儿,粉嫩的花蕊同洁白的梨花交织在一块,开得好不热烈。
我和玩伴们经常会去折下几枝带回家,插在自己的床头。
估摸十岁大那会,苏沁沁还把花瓣掺进护肤品中,加入些许花露水制成了新品,然后和大伙们一起分享。那时大家就站在树下,花瓣随风飘落,小姑娘们笑颜如画。
路的这边则是大片的田埂,耀眼的光芒照在忙碌的农民身上,他们弯着腰,身上衣服简单陈旧,汗水沿着布满皱纹的脸上滴落,凉风吹过,带去了丝丝燥热。
我一眼就看到了田里的爷爷奶奶,他们也在陪我等车。
“查外来来嘞。”(车快要来了)
我听到奶奶朝我喊了句,专属于公交车的嗡咙声也随之而来。
我提起地上的大袋子,回了句:“沃早嘚。”(我走了)
公交车在我跟前停下,车门一开,我一手提着菜,另一手拎着包,有些艰难地从兜里掏出钱币,塞进了箱子里。
引擎声响起,我找了个空位赶紧坐了下去,长长呼了口气。
因为是在大伯在借住,所以奶奶总要给我准备一大袋子的菜,让我带给大伯家,也算还人情。
当然,这在他老人家眼里是顺便,却不知道我要拎着沉甸甸的菜走好几里的路。
我所坐的公交属于连接镇乡和市的,到了城南站就会停。市里也有公交,可不通我大伯家,我得靠脚走,所以没到这个时候我就会生起自己的气来。
你没事带这么书干嘛?你又不看!
我心里边烦,就拿露在袋子外面的葱发泄,狠狠地对折强塞进袋子里,不准它露出半分。
露出来像什么话,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是带菜进村卖的乡巴佬呢。
一路的绿意盎然都不足以抵消我这一时起的烦躁,结果一到站,我把大红袋子抱在胸前,挡了一半的视线,一不小心绊到了什么,差点摔个狗啃。
袋子鼓鼓胖胖,我身板又小,手酸得厉害,没走几步就要停下来颠一下。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害怕碰到熟人,尤其是付鸣楠。
城南站位于城区的外沿,国道绕过,发出沉闷巨响的大货车川流不息,带起一地的灰尘,灌入旁人的心肺。
我的内心是畏惧的,尽管布置了红绿灯,巨物的威胁感还是充斥着整个视网膜,时时刻刻担心货车刹车不稳冲了过来,过起这里的马路来无不战战兢兢。
好不容易等来了绿灯,突然一辆电动车驶来,停在了我的身后。
“宋知浮!”
我的瞳孔缩了又缩,转过身来,对上了痞笑的江延帧。
“江延帧?”
“哟,江哥,这哪位啊?”后座坐了一个同江延帧年龄相仿的男生,视线落在了我的脸上,颇带喜感。
江延帧坦言:“妹妹。”
“我靠,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这么漂亮的妹妹?”那男生挑眉,继续道:“亲的?”
我被这么直白的夸奖弄得有些不好意思,淡淡笑着,抵在胸前的大红袋子显得越发尴尬。
“不是,亲戚家的。”
男生闻言,露出了然的表情:“我说嘛,哎,小妹妹,能认识一下不?”
目光又扫到了我的身上,那人还拿出了手机,等我报qq号。
我一时有些紧张,更有些难为情,拒绝的话还在酝酿,那人又悻悻地收回了手机。
“啧啧,大不了不加嘛,瞧把你紧张的。”那人戏谑发笑。
我顺着他的话看向江延帧,只见江延帧神情冷峻,狭长的眸子睥睨着他身后的人。
“这人老不正经,以后看到了绕着走知道吗?”
后头的男生一听就急了,控诉道:“江延帧,有你这么诋毁兄弟的吗!”
我脚趾紧抠着鞋底,生怕重心不稳大红袋子给摔地上,抖出一大袋子菜,包心菜在地上滚动,滚到江延帧的车边。
幻想仅是幻想,并没有发生,可我想走的心很迫切。
江延帧好似看出了我的想法,不再同身后人瞎掰,道:“到这等我,我送他去车站就回来接你。”
我闻言憨憨地直点头。
“拜拜咯小妹妹!”那人回头冲我眨眼。
很快我就听到江延帧渐远的声音。
“闭嘴吧,少他妈打她的注意!”
之后就是被风吹散的吵闹声,我听不大清,也没什么兴趣,等抬脚要走时,才反应过来江延帧的话。
接我?
他们大人都喜欢故作熟络吗?还是在大伯那里听到了关于我的事,也开始同情我了?
一想到这,我心里瞬间对江延帧砌起了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