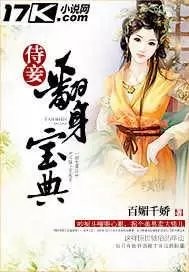涨潮了,海浪一浪高过一浪,码头的水位在不断地上涨,岸边那些停摆的船只,在海水的浸泡下,如鱼得水一样,开始摇头摆尾起来。
孙老六戴着一副墨镜,倚在一辆“帕萨特”轿车的车门上,向海面观望,眼中透着几分自豪,又有几分感慨。
他近来脸上那令人生厌笑容已远没有从前那么多了,无论是谁和段二胖子作对,都不会有好心情的。段二胖子是一只恶虎,谁要是摸了它的屁股,就得随时提防它有反扑的可能,所以,孙老六不得不时刻绷紧自己的每一根神经。
其实,孙老六的势力不及段二胖子,如果两个人真要硬拼的话,孙老六万万拼不过段二胖子,孙老六当初只是凭借着一股贪念,一股雄心,和段二胖子过起招来,可双方僵持以后,孙老六才发现这件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但事已至此,他已是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扛下去。
保镖方保信、杜锋就在轿车的另一面站着,这二人就像是孙老六的两只尾巴,孙老六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很少有分开的时候。
孙老六转了个身,在轿车的机盖上坐了下来,他冲着方保信问:“最近船只出海捕捞的情况怎么样?”
方保信从车头绕到孙老六的跟前:“这几天出海的船只收获还可以,捞上来不少螃蟹。”
孙老六“哦?”了一声问:“个头怎么样?”。
方保信接着说:“个头倒不是太大,现在海里这么空,能捞上来东西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孙老六摘下墨镜,揉了揉眼睛:“你叫人这几天给我收购个二三千斤,我要往外地发。”戴上墨镜又补充了一句:“我要个头大的,肥的,价格还要低。”
方保信面有难色地说:“咱们以前的收购价格已经很低了,就这样还有几家船主对我们心存不满,如果再压低收购价格……”
方保信的话还没说完,孙老六就打断了他的话:“怎么?到现在还有人敢和我孙老六支棱脑袋的?”
方保信回答说:“他们明面倒不敢说什么,暗地里恨不得能吃了我们。”
孙老六墨镜后面的眼角肌肉抽动了一下:“不压低收购价格,我们怎么能赚大钱,如果连几个船主也摆不平,我们今后还怎么在港上混,你们跟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难道这种事还要我再教你?”
方保信唯唯称是:“六哥!我明白。”
这时保镖杜锋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提醒孙老六说:“六哥!我们和‘蛇头’魏刚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该走了。”
孙老六点了点头,挥了一下手,三人便一同钻进了车内,由杜锋驾驶着轿车,向赢州城内的天菱商厦缓缓驶去。
天菱商厦的一楼是孙老六租来准备开歌舞厅用的,现在内部装修已经完工,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却迟迟没有营业。
大厅内封闭很严,也很黑。孙老六和方保信、杜锋三个人的皮鞋踩在水磨石的地面上,发出“哒!哒!哒!”响亮的回声,就如同走在山洞里面一样。
三个人在一个角落坐了下来。方保信摸索着打开了几盏壁灯,灯光很暗,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微不足道。
方保信望着装修豪华,设施齐全的大厅,心有不甘地对孙老六说:“六哥!咱们还等什么?难道我们真的怕了他段二胖子不成?”
孙老六在吸着烟,沉吟了片刻方说:“现在我们和段二胖子正是针尖对麦芒的时候,难保他不对我们实施报复,这个迪厅可是花费了我们上千万的资金呀!如果在这个时候开业,段二胖子很可能会把这里作为袭击我们的对象。”
方保信抬起二郎腿,不屑地说:“那也不见得,我们在他的金夜迪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他们到现在不是也没有什么动静吗!我看他段二胖子是老了,做事情也开始思前想后,畏首畏尾了。”
孙老六表情凝重地说:“还是防着点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段二胖子绝不是个省油的灯,如果他们真的在我们开业期间进行报复,不但会给我们的经济造成损失,也会给我们的声誉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个迪厅,是咱们进军娱乐业的第一枪,如果这第一枪打不好,今后还怎么开疆拓土。”
方保信听了孙老六的话,很受启示:“六哥说的也很有道理。”
正说着,只听得“吱——”的一声,大厅的门被缓缓推开了,一道刺眼的光亮从门口直射进来,同时也把一条细长的人影印在了大厅的地板上。
因为逆着光,所以孙老六等三人根本看不清来人的面目。
“魏刚?”保镖杜锋有些拿捏不准地问。
“哈!哈!哈!怎么,几天不见你们就不认识我魏刚啦?”那个人影笑了起来,并随手带上了门,向孙老六这边大踏步走了过来。
孙老六等三人没有动,而是默默地注视着来人由远而近。
渐渐的,来人的身形在壁灯光线的照射下,轮廓变得清晰起来。只见这人四十出头,身材瘦削高大,典型的一张大马脸,卧蚕眉,细长眼,笑起来的时候,满脸都是皱纹,就象是一件衣服被放在了屁股底下压褶了一样。
看清了来人的相貌,孙老六笑骂了一句:“魏刚!你他妈的怎么越来越瘦,越来越老了,是不是干那事儿干多了?”
那魏刚一裂大嘴:“怎么,你眼红了?要不我今天晚上给你送两个过来?”
孙老六皱着鼻子说:“算了,就你弄的那些货色,给我提鞋我都不要。”
魏刚在孙老六的身边很随便地坐了下来,指着孙老六笑说:“老六!我看你纯属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呀!”
孙老六冷笑:“我吃不到葡萄?我随便捡一个都比你弄的那些强。我就纳闷了,韩国那么多美女,为什么偏偏要你那几个破玩意!”
魏刚瞪眼反驳:“谁说是破玩意?人靠衣服马靠鞍嘛!你别看她们大多数都是从穷乡僻壤的山沟里整过来的,只要到了那边好好拾掇一番,个个都如花似玉。”他一挑大拇指:“再说,我这几个可都是原封的,你想不想尝尝?”
孙老六摆摆手:“算了,有颜色没味道,还是留给你卖大价钱吧!”他咳嗽了一声:“你这次又整了几个?”
魏刚伸出五指翻了三下。
孙老六脱口道:“十五个?”
魏刚淫笑不语。
孙老六提醒说:“这么多人你可得自己捋顺了,别象上次那样,还没到国境线,就自杀了一个,如果让别人发现了尸体,麻烦可就大了。”
魏刚一拍胸脯,打包票地说:“你放心,这些山沟里的姑娘单纯的很,听说偷渡到韩国后能赚大钱,个个高兴的不得了呢!”
孙老六骂道:“你他妈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精了。这回我给你一下子引渡这么多人,你可得多给我点费用。”
魏刚哎了一声:“差不了你的,咱们还是按人头算。”他搔了搔头又说:“老六,我有一个事,你能不能帮忙给办一下。”
孙老六盯着魏刚:“什么事?”
魏刚的大马脸上随即升上了一股怒色:“他妈的!最近咱们赢州市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三个愣头青,专门骗吃骗喝,白坐车,还号称什么赢州三龙。你也许不知道,我有一个老实的弟弟,是开出租车的,前几天,碰上了这三个愣头青,他们坐了我弟弟的车不给钱,我弟弟就和他们理论,却被这三个愣头青暴打一顿,所以我想请你出面帮我教训教训这三个死小子。”
孙老六“噢!”了一声:“这三个人我也听说过,是三个刚出道不久,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地癞,既然得罪了你的弟弟,我就给你出这个面,你说吧!想怎么修理?”
魏刚握紧拳头,捶了一下大腿,狠狠地说:“最好给我废了这三个愣头青。”
孙老六拍了拍魏刚的手背,慢条斯理地说:“没问题,这件事就交给我了,包你满意。”
魏刚一拱手:“那就多谢了!”
孙老六若无其事地说:“小事情,对付他们三个人,就象对付三只野狗一样,只要不出人命,什么事也没有。”
魏刚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纸包递给孙老六:“老规矩,这是这次引渡的定金。”
孙老六笑嘻嘻地接过纸包,也没仔细看就交给了方保信。
“说吧!什么时候发船?”孙老六问魏刚。
魏刚又搔了搔头:“过几天吧,我准备再凑几个一起走。”
“那好吧!”孙老六跟魏刚握了一下手:“人齐了你随时通知我。”
魏刚走后,孙老六等人也关了灯锁上门,下台阶的时候,杜锋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接听电话时杜锋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凝重。最后他说了声:“知道了,我马上回去。”便挂断了电话。
孙老六看出杜锋的神色不对,关注地问:“怎么?出什么事了。”
杜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儿子高烧拉肚子,好象是食物中毒,你弟妹让我回去送她们去趟医院。”
孙老六刚才眼中的那种关注变得淡然起来,只说了句:“你回去看看吧!要不开我的车子去。”
杜锋急急地说:“谢谢六哥,不用了,我坐出租车走。”说完就招手打了个出租车,风驰电擎般地走了……
——“要想彻底消灭孙老六势力,就必须在孙老六的身边安插上眼线,这样才能密切注视孙老六势力团伙的动向,拿到孙老六势力团伙的犯罪证据。”
这是张子航和“瘦龙”所商定下的消灭孙老六势力的第一步计划。
但是,怎样才能在孙老六身边安插下眼线,令张子航和“瘦龙”大费脑筋。
张子航认为,如果用自己的人,短时间内不可能接近孙老六,还容易暴露身份,不如采取相应手段,直接利用孙老六内部的人,那样才会使孙老六防不胜防。
经过一番调查后,他们最终把目标锁定在孙老六的贴身保镖杜锋的身上。
因为杜锋这个人有弱点,比较重感情,他虽然没有结婚,但在外面有一个情妇,情妇还为他生了个儿子,现在已经三岁了,杜锋十分疼爱这个孩子,经常带着钱财和物品回去探望他们。
一个人只要有弱点,就很容易被人利用。
张子航和“瘦龙”马上带着几个人找到了杜锋情妇的家。
杜锋情妇的家住在赢州市北元路丰华小区,其实这栋房子是杜锋自己掏钱买给他的情妇和儿子的。
小区内干净整洁,是一处花园式住宅区,张子航和“瘦龙”等人径直来到了二单元四楼。张子航让众人躲在一边,抬手按响了门铃。
隔了一会,屋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找谁呀?”
声音离门很近,那女人似乎正在从门镜中窥视着张子航。
张子航将手中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包裹在面前晃了一下:“锋哥让我给嫂子带一点海鲜过来。”
那女人听说杜锋给她带东西来,完全打消了警觉性,“咔嚓!”一声就将门打开了,张子航和“瘦龙”等人立即乘虚而入。
那女人见一下拥进这么多人,顿时感到情况不对,忙把身边一个两三岁大的男孩儿搂在怀里,退到一边。
进来的几个人在房屋的四处转了转,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回到了客厅。
张子航将门锁上,打量了一下杜锋的情妇,只见她三十左右,长的虽然不十分漂亮,但很有风韵。她此时紧搂着自己的儿子,好象生怕别人会伤害到孩子。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要怎样?”那女人声音颤抖地连续发问。
张子航站到那女人跟前,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说:“你别管我们是什么人,总之,你只要听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母子的,我们来只是想找杜锋帮忙办点事情,需要你打电话让他回来。”
那女人眼睛闪动了一下,摇头说:“我不知道锋哥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
这时,“瘦龙”瞪起眼睛,冷哼一声道:“笑话,你会不知道杜锋的手机号码?我看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也不会和我们合作。”说罢,他冲身边的几个人使了一下眼色。
有两个男子不由分说,上前就将那女人怀里的孩子抢了过去,那小孩骤然受惊,“嗷!”地一下哭了起来。
那女人立时慌了神,眼泪也流了下来,她连忙说:“别伤害我的孩子,我知道!我知道……”
“瘦龙”厉声说:“知道还不快打。”
那女人抽泣着,畏畏缩缩极不情愿地走到电话机跟前,刚要抓电话,“瘦龙”却在一旁按住了那女人的手,提醒说:“你可别耍什么花样,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你就对杜锋说你儿子高烧不退,可能是食物中毒,叫他马上回来送你们去医院。”
为了怕孩子的哭声在电话中惊动了杜锋,张子航吩咐人将孩子抱进了卧室。
那女人担心孩子的安慰,左右两难,犹豫了半晌,终于拿起了电话乖乖地按照“瘦龙”的吩咐和杜锋作了简短通话。
放下电话后,那女人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中,她似乎和杜锋的感情很深,竟呜呜哭了起来。
“瘦龙”将她推进了卧室里,有人把孩子交给了她。那女人怕吓着孩子,便强忍住泪水哄起了孩子。
张子航和“瘦龙”等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小声地闲聊着,慢慢地等着杜锋。
没过多长时间,门铃就响了起来,并且从门外传来一声急促的问候:“艳红,你和孩子怎么样了?”
张子航和“瘦龙”等人迅速站了起来,“瘦龙”打了个手势,让众人在门边埋伏起来,由张子航拉开了房门。
房门刚开一条逢,杜锋就心急火燎地闯了进来,他还没等看清怎么回事,就被门旁埋伏的人掀倒在地。
杜锋挣扎了几下,没有挣脱,双手已被绳子捆了起来,接着就被人提留着推到了沙发上。
杜锋心知出事了,他坐稳了身子,定睛细看了一下满屋子的人,胆蓄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可是孙老六的人。”
“瘦龙”“呸!”地吐了一口唾沫,冷冷地说:“孙老六的人又怎么样,你们杀死徐战东的时候,就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横尸街头?”
杜锋眼中露出了惊惧之色,脱口道:“你们是段二胖子的人?”
“瘦龙”伸手拍了拍杜锋的脸蛋,狞笑着说:“在赢州市除了段二胖子的人,还有谁敢动你杜大保镖。”
杜锋把胸脯一挺,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要杀、要刮,最好给个痛快的,我杜锋可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瘦龙”哧了一下鼻子:“呵!你想死呀?那就让你的情妇和儿子一起陪你去死吧!”
杜锋蓦地一惊,瞪大了眼睛,他此时才想起了自己的情妇和私生儿子的安危,连忙问:“你们把她们怎么样了?我的事情和她们无关。”
“瘦龙”手指着关着门的卧室:“你放心,她们现在都好好的,只要你答应为我们做一件事,我们是不会难为她们母子的,如果你不肯的话,嘿!嘿!你应该知道咱们黑社会人做事的手段。”
杜锋的口气明显软了下来:“你们想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瘦龙”蹲下身子盯着杜锋的眼睛说:“我要你随时向我们汇报孙老六的日常动向,帮我们收集着点孙老六及他手下人的犯罪证据。”
杜锋的瞳孔在收缩着:“你们想要干什么?”忽有所悟地问:“难道你们想借警察的手除掉孙老六?”
“瘦龙”有些佩服地拍了拍杜锋的肩膀:“他妈的,没想到你小子还挺聪明的,一点就通。”
“这不可能,我绝不会背叛六哥的。”杜锋说的斩钉截铁。
“瘦龙”面有怒色地说:“难道你为了友情就不要亲情了?你舍得你的情妇和儿子和你一起陪葬?”他说着走到卧室的门口,顺手推开了房门。
卧室里,正有两个男子用匕首逼着杜锋的情妇,情妇怀中的孩子不谙世事,看见杜锋还喊了一声“爸爸!”
那女人斜眼瞅瞅按在自己脖子上的那把匕首,又乞怜地望向杜锋,不敢出声。
杜锋的喉咙在剧烈地蠕动着,他没有说话,因为现在这种情况,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瘦龙”继续游说:“杜锋!你要想清楚,孙老六早晚有一天要灭亡的,以他的势力怎么能斗得过我们段二哥,你跟着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再说,孙老六一直都不器重你,他有什么事情都喜欢和方保信商量,在他的眼中你只是一个武夫,你在他那里永远都不会有出头的一天。”
杜锋的眉头跳动了一下,“瘦龙”的话似乎触动了他的伤疤,他的额角泌出了密密的汗珠。
“可,孙老六一倒,我也跟着完蛋了。”杜锋的忠义之船开始偏离了航线。
“这个你不用顾虑,我们已给你准备了两条后路,一是,孙老六倒台后,你可暂到外地避一避,风头一过,你可以回来跟着我们段二哥干,陆地、港上任你选。二是,我们给你两百万,孙老六一倒,你马上带着你的情妇和儿子远走高飞,爱去哪儿,去哪儿。”“瘦龙”缓缓地说。
杜锋低着头,沉默不语。
“瘦龙”伸手为杜锋解开了手上的绑绳,淡淡地说:“我们可以给你考虑的时间,但是你的情妇和儿子我们却要带走,如果你坚持要选择忠义的话,你就等着给她们母子收尸吧!”
然后,“瘦龙”和张子航带着众人,强逼着杜锋的情妇和儿子下了楼。他们走时,看也没看杜锋,仿佛杜锋已经成了他们手中的一张牌,想什么时候发牌,就什么时候发牌。
屋子里转眼变的空荡荡的,只剩下杜锋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他此时就象是一个霜打的茄子,彻底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