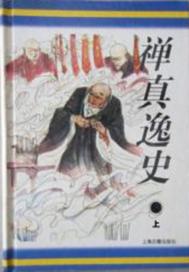段敏在金夜迪厅又出现了,这回她是一个人来的。
她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鸡心领的高弹内衣,将她的一双小巧的乳房束得高高地突起。她下身穿着一条藏青色的高弹牛仔裤,紧紧地箍住了她浑圆的臀和笔直的腿。
她背着双手,挺着胸脯,还是目高一切的样子,就象是一位中央首长在检查工作。
徐战东听说段敏来了,眉头马上就皱了起来。段敏虽然不是常来这里,但她每次来都要耍耍小姐脾气,真有些让徐战东吃不消。
段敏可是段二胖子唯一的女儿,宠爱的象心肝宝贝似的,谁敢得罪她,徐战东在她面前也只好装孙子。
徐战东强展笑容地来到段敏的面前:“大小姐,今天来怎么事先没打个招呼?”
段敏冷哼一声:“怎么?事先不通知就不能来呀?”她一边说着,还一边不住地扑扇着她的那双大眼睛四下张望着,似乎在找什么人。
徐战东到底是老江湖,他一眼就看出了段敏的心思:“怎么?大小姐!你今天来该不是要找那张子航的别扭吧?”
段敏果然阴着脸问:“他哪去了?你那天不是说要他向我道歉吗?”
徐战东苦着脸说:“你还记得啊!你能不能就当不认识他,再说人家也没对你怎么样呀!”
段敏叫了一声:“还没对我怎么样?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顶撞我,叫我的脸往哪儿搁。不行,你马上去找他来见我。”段敏语气坚硬地说。
徐战东见状无可奈何,只好到后台去找张子航。
张子航正坐在休息室里的一张椅子上和别人聊天,听说段敏要找他,连连摆手:“你就说我不在吗!”
徐战东“咳!”了一声:“你不知道她的脾气,她认准的事情是撞到山墙上也回不了弯了。你今天是逃得了初一也逃不过十五,你过去跟她说几句好话,不就什么都解了吗!”说着不由分说,强行把张子航从椅子上拽了起来:“走!走!”
张子航极不情愿地就被徐战东拖到了前台。
段敏坐在看台的一处角落里,见二人来了既没起身,也不说话,她斜着眼睛就象没瞅见似的。
徐战东赶紧用手指戳了张子航后腰一下,张子航不由自主地往前抢了两步。
事到如今,张子航只好干咳了几声,有些尴尬地伸出右手,想要和段敏握手言和,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段敏,只“段!段……”几声,没有说出话来。
没想到段敏倒爽快了起来,她提示了张子航一句:“你就叫我小敏吧!”她语气象似缓和了很多。
张子航趁机下台,笑了一下诚恳地说:“以前多有得罪,请你见谅。”
段敏这时站起身来,拿出了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算了!我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孩儿!”说罢和张子航握了一下手,嘴角却露出了一丝胜利的微笑。
徐战东在一旁圆场说:“哎!这就对了,都是自家人,何必弄的象仇人似的。”
段敏长嘘了一口气,她好象把这几天的闷气都挥发了出去,她忽然拍了拍扁平的肚子问徐战东:“哎?你们俩吃饭了没有?”
徐战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漫不经心地说:“都什么时候了,早吃过了。”
段敏有些娇嗔地说:“你们吃了,可我还没有吃呀?”
徐战东失笑道:“你没吃,你就找地方吃去呗!我们这里又拿不出饭菜招待你。”
段敏咯咯一笑,黑水晶般的大眼睛眨了一眨:“我要你俩陪我去吃。”
徐战东没想到段敏今天把他和张子航两个人黏糊上了,他可不希望和段敏在呆一起,她正经的时候象一个成熟的女人,不正经的时候象一个顽皮的孩子。徐战东忙推托说:“这可不行,我走了,这里一旦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段敏嘴一撇,露出一副不屑的表情:“能出什么事,谁敢在我爹的场子闹事呀!再说,这里没有你,迪厅也照样开,地球也照样转,你别拿着我爹的鸡毛当令箭了!”
徐战东象似下定决心不会去了。段敏越说他,他反倒在看台的凳子上坐了下来,还翘起了二郎腿:“总之我不去,都吃饱了还吃个什么劲呀?你想塞旱鸭子呀?要不让航哥陪你去吧!”
段敏居然真的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她一把抓住了徐战东的手腕:“不行,今天你们两个都得去,你不能扫我的兴。你不去,谁来结帐啊?”
徐战东指着段敏笑说:“原来你叫我陪你去吃饭,长得是这个心眼啊!”
段敏一努嘴,不乐意地说:“嘁!真是小看我段敏,说说你就当真,吃顿饭才几个钱呀?我就是天天请你们吃大餐,我也能请得起。”
她本来左手抓着徐战东,这时右手又抓起了张子航的胳膊,耍起了泼皮:“哎呀!走吧!别婆婆妈妈的啦!你以为你是谁呀?还得叫我三叩九拜呀?”
徐战东被段敏闹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站起身说:“那你也得先让我把迪厅里的事务安排一下吧?”
段敏嘻嘻一笑,放开了徐战东的手腕:“行!”
徐战东在金夜迪厅里,可以说是说一说二的人物,迪厅里的大小事务全都由他负责处理,这也是段二胖子对他的高度信任。
徐战东招手叫来一个服务生:“你去把阿忠和阿豪叫来。”
阿忠和阿豪是徐战东的近身手下,二人对徐战东一贯是忠心耿耿,言听计从。
很快,阿忠和阿豪从黑暗的一角转了过来,这二人都很年轻,不过长得有些干瘦,看上去象是有点营养不良。他们首先向段敏打了声招呼,然后问徐战东:“东哥!你找我们有什么事?”
徐战东望着来来往往的跳舞人群,嘱咐二人说:“我要陪段小姐出去吃点饭,你们在这里盯紧点,千万别走开,有什么事,打我手机。”
二人齐声称是。
徐战东将手中吸剩的烟蒂扔在脚底踩了踩,回头对段敏说:“行了,大小姐!你说上哪儿去吃吧?”
段敏歪着头,想了想:“咱们就去这附近的‘海鲜王酒楼’去吃海鲜吧?”
徐战东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那还不都随你!”
段敏脸上立时旋起两个小小的酒窝,她的笑容看起来是那么的天真可爱。段敏就是这样的人,她烦恼的时候,是看谁也不顺眼,好象每个人都欠她八百吊钱似的;她高兴的时候,就心花怒放的非要缠着别人同她一起分享不可。
段敏今天晚上好象很开心,开心的就象一只欢快的小天使,连走起路来都象要飞起来一样。
“海鲜王酒楼”在金夜迪厅的北面,隔着两条街。如果步行就有点远,要是开车就很近。
按照徐战东的意思是让段敏开车去,可段敏说什么也不同意,她说开车多没意思,一转眼就到了。出来为的就是活动活动筋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人活着就要有个精气神,一步也不想走,岂不越来越懒,越懒越没精神,人没有精神就容易生病,生了病又岂能长寿……”
听着段敏叨叨个没完,徐战东急忙制止她:“打住,我走行吧,我走换你个清静。”
徐战东当然拗不过段敏,他在段敏面前就象一个奴才,这一辈子也别想翻身了。谁叫段敏是段二胖子的女儿呢!谁叫段二胖子是自己的老大呢!
到了“海鲜王酒楼”,他们三个人要了一个雅间,段敏拿起菜谱看了看,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吃,便自己一个人念念不绝点起菜来,什么糖醋鲤鱼、香酥黄鱼、葱爆鱿鱼丝、酱焖拔勺鱼、糖烤对虾、清蒸螃蟹……她点到第十个菜的时候,嘴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她这一顿乱点,可把坐在一边的张子航点了个心惊肉跳。
张子航本就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一直是父亲用他那点微薄的工资来支撑着这四口之家。因此,张子航小时侯还过了一段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近几年,他和哥哥相继参加了工作,父亲又连年涨工资,家庭条件才有所好转。
虽然如今张子航跟着徐战东走了下坡路,但他的内心还没有完全从勤俭朴素、反对浪费的熏陶中走出来。
他听段敏口中振振有词,点个没完,早就按耐不住了,连忙制止说:“我看这些足够了吧?”本来徐战东和张子航就吃过饭了,就算没有吃,三个人要想吃光十几道菜,恐怕撑破肚皮也装不进去。
张子航一开口,段敏的嘴果然就闭住了,她倒好象很听张子航的话。
幸亏张子航说的及时,要不然,她这一顿饭还不知要浪费多少钱。
在清朝末年,慈禧太后有一顿宴席花去万两白银的惊人记录,幸好段敏不是慈禧,如果她今天坐在慈禧太后的位置上,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段敏可是没有吃过苦的,她的爹爹可是有钱有“势”的,她在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养尊处优惯了。特别是这几年随着她爹爹的势力日益壮大,她就更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钱对于她来说,伸手就有人给,容易极了。
菜上齐后,段敏倒不怎么吃,反而一会儿给徐战东夹菜,一会儿给张子航夹菜,忙的不亦乐乎。徐战东和张子航的肚子早已没有空隙了,只能望菜兴叹。
段敏的兴致很高,就象一只小燕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别人根本就插不上嘴。她不论说什么,徐战东都说“对!”“是!”,他就象是一个是一个古老的钟摆,总在机械地回应着。
张子航一直都不怎么搭腔,他本就不擅言谈。不过他觉得听段敏说话倒挺有意思,她时而老气横秋,象知道的很多;时而童心未泯,说的不着边际,弄得张子航有时候也忍俊不禁。
他们三人在这里花天酒地、高谈阔论,却不知金夜迪厅那边出事了。
段敏、徐战东、张子航三人走了没多久,迪厅里就呼啦啦涌进二十几名男子,他们堵在迪厅的出入口,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冰若寒铁。
为首的一人,身材高大,身穿一件黑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一个白色的骷髅头。他荒眉毛,三角眼,一脸的横丝肉。说不出的狰狞和凶恶。
他用眼睛仔细扫视着迪厅的上上下下,忽然上前几步揪住了一个服务生的脖领,语气阴冷地问:“徐战东在哪儿?
那服务生被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忙摆手说:“我不知道。”
那黑衣人人骂了一句:“去你妈的!”松开服务生的脖领,却踢了那服务生一脚,那服务生就势赶紧逃走了。
这些人的进入,引起了徐战东的两个近身手下阿忠和阿豪的警觉,他们二人走了过去,打了声招呼:“哎!哥们儿,你们是哪一条道上的?这里可是段二爷的地盘。”
阿忠和阿豪本想用段二胖子的名声压一压这些人,让他们知难而退。谁知为首的那个黑衣人,却张口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横眉冷对地说:“我砸的就是段二胖子的场子。”
他的“砸”字一出口,阿忠和阿豪就知道要出事了,但是二人还很镇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咱们有话慢慢说。”
这时,迪厅里的音乐忽然停至了,满屋的灯光都亮了起来,有十几个壮年男子从迪厅的四处开始向阿忠和阿豪的身边靠了过来。
所有跳舞的人都静止了,连看台上的人也站了起来,他们仿佛也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有的人开始想溜,但是门被堵住了,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这时,那黑衣人叫过来一个矮个子的手下,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那个手下仔细察看了一下阿忠和阿豪身边的人,然后摇了摇头。
那黑衣人挺直了腰,摸了摸下巴,冷冷地说:“你们去把徐战东给我叫出来,这件事和你们没有关系。”
阿豪也不客气地说:“对不起,他不在这里。”
“那他去哪儿了?”那黑衣人尖声问。
“无—可—奉—告!”阿豪一字一顿地回答,显得毫不示弱。
两个人已开始较上了劲。
迪厅内的空气顿时凝结了,所有的人就象被冰封住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他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一场风雨的到来。
那黑衣人的脸色变越来越难看,脖子下面的青筋已在条条爆出。忽然他高高地举起手臂向前挥了一下,口中狠狠吐出一个字:“砸!”
他身后的那二十几个手下随即从后腰抽出砍刀口中叫啸着冲了上去。
由于阿忠、阿豪等人事先没有准备,只有几个人带着“家伙”,其余等人只好操起迪厅内一些可利用的东西进行抵挡。一时间,两伙人如狼似虎,前追后赶,直打的昏天暗地。
黑衣人带来的那些人一边嘶杀着还一边有意地打砸着迪厅内有价值的设施。
那些跳舞的人群早已远远躲到了看台的后面,他们触目惊心地观望着两帮人的拼命打斗,就象在观赏一场斗牛比赛。
他们也知道,只要自己不乱动,这些人是不会伤害到自己的。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嘶杀声渐渐由大变小了,最后只听到了几声铁器落在地上所发出的“叮!当!”的声音。接着,迪厅内再一次陷入了寂静。
战斗结束了。
输的一方自然是阿忠和阿豪,他们本就人少,何况对方是有备而来。
偌大的迪厅内一片狼迹,有几个人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阿忠半蹲在舞台一角,他身上血迹斑斑,看气色倒象没什么大碍。只有阿豪还站着,但他的一只下垂的手臂却在慢慢地滴着鲜血。
有人喘息着喊了一声:“忠哥、豪哥快给东哥打电话,让他搬人过来。”
阿忠闻言方才反应过来,他连忙掏出了腰间的手机。可他还没等拨完号码,就见有人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抬手将阿忠手中的手机打飞了出去,并抬起一脚将阿忠踢了个四脚朝天。
只听那个黑衣人大吼了一声:“谁也不准和外界联系,谁要是想通风报信,我就砍了谁。”说罢,他举起手中的砍刀,狠狠地跺在了看台边上的不锈钢护拦上,只听“当!”的一声,声音震耳、火星四溅。
黑衣人这句话不但是对阿忠、阿豪等人说的,也是对看台上观望的人群提出了严重警告。
前来跳舞的客人当然不会没事找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大多数人的本性。再说,来迪厅跳舞的全都是小青年,他们还等着看热闹呢!
这时,那黑衣人的手下已封住各处可以出入的地方,并将躲藏在休息室、更衣室、卫生间等一些地方的人驱逐到了厅里,以便于看管,防止他们私下有什么不轨举动。
那黑衣人看大局已定,脸上渐渐露出了笑意,而且越笑越得意,他走到阿豪的跟前用砍刀的侧面拍了拍阿豪的脸,狞笑着问:“怎么样?还倔不倔了,该告诉我徐战东在哪儿了吧?”
阿豪没有动,他知道动也没有用了。但他仍然很傲,冷冷地说:“不知道!”
那黑衣人突然举起手中的刀,“啪!的一声,一刀面子煽在了阿豪的脸上,阿豪的脸立时肿起很高,他一张嘴,一口血水就喷了出来。
那黑衣人一招手,马上走过来几个男子将阿豪按倒在地。
那黑衣人蹲下身子,凶神恶煞似的又问:“快说!徐战东到底去哪儿了?”
阿豪用恶毒的眼身望着那黑衣人,大叫道:“有种你就砍死我。”
那黑衣人脸上的横肉急促地抽搐了一下,他伸手拽过阿豪的手腕,一刀剁了下去。
阿豪惨叫了一声,他的两根手指已从他的右手脱离了出去。
“啊——”看台上传来几个女生的惊声尖叫,有的竟还呜呜哭了起来,她们此时才感到了事情的恐惧。
那黑衣人站起身,又望向了舞台下脚已吓得缩成一团的阿忠,冲身边的几个人使了个眼色。那几个人便走过去将阿忠象拖死狗一样拽到了那黑衣人的脚底。
那黑衣人用脚踩住了阿忠的脑袋,阴森森地问:“你说,徐战东去哪儿啦?”
阿忠早已吓的魂不附体,但他还在本能地喊着:“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你们饶了我吧!”
那黑衣人弯腰抓住了阿忠的头发,恶狠狠地说:“不知道是吧?来人啊!把他的两只手剁下来。”
立即有两人走上前将阿忠的胳膊摁住了。阿忠发出了猪嚎一般的叫声:“啊——!你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那黑衣人用刀面重重拍了阿忠的脑门一下:“想叫我饶你,你就快说!要不然,你可别怪我心狠。”
阿忠吓得鼻涕和眼泪都流出来了,他凄厉地哀号声回响在迪厅的上空,就象是鬼叫一样。
“我!我说!我说呀……”阿忠最后的忠义防线终于崩溃了:“他!他去了附近的‘海鲜王酒楼’……”他说完已泣不成声,就象是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被父母打骂了一样。
黑衣人仍不罢休地追问:“他和谁在一起?”
阿忠抽泣着,用嘶哑的嗓音说:“和张子航,还有段二哥的女儿段敏。
“段?”黑衣人低声念了一下,他似乎对这个“段”字很感兴趣:“哪个段二哥的女儿?”
阿忠早已完全丧失了自我,将什么都抖搂了出来了:“就是段二爷的女儿……”
那黑衣人冷笑了几声,眼中放出了一种只有夜狼觅到食物后才具有的光。他晃了晃脖子,磨了几下牙,就象是一个正准备要吃人的怪物,显得异常恐怖。
他退后了几步,向身边一个络腮胡子的人吩咐道:“刘兴!你带着你的手下先在这里守着,我带我的人到海鲜王酒楼去劫徐战东。”他低头看了一下表:“估计有二十分钟我们就到了,所以二十分钟后你马上从这里撤离,这里不宜停留太久,以防生变。”
说完,他也没等那人回应,领着十来人就象一群夜蝙蝠一样,“呼啦啦!”地拥出了迪厅。
段敏、徐战东、张子航三人从酒楼出来的时候,街道上已是车少人稀了。晦暝的夜空中有浮云飘动,看不到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寂寥地闪着;街道两侧的路灯呈烟朦的橘黄色,均匀地地撒在路面上。
段敏走在徐战东和张子航的中间,她还一手搂着一个人的胳膊,三人在人行道上便形成了一个横排。一个男青年从对面走了过来,不小心蹭了徐战东肩膀一下,徐战东定住身,回头骂了一句:“你妈的,你没长眼睛呀?”
那人也回头望了徐战东一眼,不过他没敢言语,匆匆地走了。
段敏拽了徐战东一下:“算了!别惹事了,我还要回去跳一会儿舞呢!”
徐战东便没再说话,三人继续前行。当他们走到第一个路口时,就见从对面的人行道上急匆匆走过来十来人,当前一人身材高大,身穿一件黑色的T恤衫,胸前还印着一颗白色的骷髅头,在路灯的照射下,显得分外扎眼。
徐战东一眼就看出这些人绝不是普通的市民,也不是社会上一般的小地痞,而是一帮长期扎根在黑社会的老手,于是就不禁多瞅了两眼。
他这一看,对面的那些人也刚好向徐战东这边观望了过来。目光相对,那些人忽然放慢了脚步。彼此打量的一瞬间,就听对面那些人中有人高喊了一声:“没错!他就是徐战东。”
听到这一声喊,那十来人就如同听到了百米赛跑的枪声一样,挥动起手中的砍刀向徐战东等三人奔了过来。
徐战东见势不妙,拉起段敏和张子航的手就跑。段敏惊诧地问:“东哥!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是什么人?”
徐战东气喘吁吁地说:“搞不懂,闹不好是孙老六的人。”说着他带着段敏和张子航拐进了一个胡同。
徐战东知道对方人多自己人少,不能力敌,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本想带着段敏和张子航走几条容易躲避的路,将后面的人甩掉。不曾想胡同里黑,路不好走,段敏一不小心歪了一下脚,竟摔倒了。等徐战东和张子航扶起段敏时,后面的人已追了上来,徐战东和张子航只好赤手空拳和对方展开肉搏战。
由于对方的目标主要是徐战东,所以他们的大部分火力都集中在徐战东身上。徐战东象一头发怒的狮子,左闪右打,虽然身上被连砍几刀,但依然勇猛异常,并且还拼着性命从对方手中抢过一把砍刀。
张子航虽然没有徐战东威猛,但他灵动性比较强,前穿后跳,总能躲过对方的砍刀,不过手臂处也有几道轻微的划伤。
要说他们三人中最幸运的是段敏了。他是女性,自然就没有人对她实施暴力了,虽然有两个人向她逼了过去,但态度也很“温柔”。
其中一人奸笑着:“哈哈!没想到啊!那段二胖子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真不知道他是哪辈子修来的福”
段敏后退着,已被逼到了一处墙角,她后身紧贴着墙壁,面有惧色地说:“你们别过来,你们如果敢动我一下,我爸爸知道了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另一人失笑了一声:“小妞儿!我们是不怕你爸爸的。不过呢!你也不用害怕,。只要你乖乖地听话,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说着,他伸出了左手,慢慢抓向了段敏的前胸,敢情这个人是个十足的花心,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忘占女人一下便宜。
这一情况,被在一边打斗的张子航看在眼里。张子航一闪身,急忙从后面窜了上来,他一伸手便抓住了那人的胳膊,并就势一扭,只听“嘎巴!”一声,那人的胳膊就被张子航给卸了下来。
张子航这一手,是警察抓捕罪犯时惯用的手法,只不过比平时狠了一些。
那人惨叫一声,倒在地上,疼的直蹬腿,就象一只被抹了脖子的大公鸡。
与此同时,段敏也趁机做出了应变反应。段敏本就经常跳舞,腿脚比较灵活,她抬起一脚,正踹在另一个人的下裆上。那人“嗷!”叫了一声,弓起了身子,在原地转起圈来。
这下那人却被彻底激怒了,暴露出了他凶恶的本性,举起手中的砍刀便朝段敏砍了过来。
段敏似乎被吓呆了,她茫然地望着砍刀从自己的面前落下,却忘记了躲避。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子航纵身扑向了段敏,将她压倒在地。但在那一刹那,张子航的后背却被那人的刀由深至浅划出足有半尺长的口子,顿时鲜血浸透衣衫。
那人红了眼睛,举刀还欲再砍。卧在段敏身上的张子航急速翻身,抬起一脚正中那人的小腹。
那人根本没有防范张子航这一招,一下就被蹬出了十米多远,半天没有爬起来。
张子航慌忙拉起段敏,向胡同的另一端奔去。
接着,就听到有人大喊:“站住!别走!”有几人提着刀从后面紧追了上来。
张子航抓着段敏的手跑着跑着,忽然感到脚下被东西拌了一下,身子禁不住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原来这路边不知因何堆放了一堆鹅卵石。危急之中张子航俯身便抄起鸡蛋大的石子就朝追来的那几人一顿乱撇。
只听,黑暗中传来两声“啊!啊!”的叫声,显然是有人被石子击中了。
果然,那几人停住了脚步,闪身躲在了一边,一时不敢靠近。
张子航趁机拽着段敏闪进了另一条胡同。就这样,经过两折三拐,他们渐渐地摆脱了后面的那些人,来到一条有路灯的街道上。
这时,张子航才感到背后传来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脸上的肌肉也随之扭曲了一下。
当段敏看到了张子航后背的刀伤时,不禁吓了一跳,她惊叫了一声:“航哥!你受伤了,流了很多血。”
张子航强忍着伤疼摇了摇头,他推了段敏一把,喘着粗气说:“别管我,你快走!”
段敏也是娇喘吁吁,惊疑地问:“那你呢?”
张子航不假思索地说:“东哥还在里面,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说着,张子航从路边找来一根小孩手臂粗细的木棒,转身又返了回去。
张子航在胡同里深一步浅一步地小跑着,可是,此时的胡同里既看不到人影,也听不到打斗的声音了。张子航心下生疑:“是自己走错了路,还是徐战东他……”他有些不敢往下想。
放慢了脚步,张子航一个胡同一个胡同的找。由于这里的胡同纵横交错,张子航也记不清自己和段敏刚才到底是从哪个胡同里跑出来的。
最后,张子航终于在一条胡同的拐角处发现了徐战东。
徐战东斜倚在墙边,歪着脑袋,满身都是血迹,他双手捂在自己的左肋下面,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是昏迷了过去还是死了,行凶的那些人早已没有了踪迹。
张子航胆蓄地喊了一声:“东哥!”他走到徐战东跟前,俯下身子发现徐战东双眼紧闭,面色很苍白。
“东哥!”张子航又叫了一声,声音已有些颤抖。他丢掉了手中的木棒,开始用手掌拍打着徐战东的脸。
徐战东竟然“哼!”了一下,慢慢睁开了双眼,但眼神却显得很空洞。
“你怎么样?”张子航急切地问。
徐战东望着张子航,微微苦笑了一下,用孱弱的声音说:“航哥!我!我恐怕不行了,这些人存心是想要我的命。”
张子航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捧住了徐战东的脸,嘶声道:“东哥!你不是告诉过我,你们用的这种刀是砍不死人的吗?”
徐战东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而是放开了捂在左肋下的双手。
张子航这时才发现,徐战东的左肋下面竟然插着一把匕首,而且直没刀刃,只剩下两寸半长的刀柄露在外面。
张子航惊呆了,一时手足失措起来,他本想伸手去触摸一下那把刀柄,但手指抖了几抖,又缩了回去,喉结处剧烈地蠕动了几下,脸上一片茫然。
好一会,张子航的理智才有所清醒,他抻直了嗓子:“东哥!没事的,我送你去医院,我送你去医院……”说着张子航艰难地背起了徐战东。
徐战东似乎被张子航的举动感动了,他眼中有亮晶晶的东西一闪:“谢谢你!航哥!”
张子航不说话,他迈起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走着。徐战东本就比张子航壮实,而且张子航又受了伤。张子航每走一步落在地上发出的“嗵!嗵!”的声音,就象是有人在敲打着地狱的门一样。
胡同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四周的人家似乎都已进入了梦乡,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张子航和徐战东两个人。
徐战东有气无力地咳嗽了几声,脸上的表情却显得出奇的平静,他轻轻叹了口气:“航哥,在这个世界上我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我十七岁那年,我父母就离异了,父亲舍我而去,母亲又改嫁他人,我怀着对父母的怨恨,开始和一些小地痞混在一起,从此走上了‘打、砸、抢’道路。后来,我遇见了段二哥,他很看重我,收容了我,我便跟着他吃尽了山珍海味,享尽了美女醇酒。哈!哈……”他干笑了几声:“我现在死了也值得了,值得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空旷和遥远,就象是从另一个空间里传过来的。
徐战东真的可以死的无憾了么?他的人生坐标难道就仅仅是吃、喝、玩、乐吗?没有亲情没有爱情还算是完整的一生吗?他的这一番话,是在向张子航表达他自己人生的空虚和失落,还是在掩饰自己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呢?
张子航低头看了徐战东一眼,借着微弱的光线,他看到徐战东的脸上浮现了一层灰色,一层死亡的灰色。
张子航的心直往下沉:“东哥!你别说话,你会没事的,你不会死的……”
几百米的胡同,仿佛一下子变的没有了边际,总也走不到尽头。
徐战东却象似快要睡着了,他耷拉着眼皮,有些梦呓地说:“航哥!象我们这种人,早晚有一天会走上这条路的,就算不走这条路,也迟早会被警察逮住,投进大牢……其实我也不想拖你下水,都是段二哥让我这么做的,他说你哥哥是刑警大队长,能把你网络在手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是航哥!这件事虽然本质上和我无关,但把你拉进黑社会却是由我一手策划的,你千万要原谅你东哥啊……”他在临死之时才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残忍地将一个无辜的人推下了火坑。
张子航感到鼻子一阵发酸,面对一个临死前真心向自己忏悔的人,他还能说些什么呢:“东哥!你别说了!我不怪你,我不怪你……”
徐战东凄凉地笑了一下,全身忽然颤抖起来,连牙齿也在不停地打颤。他一扫刚才面对死亡的那种平静,伸手紧紧抓着张子航胸前的衣服,好象很痛苦似的瞪大了双眼,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航哥!我!我还不想死呀!我还年轻,我还不想死呀!你救救我吧!航哥……”当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才深深感到了死亡的恐惧,萌生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可是,他的声音却越来越弱,到后来只有嘴唇在蠕动着,双手也无力地滑落下去。
张子航停住了脚步,他知道,一个生命消失了,就这样从自己的肩膀上永远地消失了。
在无边的黑暗中,张子航第一次感到了生命的渺小。悄悄地来,静静地去,留不下一点痕迹。什么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当你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世上所有的东西在你的眼中都会显得那么的苍白,可贵的只有生命,没有了生命,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张子航“咕咚”一声跪在了地上,此时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就象是一股清烟凝成的,经风一吹,也会象徐战东一样,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他感到了一阵眩晕,身子慢慢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