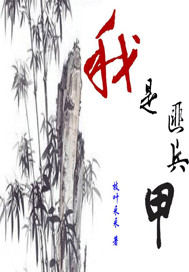田绪隆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那些人的身影慢慢扭曲,而后像泡泡糖般粘附在一起,变成一个巨大的、混沌的团,从那不可名状的团里,冒出许多狰狞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脸。这场面,像一幅抽象的油画,既艳俗又先锋,可田绪隆此时完全没有欣赏这幅后现代艺术的巅峰之作的心情,他的心脏内,原本奔腾着的血液像是见了鬼一样溜回血管里,而这也并不能怪它们——毕竟,田绪隆真是见了鬼了!
“我是谁?我在哪?”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什么牛鬼蛇神?”
“天灵灵,地灵灵,列祖列宗快显灵,妖魔鬼怪快离开……”
田绪隆的身体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坐起来,他满头大汗、面目狰狞,瞪大了眼睛,仿佛要撕碎面前那堵灰白的墙,像极了冲向风车时的堂吉诃德。他愣了几秒,忽然发现刚才的一切,那可怖、可憎、可恨的,集聚了人类一切的邪恶和黑暗的,如同嚼过无数次的泡泡糖一般的团,只不过是梦的幻影时,他先是仰头大笑,而后怅然若失,最后破口大骂,两个拳头抓狂地锤向身下那张早已摇摇欲坠的床…… “bang”的一声巨响之后,整个房间里只剩下钟表走时的滴答声,一片死寂之中,只剩下一脸无所适从的田绪隆、凌乱的床单和那张坠到地上的、散架的床铺。
田绪隆此时的内心是崩溃的,仿佛刚刚有一万只羊驼践踏枯了他内心仅存的处女地,它们还非常不客气地在上面排泄了一些本属于消化系统的残渣。他出神地盯着墙上的那四个大字,仿佛凝视着深邃而遥远的未知。墙上的时钟用时针、分针和秒针的角度变化组成一个个巧妙而隐晦的密码,仿佛在用这种方式提醒着面前那个呆滞的生灵:眼前并非静止,一切皆流,一切皆变。此刻的他,像极了一名正在仰望星空的、古希腊的贤者,试图用那可与苍穹比阔的远见,超越那目之所及,他的思想,仿佛已脱离于凡尘俗世,飞向九霄云外。但很可惜,田绪隆终究不是什么贤者,他顶多算个有想象力的俗人;钟表也没有表达什么隐晦的密码,如果一定要有,那么现在的时间是早上五点。田绪隆扭过头,望着窗外,那是一抹鲜亮的鱼肚白,好像昭示着黑暗的终结、万物的新生。最终,所有的愤怒、恐惧和孤独,都化作了一声轻叹:
“哎……”
极不情愿地起身、极不情愿地收拾床铺、极不情愿地刷牙洗脸,仿佛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了恶意,而自己,又是那么的迫不得已。有人说,生活本就是诗意的,田绪隆深以为然,只不过,在他看来,存在于他生活里的、那些所谓的诗意,如果有人愿意好好编辑一下的话,估计是一本不错的,充满了伤痕文学色彩的诗集。但他真的就这么惨吗?也不尽然。总有人和他语重心长地讲:“你就知足吧,你过得其实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了!多少人付出着比你百倍千倍的辛劳,却也无怨无悔,你又有什么可说的“?可看着那些衣着鲜亮、儒雅随和的人口若悬河地向他倾泻这些观点时,他又会陷入深深的纠结与怀疑:
“真的是这样吗?”
他不断的审视着自己的内心,恨不得挖出自己的心肝来“格物致知”,弄出个所以然。但他探究来探究去,终究也没有什么结果。于是乎,曾经鄙视“随波逐流”的他,特意去买了个最便宜的毛笔,弄了几张宣纸——看网上讲,宣纸分生宣和熟宣,生宣柔软,吸墨能力强,把握不好容易洇墨。他买的时候,还特意问了问店主,这是生宣还是熟宣?店主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指着自己拿出的一打纸,笑着说:“他们那些教国画的老师都买这个。你要几张?”田绪隆蒙了,不知道怎样是好,也懒得再去深究。于是,他装作自然的说:“那就这个吧,拿三张,再拿两支笔。”店家一边抽纸一边说:“笔在笔筒里,左边的三块,中间六块,右边的十块。”他想了一下,从左边和中间的笔筒各抽了一支,店家把宣纸塑料袋里,他接过那塑料袋,举起手中的笔,点点头,说:“算一下多少钱”。“十五块”。他把钱放到店家的手里,把两支笔扔进塑料袋,拎着袋子回到了家。他一回到家,便开始找出那瓶脏兮兮的墨汁。那瓶墨汁就放在木桌子的下面,他打游戏的时候,手舞足蹈,常常会踢倒那瓶墨汁,便是气急败坏,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躬身去扶,直到他买回来那笔和纸,要往碗里倒墨汁时,他才忽然发现:每次踢倒墨汁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把墨汁放到柜子里呢?
田绪隆看着未干的墨迹,有种说不出的感觉。那字迹龙飞凤舞,很野性,有种纯真的美。在这样的三尺天地里,黑与白互为映衬,用一种抽象的排列规则,向它唯一的观众,也就是它的创作者,传递着这样深邃而简单,这样明确又晦涩的信息:
随遇而安
田绪隆显然对自己的作品十分满意,他偷偷地想,这样的艺术应该裱起来,被大家拥簇着登堂入室,悬挂在某个艺术殿堂的正中央。人们常说:三分画七分裱。这幅作品只是缺个裱框罢了!那些所谓的艺术家的作品,不也都似这般“神采飞扬”吗?他还记得他小的时候在书法班学习时,老师让他每天都写同一个“和”字,写到最后差点不认识这个字了。后来,老师从一堆“和”字里挑了一张,装裱了一下——半个月后,田绪隆就收到了一张奖状,那上面写着:小学组,国家级二等奖。田绪隆心想,他绝对是有底子,有艺术细胞的!假若自己家有两个钱儿,能送他去学特长,当个艺术生,自己必定能有一番造诣。这样看来,他觉得自己的确是个被世俗的铜臭耽搁的,泯然于世俗凡尘中的艺术家。但眼前这幅因吸墨而变得褶皱的低档宣纸,也在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十分抱歉的提醒着他:
“穷鬼!别做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