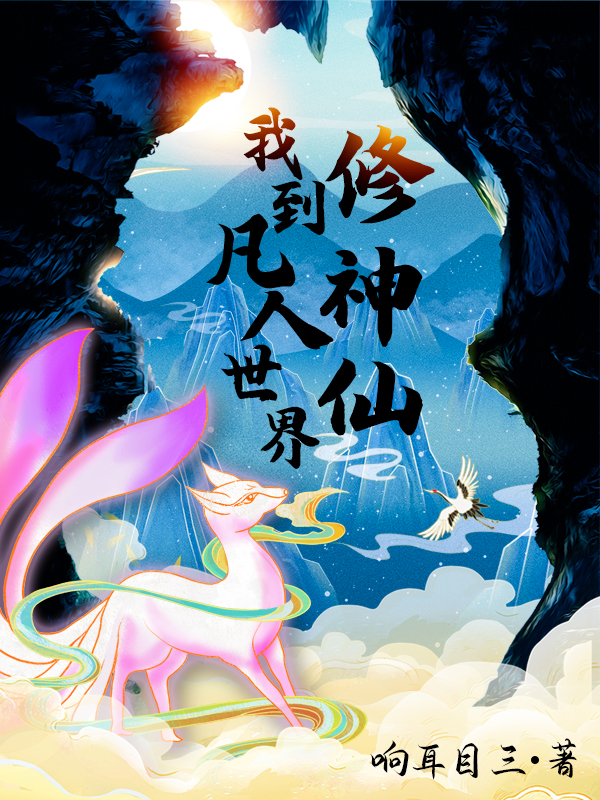在床上,桃子脑子像放电影似的,每一个片断在血淋淋地撕扯着伤疤。
房是土楼青瓦,围墙不高,两个男人在翻着瓦片和断树枝。
断树枝有长有短、有粗有细,细的像烧黑了的人的骨头。断树是晒在围墙头上,用来烧火做饭的。一到雨季,寨子边的浑如米汤的河水就从上游冲下断树枝,一同冲下的还有死牛死马和刺鼻的腥味。
桃的叔每年都唤那个傻子去河里拾断树断树,末了,给傻子一碗玉米饭。傻子吃着玉米饭,吃相如门口拴着的大黄河。
“妞,过来过来,看看沟里有什么,”四叔在唤着桃子。
“什么也没有啊,”桃子朝前挪了几步,眼睛向沟子瞟了瞟。她不愿意朝前走,围墙外的沟很深还臭,臭味是人尿猪屎的黑色臭味,她怕掉进沟里,妈妈说给她,掉进沟里,会淹死的。今儿她是要同妈去地里种玉米的,两个叔说要翻墙头,要她帮忙。一个五岁的孩子,又能帮什么忙呢!
“让你近点看,死妞,你不是想吃糖么,沟里有张钱……”
“没有啊,没有,看不见,”她迈着小步,又挪了几步,到沟边了,黑色的臭让她屏住呼吸,她准备跑开时,“呼”地一声,她跌进了黑色世界。
醒来时,她已躺在屋里,旁边坐着垂泪的妈。在她周身的疼痛里,妈在报怨:“我怎么说你就不听话呢,说让你不要去沟边,就是不听,这不,要是妈回迟点,就淹死了……”
“我头怎么这么疼,疼死了,”也用手一抹,是一手血,还有污泥。鲜红的血,让她吓得哭了起来。
“你被树头砸了,被围墙上掉下的树头砸了,你叔不是说让你不要过去呢,就是不听话!”母亲慎怪着,又爱怜地摸着她的头。
“我不去,四叔让去的……”
“还说,怎么会是他让你去的,小叔也说了,让你别去,就是不听话……”
头还在疼,血还在流着。那次流的血,让他从此怕上了血,每次看到血,都觉得有一把刀捅向自己。他更怕四叔和小叔了。那时她还不是很记事,后来,长大了,她想明白了,那是四叔和小叔设的一个套,他们是想要她的命。理由很充分,那天不是她主动去看的,是两个叔诱惑她去的,还有,就是那事发生后,也没见他们翻过墙头。
她确信是她命不该绝,要不是自己妈忘了拿玉米种子,不是妈回来救了她,她是肯定死了。妈一向是做事很细心的人,怎么会忘记拿东西的,种玉米,就只是带锄头和玉米种子,怎么会忘记了呢?
半年后,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她弱小的生命里。那天,别人都出工了,就剩下五叔、小叔和她。
抽了两支烟后,五叔和小叔在屋里忙起来,他们在接电线,妈也告诉她过,不能挨近电线,那根细小的线会被人电死,会把人烧成灰。
她在远远的地方看着。
“妞,过来帮叔拿着线下,”小叔在喊。
她只摇了一下头,不动。
“你聋了,让你来拿线下,”声音变大了。
她还是摇了一下头,不过步子向前迈了一小步。她怕了,身子有些颤抖起来。
“快过来,你怕想叫我用棍子料理你!”是在吼了,比大叫驴都吼得大。
她被吼得乱了神,开始向前跑,可能太急,也可能是怕,跌倒了,也不知道疼不疼,又爬起来,来到小叔旁边。
“拿着!”小叔把线递过来,她伸手了,不过她不捏前边播开皮的线头,她只拿后边。
“我让你拿前边!”男人把线塞向她那抖个不停的小手。
她把手缩了。
那双愤恨的大手还是捅向她,他硬把电线塞给她。
在推搡中,电线起火了……
那次,电没有电死桃子,倒是把她的小叔电着了。
桃子没死成,两个叔没让桃子死成。
长大了,桃子也渐渐明白,真想让她死的,是她奶奶,她想让桃子死,让桃子的妈死,好让桃子爹重新娶一个能为她家接续香火的女人。
桃子妈知道桃子觉得是叔故意砸她,是多年以后的事。
那天晚饭后,桃照着镜子,指着头跟妈说:“妈,这是我四叔和小叔砸的。”那时,桃子由于要做理疗,把头发全剪光了,疤痕很明显。
妈放下抹布,过来瞧着,摸着:“这么长的疤痕!”心和手都在打颤。
“是他们故意砸的,”桃没有多少伤感,心里只是在感激,自己活下来了。
“怎么可能,不会吧,他们可是你的亲叔。”
“妈你还记得吧,那天是你回来救了我,我相信命,那天你忘记拿玉米种了,去种地,却忘了带玉米种,要是你不回,我真是要死在阴沟里了,还好,活下来了。”
“我说他们要把我砸死,我死了,你就可以生个儿子了。”
这个戴一串佛珠的女人,有些相信,他们不喜欢女孩是真的。
她生下第二个女孩后,知道婆婆会对女婴下手,自己生生产剪断脐带后,对只有三岁的桃说,妈困得很,要睡一会,你不能睡,要看着妹。月科里要用草药洗澡,在进棚子前,对桃说,娃儿,妈洗澡时,你哪都不能去,要看着妹……
“还记得吧,那个人见人爱的小表妹,不是被舅家活活饿死吗?四岁了,还是被害死了!”
这是寨子里都知道的事,一心向佛的妈,也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