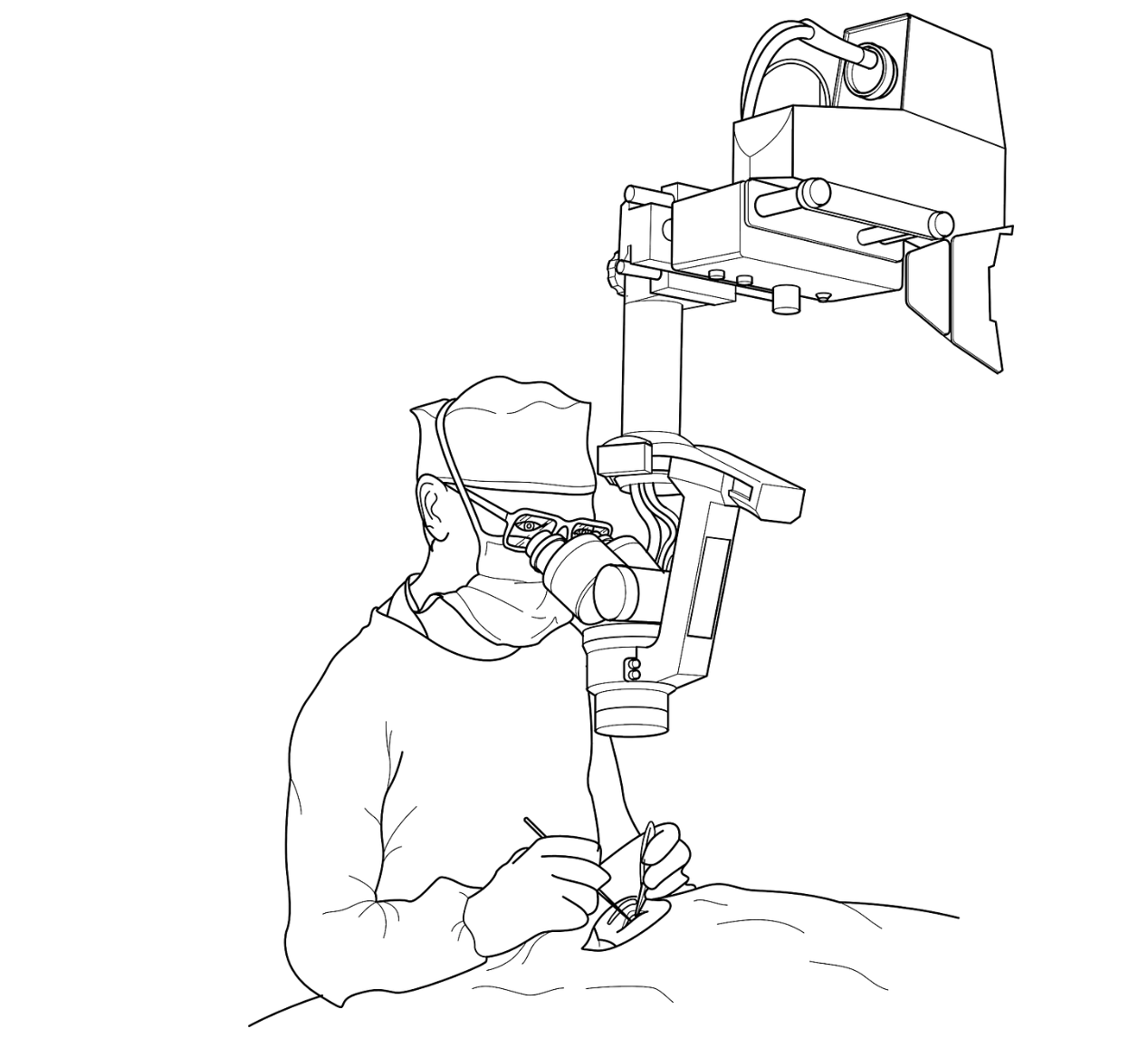在环城路KTV门口,“紫罗蓝”的荧光灯蛇星子般闪个不停。
六七个男男女女,东倒西歪地在挥手告别。
“真尽兴,下次……下次……再约,李哥。”
“好好!”
“明天怕……怕是……换节目,打……打牌咋样?”
“好……好……你说了算,高兴就好……”
“我先走了……”
“好……好,明天老地方见!”
各自打了出租车,各自回家了,像一群吃饱的野狗,各自归巢了。
最后一个走的,是桃子的丈夫。
他招了一下手,一辆出租车闪着转弯灯停了下来。
“去哪?啊,是李老师啊,这么巧?”
“你……认得我?”李想一边开车门上车,一边问。
“我杨纲啊,李老师!”
“杨纲,噢噢……”他使劲在想,也想不起有个学生叫杨纲的。
“李老师是回家还是?”
“回……回家,凤园小区。”
车子调了个头,冒着黑烟,往前驶去。
“李老师还教政治吗?”杨纲边开车边和李想攀谈。
“政治,啊……哈哈……我改教物理了……”李想也想不明白,怎么会这么说,说出“物理”时,又感觉“无理”这个上词很好,不禁“哈哈哈”地自顾自笑了。
三公里的距离,就在问一些生意难不难做、平时什么时候出车什么时候收车一些闲话中,就走完了。
他下车后,抬头看了眼家里的阳台,阳光上照出来的光,把家包围在黄红黄红的光影里,他使劲地揉了下眼睛,感觉头是有想晕,但不醉样不明显,他收回眼,一只脚伸出去,让它短一截,另一只脚伸出去,还短一截,身子在断脚的支撑下,向着左边摇一下,又向着右边摇一下……很醉嘛,站都站不稳,他挺满意。心想着自己活得太窝囊了,媳妇是太厉害了,媳妇太厉害,男人日子不痛快,今晚一定要借着酒劲,拾缀拾缀桃子。
一晚上,他的心情都不爽,眼看就要开学了,调动的事,看着得“黄”了。他心头生出怨气,觉得是自己那个“得势”的媳妇没有跟领导汇报……
上一年的调动,是自己没有处理好,还被桃子一顿训。
桃子进城了,自己还在乡镇中学,菊子打通了所有关节,就等着那一纸文件把自己领进城了。
“这事不要跟任何人说,包括你最好的朋友和家人。”桃子在电话里交待,她清楚,别的男人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自己的男人是嘴上虽有毛,可办事还是不牢。如果走露了信息,事情会出“岔子”的。
“我认得呢,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李想觉得是桃子多虑了。
学校的院子里,已有三三两两出进的老师,就要开学了,已有教师跟李想一样回到学校。李想在学校负责总务,他得先回家做一些后勤工作。
刚挂断桃子的电话,校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校长在电话里交待,让他到城里购买一批扫把。李想在接电话过程中,对校长以老子吩咐儿子样的口吻很反感,又想起媳妇说要发调令了,心说终于是奴隶翻身做主人了,就在电话里说:“校长,我已要调走了,这两天就下文件,这事你还是安排其他人去办吧。”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那……那个,李老师,这事确实再交你办是不合适了,你还是准备调动的事吧,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李想有些后悔刚才说的气话了,校长还是能关心下属的。
接下来的事,就让他难堪了,一直到学校正式开学,也没有接到调动通知。桃子也觉得蹊跷,去查看调动文件,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看了两篇,没有李想的名字。她在脑子里像过筛子样过了一遍,感觉问题出在李想身上。
“你把调动的事跟谁说了。”她打电话给李想。
“没……没说啊!”李想抓着头,在想。
“我就不信你没跟别人说过。”桃子声音提高了三度。
“真没有啊……噢……我跟校长提起过。”
“你怎么说的,快说。”桃子感觉李想泄密是板上钉钉了。
“他……他让我……去买卖扫把……我说……我要调了……让他安排……”他说话的声调像用嘴在外吐枣核。
“不要说了,我知道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人家让你买几把扫把,是会把你腰挣断了还是什么的!不想和你这么没脑子的人说事。”桃子气得挂了电话。
此时,李想也想明白了,是校长使的绊脚。
桃子通过内部人员打听了,说当时李想把要调动的事跟校长说了,校长一个电话打到教育局,说,如果你们把李想调了,他这个校长是干不了了。教育局的领导就问,调一个李想,跟你干不干校长有什么相干。他就说了,李想在学校是出纳兼总务,要是你们把他给调了,要我去找这样的人,学校在着的都是教书匠,哪有管钱的这样的人才……教育局的领导听着听着,这听出门道了,说了,你就放宽心干好校长吧,我听取你的合理化意见,李想不调了……
这件事,狠狠地教育了李想。一年过去了,又得开始活动调动的事了。如果媳妇不帮自己,自己是没有门路的,他现在就像是关进了笼子的狮子,走出笼子的钥匙在媳妇手里,要吃肉,也得靠施舍。不过,他觉得他还有獠牙,男人的身份是他的獠牙,他还是婚姻的把持者,只要她一亮獠牙,肥肉和瘦肉都是他的。
桃和弟说着话,门打开了,李想回来了,他站在门口,打了个趔趄,才摇摇晃晃走进客厅。
看着脚是很飘了,他看桃子和弟的眼睛睁得比灯泡还大。
又一个摇晃后,他的手不知放在那,在胡乱摸世界,最终于摸到一杯冷开水,把水当酒豪情地喝了,兴奋劲又上来了,对着桃说:“我不怕你,从来不怕!嘿嘿嘿……”
弟的疑惑就爬到脸上了,心说,姐夫这是怎么了,是那天平时对姐唯命是从的姐夫吗?是那个天天把离婚挂在嘴边的人吗?
同是长着胡须的男人,他确实看不明白眼前的姐夫。一边唯唯喏喏,像姐有一个炸药包,随时会投向自己,一边又像自己手持一根铁棍,随时会把姐打死打残。
姐夫的那根铁棍,可能就是离婚吧,攥在他手里,紧紧的。他很有信心,坚信桃子不想离婚,也不敢,不敢离婚。
“喝多了就去睡,我可没心情听你胡扯!”桃的眼神如寒星,如利剑。
李想一楞,眼球闪了一下,脸像被打了一记耳光,落了面子,又扔下几声“嘿嘿……嘿嘿”后,进卧室睡觉去了。
“你们真要离婚?”
“凭什么,就凭我生了个女孩?我做错什么了?”桃说得很硬气。他用眼光看着弟,像对弟说,她不会离婚的,又像是在感激这个弟弟,弟弟会给她一根救命稻草。
第二天一早,李想惺忪着眼走出卧室时,桃子已背上包准备出门。
正要出门,她犹豫了下,说:“你调动的事已教育局已研究了,你抓紧办手续吧!”
李想一愣,不敢看桃子的眼睛:“谢谢你了!”
“不要谢我,你以后少出去玩点就得了……”说完,出门了,不重的关门声,把李想吓得脸上的肌肉一缩。
媳妇走了,李想还在想,这是我的媳妇吗?还是那个曾经,性子柔柔辫子长长的桃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