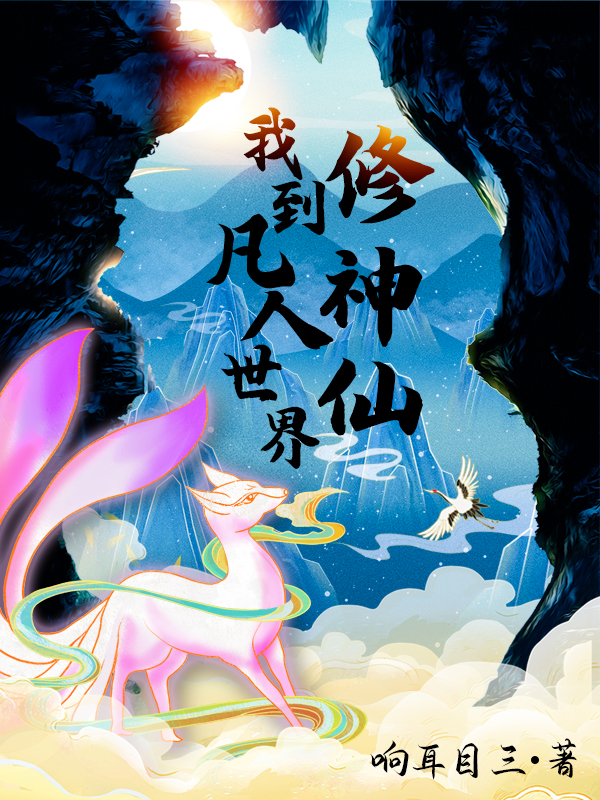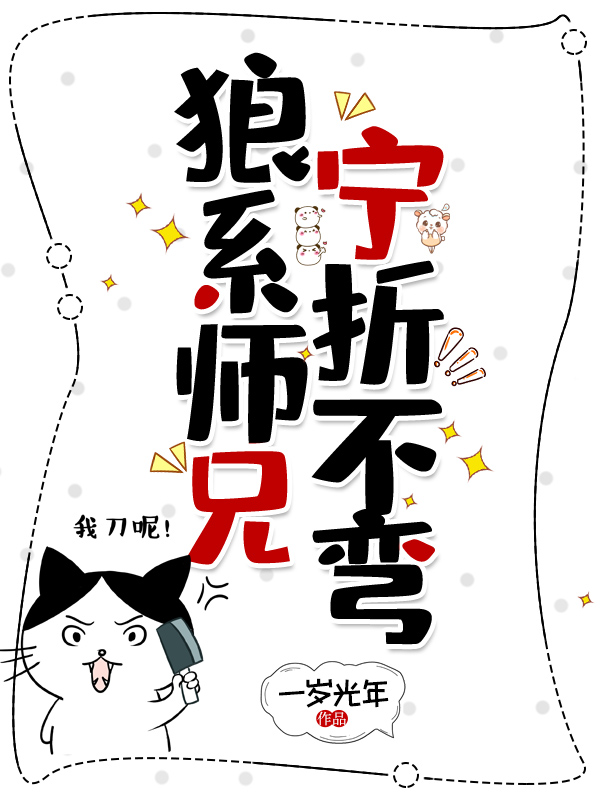桃子家的正房,和寨子里大多数人家一样,是土抬梁,土抬梁故名死义,就是土几抬横梁。房子有三隔,中间部分是柱子抬着梁,两边土几抬。中间有个大屋檐,前边有小屋檐,在小屋檐的状檐方后边,桃子的爹别着一把长刀。
长刀是当着桃子的妈、桃子和桃子的妹及弟别上去的,当时,桃子有十一岁,妹九岁,弟光明有四岁。
那天,桃子的爹拿出长刀,在磨石上磨得“沙沙沙”响,刀子磨得亮得闪着寒光时,对着自己的婆娘和孩子大声喝道:“明晚上我回来,就把你们娘几个剁掉……”
第二天开始,每天都变成明天,刀子就在状檐方下别着,每天都会被杀死,每天都充满恐惧。弟和妹很小,不懂事,晚上都很快睡着了,桃子和妈不敢睡,怕一睡下去,就没命了。
每一晚,桃子在床边坐着睁着眼熬着。风在窗外哭嚎,还有受害鸟儿声音。落叶被风吹起扑打在窗子的塑料上,沙沙作响。妈则每晚都用麻皮纺着线,或用麻线缝千层底,她把恐惧缝进黑白不分的鞋底,完成一双双温暖孩子的鞋子。
窗外有知了叫了,“吱吱——吱吱——”的声音划破夜的黑,桃就想做一只小小的知了,有一对薄薄的翅膀,想飞到清流潺潺溪水边,就飞到溪流边;想睡觉,就找个没有风吹、没有太阳晒的树洞,美美地睡上一觉。做知了很好啊,不用吃很多,吸点树叶上的水珠,再吃点树的汁液就行……
天亮了,太阳的光挣脱了大山,从窗户印射进来。
桃连脸不洗就去上学了。
学校本是安全的,可桃子担心着,自己来上学了,回去就见不到妈了,妈被爹用长刀剁了。实在熬不住了,她就会在课桌上睡着,老师也不叫醒她,因为老师都清楚她家的状况……
她在教室睡觉,不会做梦,不做梦就暂时忘记了那把爹别在状檐方下的长刀。
桃子放学,进院子。
不见妈,弟也见,妹和妈也不见。
“妈,妈……光明……光明……”
没人应。
平时,进家门第一眼就会见着弟光明,妈大多数的时间在地里。
突然,她看到了台子的石头上有血。
“血,啊!妈……妈,光明……”
声音除了把鸡吓得躲进柴垛,没有任何人应。
一种不详之感弥漫了到她的全身。
“妈……妈……呜呜……呜呜……”她瘫坐在地上哭起来,肩膀颤抖着。
……
“桃,回来了……”
“姐……姐……”妹和弟叫唤着。
她把头抬起来,妈、妹和弟神奇地站在她面前。
她站起来,飞奔着跑向妈。
妈手里抬着盆,盆里有一只鸡,妈一让,她扑了个空。
她又扑向弟,跪在地上,抱着弟,又“呜呜”哭泣起来,嘴里说:“你们去哪了,吓死我了……”
桃子不知道那天过节,血是妈杀鸡洒的。她们是去献山神了。
后来,妈说那夜她半夜梦里还在哭。
爹回来是两个月零三天的晚上。
妹和弟已经睡了。
那晚上,月亮很白,白得和白天一样。
桃子听到院子里有动静,她透过蒙在窗子上的塑料布,见爹进了茅房。
从茅房出来的爹,见到院里站着个人,一瞧,是桃子,一怔。
“你站在这干嘛。”看不清脸上的怒色。
“我拿给你刀。”桃子声音里听不出恐惧,把刀抬到爹的面前。
刀闪着冷月的寒光。
“谁听你拿的?”
“……”
谁也不说话,时间在沉默中停滞了。
“小桃,你拿刀干什么?”妈从屋里出来了。
“我怕爹半夜找到摔着,把刀拿了。”
“不是你叫拿的?”爹是在问桃的妈,是指责。
“把刀放了,桃。”妈只对桃说。她不想说不是她让桃拿的,说,男人也不会信。
“爹,你的刀。”桃上前一步。
“你这娃!……”爹接了,手一甩,“哐当”一声,刀落到了柴垛旁。
又嚷道:“你们信不信我也把你们一块扔了……以后不要再提刀的事……”
至此,桃再也没有见过那把刀,爹也没提过。
桃子也不知道她爹有没有寻过刀,当然,他是找不到的,半夜,她悄悄起床,把刀扔进茅坑里了。
那丑恶的东西,它应永远在茅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