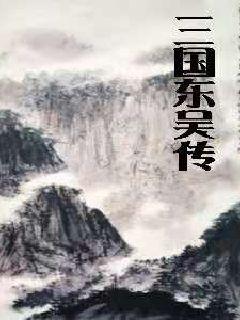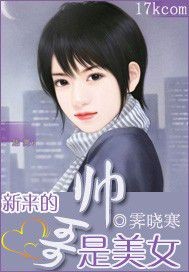第一章
纷纷扬扬的雪,下了一夜。
泥泞的路面,已看不见任何轮廓。积水的地方,踩一脚,咔嚓作响。山里一贯冷得早,但今年的雪比往年来得更早。刚过小寒,雪花就如棉絮般,一阵紧似一阵,铺天盖地,下了一层又一层。
雪地里,几行马蹄印上撒下新落的雪花,但依旧清晰可鉴。三两处暗红的血迹在雪中洇开,在明晃得让人睁不开眼的雪地里更加突兀、刺眼。一匹棕色的马,喘着粗气,在雪里孤独地前行。本该骑马的人此刻趴在马背上,身体僵硬,早已没了气息。
疲惫的马记得路,在弯曲的山谷里并未迷失方向。峡谷陡然收拢,越来越窄。最窄处,马背上的人几乎就要蹭到岩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过了隘口,地形又变得平坦开阔,一个方圆数十公里的坝子延展开来,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势。坝子另一头,地势逐级抬高。一排建筑依山而建,随地势逐渐升高,错落有致。疲惫的马在雪里吐了一口气,一声嘶鸣,打破了寂静的雪原。远处,有狗吠传来。
“启禀大王,我们派往朝廷的特使已返回,但不幸身亡。”正堂大厅正中央,一位老者须发斑白,面容威仪。本来身子陷进白虎皮大椅中的他,在屋里两侧炭火的作用下,略有困意,左手支着身子。
“怎么回事?”老者面容失色。
“这是我们在信使身上发现的手书。”下人双手呈上被卷起来、染成猩红色的信。
来意知悉,无需再议。
“这是谁干的?混账东西!”老者气得双手发抖,“把头人叫来。”
“是”。
老者把手里的信揉成一团丢进了面前的火盆,在台阶上来回走着。他座椅正后方墙上凸出的白虎头,一双突出的大眼瞪着他。
外面起风了 ,风雪也更大了。风刮得大厅外台阶两旁的三角形旗帜猎猎作响。黑边暗红色的旗子上,用黑线绣着大大的“田”字。
这是土司王田作义的府邸。田家在这一带生活数百年了,当上土司王却是30多年前的事儿。先王田洪铸历经七次苦战,打败了另几家土司,奠定了基业。现在归附于田家的主要有三大部落:以陈黑旺为头领的阳谷陈家、以达日耀为头领的万人谷达家、以黑藤里各木为首领的冥河黑藤部落。不过,黑藤部落位置偏远,且要蹚过令不少人谈之色变的冥河,归顺更多是名义上的。
脚下这块名为龙骨坪的地方,就是先王田洪铸从谭姓土司手中夺过来的。大地深处,淌着族人的血,埋着他们的骨。“你要守好家业,万万提防谭铁虎,他真的是虎狼之心。儿切记!”先王在榻上硬生生挤出这几句话,断了气。
回首间言犹在耳,田作义感觉一切恍若昨天。
没多久,从大门外走来两个身材结实的汉子。进来后扑通跪倒在地:“左头人冷青、右头人阿以柯拜见大王。”田作义挥挥手让他们起来。
“信使的死肯定和谭家脱不了干系,这个仇必须报,不能让弟兄白死!”冷青人如其名,身高六尺有余,面色铁青,瘦削的脸上线条分明,此刻他攥紧拳头、咬牙切齿。
“依我看,这倒不像是谭家的做法,谭家惯长用箭和长刀。 我进来查看了伤口,不像是刀砍所致,更像是近身用短剑刺的。再说,我派人送信使出了谭家地界。从这两点看,估计不是谭家,应该另有其人,不排除是朝廷的人干的。”右头人相对消瘦,看上去更精干,深陷的眼窝子里,眼神凌厉似刀。
“如此说来,右头人分析更有理。”土司王田作义拧紧眉头,“信使也是你们精心培育和挑选的,不至于不堪一击。但我们跟朝廷从没结下过梁子,何况朝廷眼下正需要用人。”田作义坐进椅子深处,随之一阵猛烈咳嗽,他用左手紧捂紧心口。
“大王,您身子虚,先回房歇会儿,我们跟大公子商量商量,找个解决办法。”
“你们去吧。”土司王示意左右头人退下。
帝国黄昏,适逢乱世。元末明初,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遍地开花。东南有朱元璋、张士诚,北边有小明王,还有徐寿辉等人的势力。一个破碎的王朝,在寿终正寝、轰然倒地前,势必有巨大的动静。不满者、嗜权者都在虎视眈眈、磨刀霍霍。
元朝大将帖也妥木儿带着元哀帝旨意,带着一支精锐力量,从漠北南下,几经周折辗转直至属地。沿途都有一股股力量加入。在四川亲元势力的拥护下,帖也妥木儿驻扎在四川行省东侧一线,打算同正在河南、山西等中部一带的元军汇合,形成犄角,假以时机向东出击,剿灭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在东南的有生力量。
作为元哀帝的侄子,帖也妥木儿是远在漠北草原深处的蒙古王手里尚能打出的最好一张牌。烽火四起,元哀帝内心一如帐篷外半个多世纪不遇的酷寒天气。这几天,朝廷内部也暗流涌动,一些过去强压的矛盾此刻像火山般喷薄而出,窥伺和杀戮隐藏在王宫阴暗的角落,一些人在黑夜里游走,蠢蠢欲动。元哀帝心如死灰,寄望帖也妥木儿能从南方为帝国带来好消息。
时间倒回半个多月前,夔州府将军营。
帖也妥木儿头戴黑色尖顶头盔,盔顶铜管插有一缕红色缨饰,头盔左右为铜吹返,整个头盔覆以牦牛尾,身上的盔甲泛着寒光。将军脸上棱角分明,端坐于大帐正中。如果不是受命平叛,此刻他应该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王府饮酒作乐,醉倒美人怀。然而此刻,他英气袭人的脸上现出些许疲惫,甚至带着一副厌倦感,一丝嘲讽的气息挂在脸上。
大厅正中立着一人,到访者正是土司王谭铁虎的军师义彧。“我们掌握了确凿消息,田家和朱元璋叛军暗中勾结,正谋划联合进攻朝廷部队。田家妄图趁浑水摸鱼,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将军不得不防。”义彧说,“过去上百年来,谭家都臣服朝廷,忠诚之心,日月可鉴。今铲除逆贼,还安于民,我们大王和谭家上下愿赴汤蹈火,绝不推辞。”
义彧从怀里掏出一个卷轴呈送将军,“这是田家和朱贼的联合作战图,我方眼线亲眼看见并描摹下来,冒死送出,望将军明鉴,务必先下手为强。”
帖也妥木儿扫了一眼所谓的“作战图”,嘲讽之情稍有收敛。“你长途奔波,想必辛苦,先下去歇着,这个我自会处理。明天早上有人答复你。”
义彧匆匆退下,琢磨不透将军的心思。
一轮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天上,却没有温度。冰封的世界,一切都泛着寒意。
“将军答应了你们的请求,条件是一个月内必须先选一千勇士充实到帐下。待到将军进一步巩固大本营后,再向东征讨乱贼,谭家须全力配合,到时候谭铁虎带着人马跟随将军出击。重新平定天下后,你们土司有大功,我们如实禀报圣上,他定会重赏,这可是壮大田家的大好机会。”来人告诉义彧,“至于田家主要叛将,将军说,你们相机予以剿杀,但不能滥杀无辜,不然将军也饶不了。”
收到答复的义彧,内心复杂。他当即策马东去,赶着向谭王复命。
运气不逮,田作义派出的信使,还是晚了几天。信中,田家继续表明自己对朝廷的不二之心。田作义盘算的是,在各方实力角斗尚未清朗之前,最好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在被逼到死角前,同各方都保持友好关系,也保持一定距离,保存实力,坚壁清野,必要时再投靠强者。
只是,他没料到,砍向田家的屠刀会落下得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