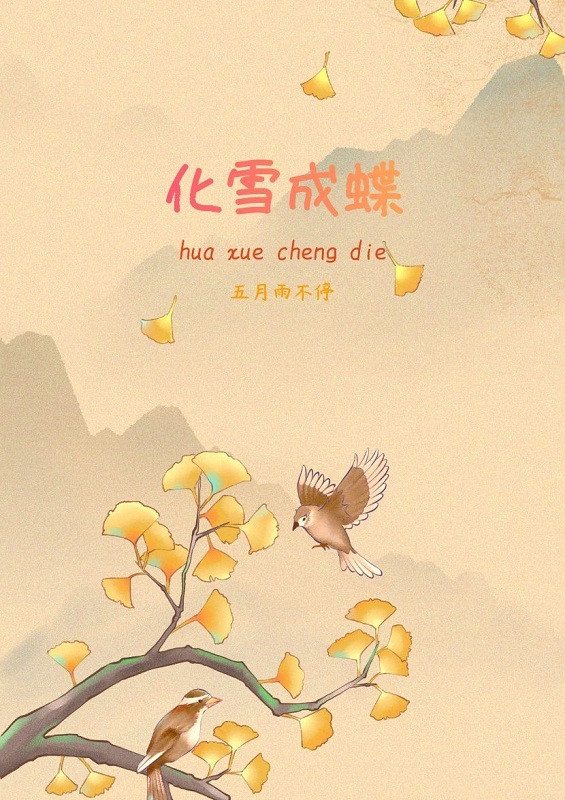城西难得下了大雨,虽出行不方便了些,众人却都快活,还是要冒雨去街坊家中,接过主人递来的干毛巾掸掸衣服,再仔细擦擦鞋边的泥泞,嘴上自进门来便没闲过,聊聊这雨多畅快,再谈谈这家事多恼人。
雨大,戏园子便歇一天,听不见平日里的热闹气,终究是有些无聊了。
孟爷孟午彦年轻时身子受了累,再加之常年的痛风,如今上了年纪便经不起这无常的天气,让下人热了炕倚着歇息,嘴中仍是哼着小曲。孟明瑛和姐姐孟言真倒是看了不少洋书,也学人家贵族的姿态,两人合了一张桌子望雨而叹。
孟氏这一代就有两个女儿,年长的孟言真本名孟宛玉,早于前年拜在本家门下,而幼的孟明瑛本名孟宛玦,也于去年拜在了周氏门下。孟言真声音脆亮,为人也敞亮大方,又是个会照顾人的,大家戏称其为“大师姐”。而孟明瑛正相反,眸含秋水,更爱低吟浅唱,人也文静,柔柔弱弱又细腻敏感。孟言真习惯于强势,而孟明瑛习惯于依附,如此,两人没闹过什么矛盾。
王娘子王昭华早过了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对美仍有执念,每日必在梳妆台前打理几个时辰才罢。被别人戏称“王母娘娘”的她眼角蔓延出的细纹让人心生敬畏,她起身时身姿绰约,款款迈步间是戏曲予她的气质如兰。
偏房内,王熙苑正帮着二哥王元彬收拾东西,大哥王言瑾也在一旁帮忙,但并不插话。
“二哥,今日雨大路滑,何故急着走呢?”王熙苑刚年过十五,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
“小妹啊,二哥急着去交货呢,可耽搁不得。”王元彬眯眼笑,笑时左脸的疤痕便皱在了一起。他腾出搬东西的手,很是宠溺的捏了捏王熙苑的鼻子。
王熙苑顺势抱住王元彬,一劲的撒娇。三个哥哥中她最喜欢的就是二哥。大哥严肃沉稳,总忙于练功,三哥王元宇终究不是自己的亲哥哥,多少有些疏远。
王氏目前只有长子王元森正式从了戏曲,拜在孟氏门下,赐名王言瑾,是孟言真的大师兄。二子王元彬对戏曲只有欣赏而不愿去学,他从小精通算数,王昭华也没将继承家业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便任其专心他事,如今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要说最受宠爱的当是王熙苑,生来便有哥哥疼,父母也是极为小心呵护的。小丫头从小就耳闻目染学了不少曲子,又承了王昭华的天赋,平日说话都带着戏韵,只是王昭华一直都未松口究竟让不让她蹚戏院这水。许是自己在这行业的苦头尝尽了,便舍不得女儿受此一难吧,众说纷纭。王昭华的小姑王梦莺三年前因病去世了,临终时要王昭华承诺养育其独子,故而王昭华又多出了一个三儿子王元宇,性子孤僻怪异,倒也不会惹是生非,如今在邻近的镇子中任一女子高中的教书先生,鲜少回家。
周爷周谦民家中放了许多古玩旧物,众人都戏称其“爱古玩甚过戏曲”,虽没去过几个地方,却欲盛下整个江山。他是对儿子极抱期望的,而那周连礼也是争气的,本身条件就不差,又舍得下苦功,只是如今还未拜师,众人闲谈时不免提起,或猜孟氏送来了一个姑娘,这边也要送去一个儿子,或说周谦民等着周连礼将自家发扬光大,会让周连礼拜在自家。而周谦民对女儿就不太上心了,名叫周简乐,如今也十七了。
秦府今日不免闹腾,那秦公子秦旋宵昨夜至今未归,虽已属正常,秦爷秦永和也不免大怒,骂着混账东西,回来要打断他的腿,可下人们心里都明白,秦永和是不忍心的,只是说着出出气,摆弄一下家主之威罢了。秦夫人身虚体弱,生秦旋宵时便大出血走了,秦永和念在旧时情谊并未再觅新欢,故秦氏这一代就秦旋宵这一棵独苗,生来便受尽宠爱,不让人省心,好热闹,爱卖弄。
此时他正与朋友约在酒楼,伴雨而谈,这朋友不是别人,也是秦氏门下弟子,名叫吴和均,是个爽朗豪气,重情重义之人。这人好酒,便没拒绝秦公子的邀约,热酒一进肚,全然忘了上次师父一顿劈头盖脸的骂。两人在酒楼最高层,远处之景尽收眼底,看到一马车在街上快步穿过,丝毫未受雨的影响,正是王元彬在赶着去送货。
“王家二公子还真是勤快,这种天气也没闲着,”两人便顺着王氏聊了下去。“嘿,秦公子可知王娘子的小女王熙苑?”吴和均提了一嘴,也是想闹闹秦旋宵。秦旋宵自诩风流,有不少女子追随,人也心高气傲,竟与兄弟说那王氏也欲收他做女婿,大家都知道王氏多宝贝那女儿,有多少人至今未见过她一面。秦旋宵当时摆了众人一道就招摇自得回家了,不承想次日王言瑾和王元彬就找上了门。此事最终是以秦永和好不容易挥出的一棍和秦旋宵半分假装的惨象结束的,确是丢尽了脸。
这事吴和均自然知道,就是知道才要故意提及的,那秦旋宵果真变了脸色。那把戏他玩了许久,却从未遇到过王氏这么认真的,非要讨个说法,最可气那王元彬,还要父亲将他杖责三十才肯罢休,幸亏那王言瑾明事理,要了个口头的道歉便让秦氏自行处理了。
“王氏对那女儿可宠的很,娇养在深阁,谁能见到?或是这女儿见不得人吧。”秦旋宵戏谑道,他可不是大度的主,至今还耿耿于怀呢。
聊得正欢,吴和均想起什么,便放下酒杯,“公子,你与师父可商讨过拜师一事了?”秦旋宵已在自家戏院串演过几次,却始终还没正式拜师。“商讨什么啊,老爷子一说话就和我急。”秦旋宵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他虽没心没肺,却也早已在为自己做打算,如今,他更愿去周氏门下。可秦永和不觉得周氏合适,他总觉得周谦民这人城府太深,不好对付。
秦旋宵只顾着谈乐饮酒,不料秦永和刚下了大决定,此刻正坐在摇椅上哼曲喝茶呢。
这雨终究不敌城西的旱意,次日清晨便停了,焦灼的太阳休整了一日,此时也卯足了劲晒着。虽是早就修了大路,大家还是惯于走土路,雨水一来和了泥,在各处彰显着足迹。今日大伙的步子都急了些,不似往常悠悠的。这是去哪儿啊?若有外地人问起,大多人定是头都不回地答道,看戏去啊!
老人们念一个“旧”字,不大接受新鲜的,可各班班主自上了年纪后就不爱再出场折腾了,故而戏院鲜少能看见几个上了年纪的。可今日不同往昔,王熙苑在自家戏院认出了好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好像此时腿脚和听力都好了不少。
今日一大早王昭华就带她到戏院且亲自细细的打扮上了,看出来扮的是青衣,那气势似是要比过一世风华。王熙苑在一旁虽是疑惑却不敢发问,她或多或少是怕母亲的。“苑儿,你看母亲这姿态与年轻时相比有差吗?”王熙苑摇头是很实诚的,可心中也愈加疑惑。
开了场,母亲也上了台,王熙苑躲在后台悄悄探出了头,台下的热情将她吹得头晕。她四处望着,见好些个年轻女子心思不在听戏,脸颊上还带着红晕,几个簇在一起,朝着一个方向时不时谈笑。顺着那不时撇过去的目光,她看到了一位高而偏瘦的男子,不穿洋衣却穿着长褂,手中把玩着一折扇,于一开一合间露出其上墨宝——风华绝代。
她常年在闺阁,不认得这男子,却识得他身旁的秦永和,便理所当然地想到了秦公子秦旋宵,不免脸红。她不禁又往秦旋宵那边打量了几眼,这才认清他的模样。城西海拔高,晒得众人都面色黧黑或是发黄,但他不同,肤色白皙却并不死板。他很瘦,脸颊上也没有多少肉,使得轮廓清晰的显了出来,面部线条在下颔处突变锋利有力,在透着红润的薄唇下汇合。他双眸清亮,好像盛着一泓清泉,平静的波动着。这相貌,纵是女子也要羡慕几分的。
她却看不出那平静的双眸下是即将爆发的烈焰。秦旋宵此刻实在是烦躁不已,却不好当着众人发作。他昨夜才回到家,本想着先溜回房间,明日再去想办法讨好老爷子,却不料,他的房间已燃着灯,秦永和正候着他呢。
“父亲……”他虽是平日里和秦永和总拧着干,但在这种时候他还是忌惮的。
“宵儿,今日出去可累了?”秦永和说这句话时已藏不住脸上的笑意。
秦旋宵不敢贸然答应,站在秦永和面前微弓着腰,头垂着,一副温顺乖巧的模样。而秦永和见他这个样子倒觉得好笑,他咳了几声以掩饰笑意,想尽量严肃些。
“宵儿,你虽逍遥,但一定是有打算的对吗?”
秦旋宵可算明白了今日父亲特地等他的用意了,而且看来他已有决定。不过秦旋宵终究是对自己和父亲高估了些,以为父亲定与他心意相通,便作揖恭敬地答道,“一切还由父亲定夺。”
秦永和很吃这一套,还满意的晃了晃头。
“那你明日便随我去絮兰园认认师父吧。”
树梢上沉睡的蝉此刻也惊醒了,烦躁地叫了起来,直到天明才缓下。
周连礼也未拜师呢,但周谦民气定神闲,成日守着他的宝贝,也没提过这事。而他不提,周连理也就不好提,否则就是着急去孝敬别家了。今日周谦民带着周连礼一大早便出门了,说是去钱老板那里淘淘宝贝。周连礼的母亲杨氏是极守本分的,总觉得和钱可俞走得太近不好,那钱老板是什么人呐?是从戏园子里逐出去的人啊,犯得可是欺师灭祖之罪。可周谦民嫌杨氏麻烦,他说交易换物不换心。
钱可俞与周谦民同辈,与孟氏同门而出,原叫钱午城,被逐后开了当铺,命名为云城斋。有许多人看不惯他,路过当铺是都不带瞥一眼的。可钱可俞有那通天的本领,硬是两年时间就把生意做大了,这就不免有人赶着巴结了。
“周爷”,早闻了风声,钱可俞已然在当铺门口候着了。周连礼跟在父亲后面向钱可俞作揖,神情却没有多少恭敬。他虽是总陪着父亲来云城斋,却也不十分喜欢钱可俞。
当铺内蛮热闹,见周谦民进来纷纷问候,顺带着夸一句周连礼。
钱可俞带着周氏父子一直上到二楼深处一厢房,仔细吩咐了下人守在门口后便从暗屉中取出一小巧的锦盒。“周爷好福气,正赶上我这儿昨日刚进一宝贝,您肯定喜欢 !”说罢,打开锦盒,赫然盛着一枚玉玦。
周谦民素来爱好大气的玩意儿,可见这玉玦却不胜欢喜,小心放入手中,细细把玩。看着周谦民这副模样,钱可俞心中暗喜,这玉玦做工精良,可不是小数目,但周谦民定然不愿喜爱之物落入他人手中,他很清楚这点,已然在心中盘算要价了。
周连礼这时开口了,“这玉玦的价钱怕不是个小数目吧,钱老板。”而周谦民略带责备的撇了周连礼一眼,“这玉玦的价值能用金钱来衡量吗?”转而向钱可俞,“钱老板明日到我府上取便是了”。
次日,周谦民神清气爽地坐在大厅中品茶,候着云城斋的伙计送玉来。
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后,周谦民连忙起身亲自去迎接,进来的却是孟午彦门下弟子陈言首,他带着一顶锦缎圆帽,喜气洋洋地。
“周爷!”周谦民正疑惑陈彦首的来意,只见他从袖子中拿出那手帕包着的锦盒,周谦民才快快请了陈言首到大厅同坐。
必要的问候是少不了的,“孟爷还好啊?”“托您的福,挺好的。您老人家还是一如既往的身子硬朗啊!”陈言首顿了顿,“我正巧去云城斋办事,就顺手帮钱老板带了物什来。”周谦民接下宝贝,神情也缓和了些,但眼中的戒备丝毫不少,“劳烦你了,报酬我会转日亲自送去的。”他眯了眯眼,似是要看透陈言首的心思。众人皆知,钱可俞和孟午彦可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这陈言首能毫无避讳?莫不是两人背地里有什么交易?“孟爷也托了你去取东西?”那陈言首没什么头脑,一股脑地就全说了。
“哪可能啊!我师父发过毒誓的,此生绝不再见钱老板,就是到了阴间也要绕道走呢!我这是为了点私事。”“什么私事?”周谦民小心翼翼的继续发问。
原来这陈言首的父亲与钱可俞是异姓兄弟,即陈言首与钱可俞以叔侄相称。前日陈言首的父亲病逝了,他一时无处投靠,全由钱可俞接济度日。
周谦民听着愈发疑惑,“怎么不去投靠孟爷?”只见陈言首脸色一阵白一阵红,支支吾吾的半天开不了口。其实他已经有几个月未见师父了,师父不愿见他,他也不敢见。“周小姐应该快回家了吧?”他这话题转的生硬,周谦民自然发觉。
之后的谈话两人都兴致缺缺,有一茬没一搭的,几句后陈言首就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