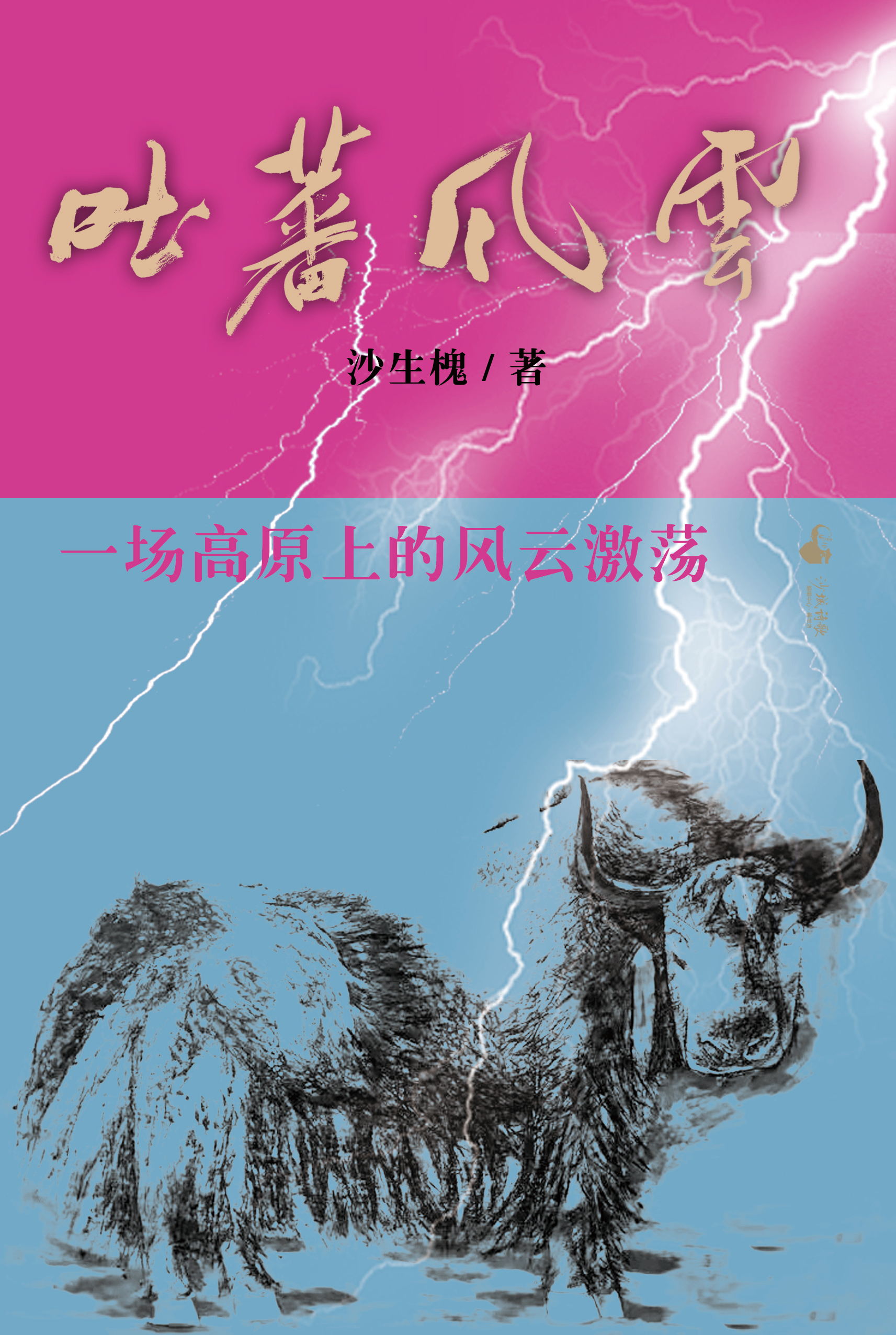父亲经常这样说:学好手艺能防身,单怕艺不真,手艺要不真,那就防不住身。这话时常在我耳边回响。我怀疑父亲在我不懂事的时候也会对哥哥们说。哥哥们成人以后多以技艺生活。可惜,年少无知的我怎能体会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当然也可能是生活阅历的不足。父亲有点重男轻女。
父亲生于一九二六年,他自己多说是民国十四年,很有中国特色的记年味道。他读书很少,只有半年私塾,他很自信自己的医术和知识,当然,他嘴上并没有这样说。他有时也很自信自己的早熟,常言,八岁头上学赶集,十三头上学种田。我常想,农村孩子大抵都如此,即使当时的地主阶级也是勤俭持家的。
至于父亲为什么学医,应该和爷爷的引导有关系,真佩服爷爷的洞察能力,爷爷把父亲引导到医学的道路上来是绝对正确的。爷爷有二个儿子,俺还有一个老叔叫李清文的,很会讲故事,如果有人推广,绝对能靠评书混饭吃。当时,俺的家庭并不穷。
爷爷的死亡令人痛心疾首。
爷爷喜欢俭朴和低调,过年新染的大褂子,一定要打上几个补丁才肯穿在身上,干起活来,中午不回来吃饭,头顶湿毛巾在毒辣的太阳下锄草。早起去干活,一手拎着铜茶吊子,瓷碗扣在壶盖上,一手扶着肩上的锄头,到了地头上,用吊子盛满泥河边的"井把凉"水,以备解渴之用。能不请短工就不请短工,中午,奶奶扭着小脚给爷爷送饭,在爷爷吃饭的间隙,奶奶也会帮助锄草。
"井把凉”是河边从沙缝中渗出的地下水,这种渗水泉眼很小,渗出的水并不多。村民就在旁边挖一个一米长宽的坑用以贮存水,想喝的时候可以挑回去,也有调皮的小孩子直接用手捧起来喝,我就这么干过。泉水甘甜而且清凉,尤其在夏天,真是消暑佳品。
我也喝农夫山泉,我更喜欢家乡的"井把凉”
奶奶是小脚,这影响了人的生活和劳动。
裹小脚需要把脚的四趾对折到脚底,只留大脚趾不弯曲,从小女孩五、六岁开始缠足,让脚在发育生长的过程中形成畸形。据说此陋习起于北宋,灭于民初。成形的小脚俗称"三寸金莲”。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
母亲是胆小的,她在五、六岁的时候是可以不裹脚的,但她还是缠足了。是惯性的使然还是对未来的恐惧,应该兼而有之。俺老婶就没裹脚,宅子西头古大奶也没有裹。
古大奶是一个猛人,听说,她丈夫曾经被土匪绑过票,她直闯匪窝,把胸膛拍的山响,口吐狂言:"朝这打,放了古石匠。"
由于走大匪首古六的关系,终于放了她老公。解放后,如果有谁和古大奶骂街,那是一定要输死掉的。
其实,我老婶也不弱。
有时,在晚饭后,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常常让我帮她剪小脚上的老茧。
早些时候是用菜籽油作燃料,能用煤油作燃料也是古老中国呈现现代科技文明的微光。
装煤油的瓶子是用过的为药瓶,玻璃的,这在当时可是宝贝,物质缺乏嘛。父亲有时把这种小玻璃瓶给左邻右舍用,大多的乡邻都感激万分。我家的灯芯是用医用纱布,多数人家都用粗棉线拧成,油灯盖用废旧的薄铁皮剪成圆圆的一小块,中间钉一个小孔穿灯芯,也有用牙膏皮做灯盖的。当时的牙膏皮可是用薄薄的铁皮做的,塑料是没有的,可以想象当时的工业很不发达。
昏黄的油灯光照在土坯墙上,房间并不明亮,但感觉到很温暖。
母亲常说:“老九,剪脚钉子。”
这有让我帮忙的意思。“老九”是我的小名,我兄弟姐夫九人,我是老小,由于兄弟姐妹多,起小名就不那么慎重了,尽管我是男孩子。
“脚钉子”是我们这里对脚上老茧的俗称。
母亲的脚被汗液浸泽的发白,缠绕过的小脚形状颇似毛竹笋。弯折的四个脚趾紧帖在脚底板,由于走路压迫的缘故,象没有完全成熟的小扁豆。由于汗液不易排除,不透气,虽然母亲洗过了,但还有些异味。“三寸金莲”,俺感觉这名字并不美。
母亲以前不参加劳动,解放后,妇女能顶半边天,小脚女人也要参加劳动,但不能在水田里插秧播种,只能在干旱地里劳动。在参加劳动的这种情况之下,“脚钉子”就长得频繁。
吃过晚饭后,父亲行医看病还没有回。赤脚医生是没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的,哥哥姐姐有的已经出嫁或者分家单过,七哥八哥还在上学。那么,母亲指使我这个老幺帮忙那是顺理成章的。
咱家的针头线脑剪刀啥的都放在筐里。这种筐是用竹篾编制的,露河岸边竹子很多,就地取材。竹子可以起三层篾子,第一层是青篾,第二、第三层是黄篾,用青篾编制的筐结实耐用。咱家的这个小针线筐是用青篾编制的,小巧而且精制,还是爷爷亲手编制的,筐里常备有针线、剪刀、碎布。剪刀的刀口都磨地出现了月牙形,以前多是爷爷在磨刀石上磨,后来是父亲,我有时也装模作样地磨,父亲发现了总是不让,他说,磨剪子也是一种一技术活,小孩子不会。磨刀石产于东南的桑山县,细细的山石由古奶奶的老公古石匠打磨而成磨刀石。
这个小筐有我好多好多童年的回忆。
母亲把脚放在小板凳上,从针线筐里拿出剪刀。
“这剪刀还是你爷爷买的,你爷爷去逝十多年了。他不喜欢穿新衣服,怕人家说他有钱。”母亲对爷爷很有感情,边剪“脚钉子”边说道。俺并没有见到爷爷的面,想想都有些惋惜。
“痛吗?”我问母亲。
“不痛,剪了肉了痛,——噢,噢,”母亲痛得一叫,应该是剪到肉了。用剪刀剪脚底的老茧不容易,有时剪到肌肉也并不奇怪。
“拨一下灯芯子,”灯火有些暗淡了,母亲又吩咐我。
“哎!”我答应一声,拿起使用过的火柴棒,挑掉灯芯上的灯花,房间里又亮堂了一些。
当时,我们使用的火柴品牌是安阳火柴,打火机是没有的。
“爷爷是咋死地呢?”我很好奇的问母亲。
母亲并没有说,好象也不愿提及。
我还想进一步追问,父亲带着夜晚的凉风回来了。父亲一边把药箱放在方桌上一边说:“还没睡呢。”
“吃饭了吗?”母亲不接父亲的话茬。
"在古寨古麻子家吃的,面条子。”
俺们这里也算是渔米之乡,种植小麦的很少。父亲不喜欢吃面食。那时的赤脚医生称呼为先生,颇受人们的尊敬,走村串户看病,老乡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食物拿出来给先生吃。
父亲想帮母亲剪"脚钉子”,母亲打开了父亲的手说:"去,一一你又不爱吃面。热点晌午的米饭吧。”
"不爱吃也吃一点。时候也不早了,准备睡觉吧”
"明天还要早起干活呢,”父亲又补充了一句。
母亲起身拍打一下身上的灰尘,收拾好针线筐.吹熄了煤油灯。
农村的夜晚安静的很。
一天傍晚,临近收工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太阳了。古大奶在高处对母亲干活的地头高喊:
“喻啊——,出事了!“
母亲感到事情不简单,能让古大奶焦急地呼喊声中听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她颤着小脚,扛起锄头就往回急走。古奶奶收工前回家干什么不得而知。
母亲回到家看到的是,爷爷平躺在堂屋的地上,外穿着粗布蓝色的大褂,有补丁,头发花白,脸色灰暗,一双新布鞋穿在脚上,没有袜子,已经没有呼吸了。宋嫂、宋二嫂、古奶奶也在,他们在窃窃私语。男人们还没有回来。母亲默然找一张烧纸盖住爷爷的脸。她发现爷爷的脖子上有绳索的勒痕。又用粗白布条裹着爷爷的脚当袜子,重新又把爷爷的鞋子穿上。
“烧纸“是我们这里祭祀或上坟用的一种纸张,纸黄色,烧的纸灰极轻,易飞舞到空中。母亲如果见到飞舞到空中的纸灰多念一句:”祖先收到了。“这种烧纸在使用前先要处理一下,用纸钱梳均匀敲打在纸上,并非一张张地敲打,而是一摞摞的敲打,然后三张或几张折叠易于燃烧。”纸钱梳“是木柄的,前端有硬铁片镶的圆圈,中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铁圆圈。有一个头的,有两个头的,最多有三个头的。应该是模仿古铜钱用的。当然,现在也有人用纸币直接在烧纸上印。
母亲很茫然,不知所措,宋嫂、宋二嫂也没有建设性的建议。古大奶一锤定音,让我大姐去顺流店找我的父亲回来。这时,十七八岁的大姐,她的勇敢体现了出来。母亲给我大姐找了一个铁皮手电筒,不很光明,大姐于是趁着夜色,趟过露河往北去寻父亲。
爷爷死了。
他走的很简单。
他走之前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道。是饿死的吗,还是担心自己的苟活侵占了孙子孙女的食粮呢?也或是疾病的痛苦引起的吗?
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他去逝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现在,每当上坟的时候,看着爷爷的墓碑总有些无奈。
墓碑是后来父亲立的。二叔并没有参与。虽然很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