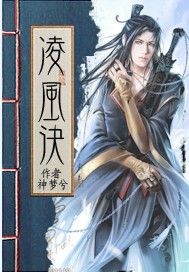既然做了个不用上班、也不用上学的“躺平”凡人,那么我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早晨睡到什么时辰完全由我决定。
但,我被打脸了。
开场是一声小男孩暴躁的尖叫,把我陡然惊醒。
我的脑子里还残存着梦境的影子碎片,心口里本就很是不畅,睡眼朦胧地看了一下墙上的挂表:6:35。.
此后,楼下的女人就开始了不停的大呼小叫,催着她儿子赶紧穿衣服、赶紧上厕所、赶紧吃早饭、赶紧收拾书包、赶紧别忘带东西,赶紧出门快上车……而她那个上小学的儿子,则是要么嘟嘟囔囔顶嘴,要么哼哼唧唧磨蹭,中间随时爆发出不可预期的大吼。
母子俩针尖对麦芒,你一句我两句,各自不甘落后地一直闹腾到七点半,随着他家防盗门“咣当”一声关上,母子俩大声互相埋怨着下楼而去,我的世界终于消停了。
我明明睡意还在,却被吵得合着眼也根本睡不着。
作为一个见识广博的老神,我自然不会同凡人计较——他们的一生不过几十年,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他们为了那许许多多的欲望和痴嗔忙忙碌碌,难免要争分夺秒,难免要争抢吵闹。何况,除了自身之外,他们还要将儿孙未来的欲望和痴嗔也扛上自己肩头,活得辛苦暴躁,在所难免。
我只是在想:这就是玄木须所说的“六楼清静点儿”?看来我确实还是得感谢他家八代祖宗,若是他当真如愿把我安排在他感觉更富有“人情味儿”的胡同里头,估计此刻我的脑袋已经炸了。
睡不着,就只能起床。
望着卫生间里的镜子,我一皱眉。
镜子擦得相当透亮,可镜子里有个头发蓬乱、脸色晦暗、双眼无神的邋遢鬼。两条胳膊有上四条三寸多长的伤口,伤口上凝着脏兮兮的血痕,身上穿着一件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红裙子,裙子上还沾着工地上的各色尘土——纵然我是个对诸般好坏色相都已无甚兴趣的老神,但能把自己作践成这样一个“人间叫花子”的腌臜德行,我觉得,我对自己还是真够狠的。
感慨之余,不由随口就掐了个净身诀,谁知,法术竟然灵了!我浑身上下立时便十分洁净。法术恢复了!
看来,昨天夜里,它只是暂时失灵了一下而已。想想这些法术被我用了这若干万年,偶有一回不大灵光,也该算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再施术消去了胳膊上的伤痕之后,我还顺手掐诀给自己换了一件样式顺眼些的棉布裙。
心里盘算着,待我梳好头发,便要将司命召来问个清楚。可伸手再要化出梳子,法术却又失灵了……
我拿起柜上的牛角梳,一边梳理长发,一边心态平和地想:法术时灵时不灵,总比一直都不灵要好。
看了看墙上,挂表显示还不到九点。
看了看沙发,黄色猫妖还没有醒来。
看了看窗外,这房子果然阳光很是充足。
房子虽不大,收拾得很是齐整,日常所需之物一应俱全。北边卧室里满铺了原木色的榻榻米,我昨晚就睡在榻榻米上,窗边还摆了茶桌蒲团,可以欣赏窗外波光粼粼的西海子。南边房间更大些,窗外也没遮没挡,楼下是一片单层平房的灰瓦屋顶。东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超薄平板电视,西墙上则是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布沙发。沙发桌上还摆着个两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盘,一个里面放着若干种水果,另一个里面则放着十几包各不相同的小零食。南北两个房间中间,夹着一个只能放下一桌两椅的小厅,桌上还放着药和外卖餐盒。小厅无窗,但与南向房间之间的隔断是半透明的玻璃砖,还算亮堂。
我不比那些凡人,既不需要忙着生,也不需要忙着死,时间就如同指尖上的风,随它吹过。
于是,我闲闲坐在北窗边,闲闲喝了两壶茶,闲闲嗑了一大包瓜子,闲闲翻了几本书。直到门铃响处,玄木须驾到。
自我打开门的那一刻起,这两室一厅的小房子里,立刻每个犄角旮旯里都盛满了导游城隍玄木须的“活色生香”。
他浑身上下裹着一团烤肉香味,热情洋溢地径直冲到餐桌前,急急放下托在左手里的纸袋,嘴里连连吸着凉气:“哎哟真够烫手的嘿!芝麻椒盐烧饼,还是刚出炉的呢,那叫一个又脆又香嘿!”扔下烫手烧饼,他这才举着右手的袋子,朝我打了个“吃货的招呼”:“神姐您了早啊,洗脸刷牙了吧?来尝尝咱这炙子烤肉,真正老字号的地道玩意儿,就着烧饼,再加上鲜酿的啤酒,绝了。”
我瞟了一眼挂表——十二点一刻,礼貌地点点头:“您了早。”
我相信玄木须不管到哪里,都是一副回到自己家的轻车熟路。
进门洗手,摆盘倒酒拿筷子,一套动作干净利落,但嘴上更利落,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他已经兴头头、乐颠颠地从啤酒的鉴赏,说到了美元升值,从京城烤肉名店的来历,说到了每晚在播的电视剧。
我抱着肩膀站在一旁,心下将拦住他的话头和拦住发狂的惊马做了个比较。在轻叹一声之后,我断然出手:“跟我说说补考流程。”
委实出乎我的意料,“话痨”玄木须对补考流程的介绍,简洁得几乎丧失人性。
“第一,不能违反人间的伦理和法律,将考题中的十条人命安然送入他们心甘情愿的生命轨道。第二,人间的24小时之内只能用三回小法术。第三,最终解释权归天庭职考司。”
他背书一样地说完这三句话之后,端详了一番我的面色,才小心翼翼地试探道:“神姐,据我看来吧,以您的实力,这都是小事儿,哪能难住您呢,您说是不是?”
我想了想,也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便点点头:“行了,那现在就把章来娣的尸首和魂魄都弄来吧,赶紧让她还魂。”
玄木须歪头嘬了一下牙花子:“她是死鬼,大白天的不能出来。”看我神色并无变化,他的话量渐渐又恢复如常,“神姐,您这长生不老的,自然是万事不着急了。今天晚上,咱肯定得加夜班了。来,兄弟我僭越敬您一杯。您瞧,我这天庭的基层也不好干,想当年我还是人的那会儿,都没干得这么没黑没白的……”
我将酒杯一推:“我从不饮酒。“
玄木须显然不信:“神姐,看您这豪情万丈,怎么可能不喝酒呢?“看我斜着眼冷冷看着他,又立马改嘴,”神姐果然是六界之中最特立独行的女上神,说一不二!佩服佩服。“
午饭结束后,玄木须十分有眼色地告辞。我看他提着装满垃圾餐盒的袋子朝外走,赶紧嘱咐一句:“晚上所有‘特地道’的吃食,全免。“
我又闲闲坐在北窗边,闲闲喝了两壶茶,闲闲嗑了一大包瓜子,闲闲翻了几本书,闲闲等到天黑。
其间,趁着烧水沏茶的空当,我闲闲地想:人间有句名言,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能有起死回生的机会,那些死鬼应该求之不得才对,还会有不“心甘情愿”的?用这种没水准的东西来做考题,可见就是司命在工作时间摸鱼。
可谁能想到,我又一回被打了脸。
章来娣还当真就是个不肯起死回生的死鬼!
午夜,我盘腿坐在沙发上,双手捧头,看着地上的两个章来娣——哭哭啼啼坐着的,是章来娣的魂魄;安安静静躺着的,是章来娣的肉身。
玄木须倚墙站着,两手插在裤袋里,仍然颇有耐心地劝降:“……小章,你能有起死回生的机会,那可都是这位神仙看你可怜,好心帮你,只要人活着,万事都有希望不是?“
章来娣一直低着头,抽鼻子抹眼泪,嘴里反复嘟囔:“我做人太失败了,我不想活了,我想变成厉鬼掐死胡清北……”
这三句话,她已经来来回回说了一千二百六十七遍,现在是一千二百六十八遍……我终于忍无可忍:“还有完没完?就你这个德行,做鬼你也是个糊涂鬼。”
章来娣抬头来看了我一眼,随即两手捂脸,呜呜大哭:“我做人太失败了,我不想活了,我想变成厉鬼掐死胡清北……”
我——想——抽——人!
“我出去透口气,今晚上就到这儿吧。”我缓缓站起身,按着太阳穴朝门外走,“老玄,这烂摊子交给你收拾。”
玄木须的一双小眼睛一直在偷偷瞄着我的脸色,一边答应着,一边很是识趣地在我开门之前解开了封住这个单元房的结界。
我心中暗骂:“木须你妹!你要是昨天也这么设下这一道结界,我至于一大早就被楼下吵醒吗?”
我搞不定凡人这些破事,我要趁着还有今天的三回法术,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