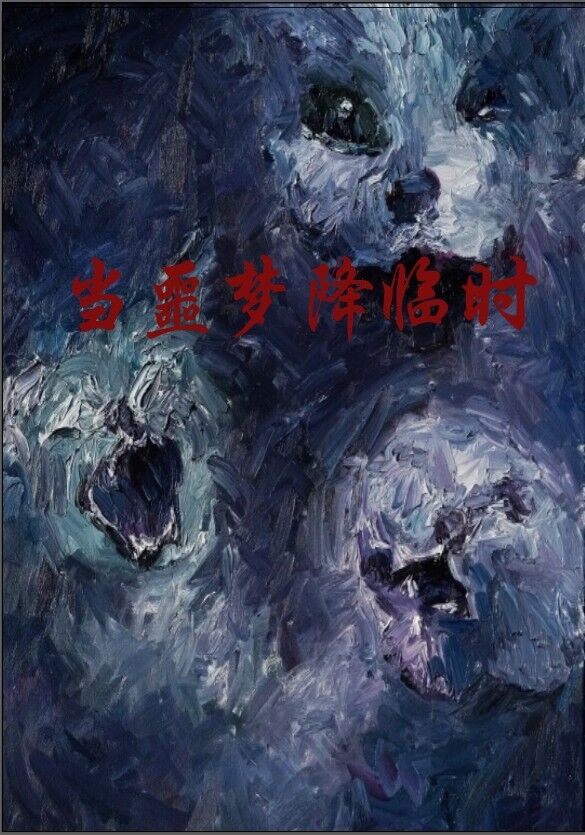隔日一早,常梦的死讯便传到了大林帝都,朝堂之上众臣举辩无常,无一不将矛头指向刚从令阳回京的左郎。
陛下万般无奈,只能传昭左郎府邸…
朝堂辩论本就不是左郎的强项,入宫前尤中客要来了涟漪楼所得的皇文帛书,提起墨笔在尾段,写了一句话,并且说道:“大人不妨就承认下来,若朝堂无人替您争辩,老太后看过此后,定会保大人无恙。”
尤中客送上帛书继续说道:“大人本就是奉太后之令密查何氏遗孤,余国偷调粮草辎重之事太后根本就不会在乎,我们只不过是顺手解决掉了常梦,谁又知道,东门刺杀是陛下的决定。您只要让众人知道,左郎早已是太后麾下,其二是让太后感觉,为了此人常梦必死无疑。不管何今安是什么人,只要他姓何…”
尤中客自然不会告诉左郎,他早已安排了宫中禁军。若大人有恙,他会让庙堂大乱。
有了能未卜先知的尤中客谋划,左郎便再无顾及,招呼车驾,动身出动。
宫城外有统领二十万禁军的将军司空大山,他见左郎之驾远远过来,抬手行了边城军礼,却又害怕将军谩罪,转而变成了宫廷礼仪。
待马车近些,司空大山眼睛有神,也有失落,心中万般感慨,到头来,只是欠身说了句:“左大人。”
宫道的禁军内卫听闻将军面王,早早的磨亮了战剑。左郎从他们中间漫步穿过,竟无奈地沉着头。
他们的眸子,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直追随的人。
司空大山靠近左郎默默说道:“将军,请您抬起头来,让他们看看您。”
左郎抬起头,步伐紧了许多,他不敢再去看这些熟悉的庞子…
“若将军公堂受阻,我等为将军厮杀…”司空大山说。
“这是先帝对你我的信任,只要边城军守着宫城,我便不会有事。”左郎回道“这个天下只能是姓李。”
“我只认左字旗,不识李姓王。”
“五爪龙旗下没有逆臣叛将。”
林国的百官公堂,老太后已经执掌了十一年。自先帝逝世,霑庆皇帝继位,何皇后便奉先帝遗诏摄政大权,直到霑庆帝加冠。
如今霑庆皇帝自然是过了加冠的年纪,却迟迟不举行大典,奈何何氏一族在老太后的庇护下加官进爵,百官也是敢怒不敢言。
朝堂之上,太后高座与陛下之左,何太后虽说上来年纪,可也是风韵犹存,体态万千,举动之间显出一股傲尊之气。
比起霑庆帝,却是略输一筹。他端正驾座,不怒自威,两眸之间显帝王之相,胸中更有大志。
中殿内争论不休,左郎进殿后,小小地太常节律郎为了博取高官的眼眸,第一个展露了锋芒:“左郎大人,朝堂之上穿着怎能如此随意!”
除了告病的丞相赖桴源,大殿上百官集齐。左郎看着丞相位无人,想着最难的钉子不在。
便不理会节律郎,就是一个眼神也懒得搭理他,行大礼说道:“臣参见皇太后,陛下!”
霑庆帝见左郎眸面不改色,他知道宫城之军,唯有他令,方可动亦。众下之文人,皆是匹夫之勇,他不动声色,自然是运筹帷幄。
老太后以为算计了天下而沾沾自喜,却不知意欲投入麾下的左郎是先帝的手笔…
左郎起礼后,回道:“臣得圣诏入宫,不急换服,请陛下太后治罪。”
太后自然不会追究这些索杂的礼仪,缓缓抬手示意。
左郎摆正了身子,已经做好了舌战群儒的准备,再不济也就是站着挨骂,难道还真的有人以为太后会杀了他不成。
礼部尚书楼当河曾是丞相赖桴源的学生,自然与左郎相对,便抬手起礼,质问道:“左郎大人,您可知余国上卿常梦命丧令阳!”
“知道。”左郎稳稳道。
“你方离开令阳,常梦便死了,现在有人说是你的部下杀了他。”
左郎道:“我奉太后之命,潜入令阳彻查余国调集粮草辎重一案,并未见过常梦大人,怎能是我杀的他呢?”
“左大人莫急,”楼当河如实道:“常梦车驾之后有铁甲随护,他们可说了,追杀凶手时,与使用狼头黑刀的青年交锋。普天之下,习惯用此刀的恐怕除了大人部下,就没有别人了吧。”
“抓到此人可与我对质啊,看看是不是我的部下,”左郎见楼当河摆出一副无可奈的模样,便继续说道:“看来是让那人给逃了。”
“好吧,”左郎继续说:“那持狼头黑刀的青年是都匀,公执司暗使。我回途时,以为是涟漪楼的门客追杀,便派他前去断后,岂不曾想是闹了场大误会。”
“那常梦之死岂不是与大人无关。”
左郎道“若是楼大人非要说是我杀了常梦,左郎只能说不善言辞,认下这口黑锅便是。”
站在右侧的外袍青年,挪步出列,向太后,陛下躬礼后,像是要替左郎辩解,他道:“臣是外臣,本该不便插手贵国朝堂,可心中实在难忍,还请圣人恕罪。”
太后抬手示意他起身,浅浅道:“贵使不必拘礼,尽管说来。”
“谢太后大量,”青年说道:“常梦死与令阳城东外,乃为余土,左郎大人是为军士,必然懂得侵土宣战的道理。再说凶手使用余国剑,刺入常梦胸膛…外臣看来,此事或真是冤枉了大人。”
左郎侧身看着青年,问道“这位大人面生,还未请教?”
“不敢,不敢,威国使臣吕望见过左郎大人。”他行礼道。
左郎上下打量此人,果有儒家风范,他浅手回礼。
随后从袖中取出文书,双手奉在掌上,秉给堂上:“此乃令阳城所得余国皇室亲笔帛文,请太后,陛下阅目。”
而另一边,鬼屠先生尤中客也有了动静。
宫墙之外,北衙公执司官衙紧闭,门前的官道列队站满了带刀的黑袍公执卫,他们哄走路边的商贩,对行人大声喝道:“公执司办案,闲人误伤,速速去开…”
赶走行人后,他们列队将北衙公执司包围的密不透风。
衙门内的刑场,独眼刽子手正在磨刀,发出惊悚的刺啦声。他穿着干净,坐在长椅上,背靠常青树,翘着二郎腿,嘴里不停低喃着:“老子杀了一辈子人,这么轻松的还是第一次。”
穿着二品官服的大员,还未来得及换上囚服,便被押到了肆防大牢的刑场上。
刽子手见状,朝刀口大喷了一嘴酒,即刻起身,向他走来,豪气道:“费那劲干嘛,还搞什么排场,老子直接给他的痛快的。”
押解大员的头头,竖起狼头宝刀制止他,他又道:
“看来是不想让他痛痛快快的…”
说罢他驾刀在背上,又回到了那颗树下:“你们这些人,心是真狠。”
头头收回刀,跟他说:“我的好哥哥呦,你也别为难我,您是知道的先生不来,出了事,我可就惨喽。”
刽子手指着头头道“你…你…你…又拿先生来压我,先生是你老子啊…”
这二位都曾是血染令阳的誉名将军,这同父异母的哥俩儿,哥哥随夫姓:刘大蟒,弟弟随母姓:柳当一。
这哥俩儿可不是一般人物,当年令阳之战役,百人架上圆石头与攻城车,在涂满竹茹、麻茹、小油、桐油、黄蜡、沥青作为辅助。拉撑着投夹与车身的缰绳掺有密密麻麻的轻钢丝,数名大汉持利斧奋力砍去,也没见它有丝毫动静,柳当一见壮,拔出狼头刀,飞跳起两人高,大吼一声“去开”!
就这一劈,绳子断了。
圆石头像是受了惊的野马,飞腾而去,弓手射出火箭击中石头,他顿时浑绕火焰,直扑令阳城墙!
与此同时刘大蟒所摔的重甲铁骑,也攻到了护城河,他们啊,硬是用活生生的肉体填平了这工事未成的护城河。
如今呐,他的一只眼睛还留在了哪里…
衙门被铁甲黑卫推开,随后文生被黑袍遮面的甲士抬着撵车跨进门槛。
不用想,京州城内除了皇帝宗室有这待遇的单此一人。
内场的二人听闻动静不对,便提早准备,将大员押解到刑场跪下,后点首退到一旁。
大官被缰绳束缚的紧,他两目呆滞,大愚若智般的盯着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文生:“尤中客,原来是你?”
文生面容消瘦,两目却是有神,说不上是秀气,却也谈不上寒酸:“尤某人本是唐城一落魄书生,受恩师点悟,后来林都府又得上将军赏识,这份感情,在下是记得的。各为其主,尚书大人莫怪…”
林国霑庆十一年,朝中大权任在老太后手中,多位大臣联合太后架空皇帝。
刑部尚书方新便为太后一党,他多次阻碍陛下夺取大权,可律法昭昭,怎能容忍。
尤中客便用丞相赖桴源将其设计,与大寒日,一把冰冷的火焰烧进了丞相府邸,公执司奉命追查,也不管是不是他,公执司的使命便是除掉帝王的眼中针。
在林国忤逆犯上可是死罪,他多次轻视皇权,即使有太后撑腰,也奈何不了多久。再加上丞相府的施压,太后也只能放弃这颗棋子,另立门近。
他眸窿深凹,捶死挣扎:“我是太后的人,你敢杀我吗!”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皆是我王臣民。”
他明白了:“原来左郎是陛下的人。”
尤中客示意甲士抬他到方新面前,如实道:“先帝创建公执司之初衷,便是为了除掉阻碍今日圣人执掌天下的贼,只是以前公执司还未与林之立足,需先自保。而今日之后就不同了,不管是老太后还是赖桴源,只要他们敢阻碍皇帝大权,下场都会与大人一般。”
方新万万也没想到,这个被朝堂遗弃,百官唾骂,宗室打压的公执司竟是霑庆麾下的杀人利器。
这么多年来公执司小小的衙门是多么的不起眼,他竟然还心存怜悯,没有早点拔掉这颗扎命的钉子。
“先生与我说这么多,看来我是必死无疑了。”
“大人若是愿意归顺陛下,便不会死,公执司三座衙门,数千文生也会为大人归还清白,待到霑庆盛世到来之前,大人必然是霑庆年的一代名臣。”
“我是死罪,”方新清楚的说道:“就是我愿意,你们会相信我吗?”
“自然是不会,可人生在世,谁还没个亲人,方家老少二十多口,尤某会替大人先照顾一段时间。”尤中客示意刽子手退走,又道:“大人的才略胆识异于常人,这也是陛下的意思。”
方新自然对自己的才略胆识无从质疑过,他仔细想了半刻钟也没有回复尤中客。
是回到太后身边做陛下的探人,还是忠于太后以死为鉴。
他一生清白,只是过于张扬了些,从而引火上身。
尤中客没有催促他,用一把火,换来的尚书,这是比稳赚的买卖。在说那把火要是能让他隐去趾高的心态,无疑是陛下麾下之利器。
又过了半刻钟,方新叫醒了正在打鼾的文生。
他同意了…
朝堂之上,老太后阅着帛书,眸色犀利。直到看到末尾的最后那段字“涟漪楼何姓之女,始出南国。”
他本不在意这些,更不会在意余国偷调粮草辎重,他在意的是今日之最大收获——公执司。
十一年来,公执司从不插手朝堂之事,也没有明确表示是谁的人。
可自从从月半前,左郎秘乘余国调兵遣将之始,她便察觉左郎有意归顺。
又以寻找何氏遗孤,再为试探。
如今,得知左郎是全心为自己做事,自然也要护住这将门之后。
十一年来,左郎被朝堂遗弃,可宗室百官只敢逞口头之能,却无一人敢动他。
不为别的,他尚有公执司数万人马,消息通天。数万人马扎进京师,谁不惧怕。手中更有先帝大令,可无诏入宫…
老太后想到这些,突然间发现,左郎这些年隐蔽的真是极好。若不细想,谁能知道,这隐忍了十一年的公执司,竟是这般家底。太后想通了这些,自然是要力保左郎,可众臣之言难辩,她只好将目光投向身边的傀儡皇帝,让儿子出这个头。
霑庆皇帝现在也只能做母亲的乖乖儿,他犹豫了一会儿,踌躇后问道威国使臣吕望:“先生游说列国,可曾去过余土。”
“回陛下,”吕望行礼道:“自然。”
霑庆皇帝又问:“先生以为我大林与余国相比,如何?”
“余国沃土千里,可终不及林,”吕望满志而言:“就拿两国帝都来说,余国上都城,广阔缭绕,美景犹如旖旎,可大多数被圈进了皇家园林,仅供一族观赏…而大林之京州城,竟显两字,霸气!逢节不宵禁,业成年林乐祖陛下曾言“欲杀寡人也,四城皆开,退去禁卫,误伤百姓!”这不是豪言,而是底气。”
好一个霸气,霑庆帝又问,余军与林军相比呢。
吕望言:“令阳之战,余国兵力大损,转而发展水军,吕望曾闻余之水师可媲与天下,可再下看来,余国边境三面环水,只可以自保。而林又不同,坊间说书人都言林之铁骑所到之处,皆为林土,上将军左公权一军,灭国十二足以为证。”
儿子的路铺好了,太后自然有话说了,她道:
“都说我大林是野狼山君,我大林就是一匹孤狼啊,纵使他多国联军,哀家也不怕。我大林也有水师百万,他敢来,可就回不去喽。”
她气息平稳。
“我朝堂之臣,还轮不到余国来处置。”
太后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众人也不敢再争论。
再说林律可管不到余国去,余法也插足不了林国朝堂,怪不得霑庆帝要让常梦死在令阳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