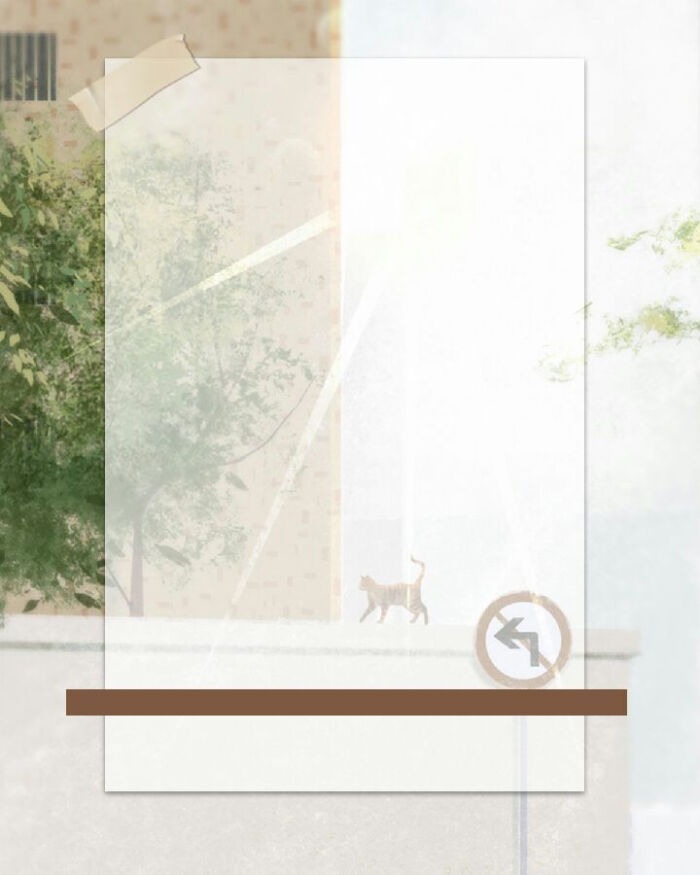九月初三清晨。
风停了,云层更低,半个手掌大小的雪花垂直地往下落。
五千士兵在城门外集结,雪已经淹没他们的小腿。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这些,因为他们知道这次不是演练,还在第一次战斗前的兴奋中。
城门楼上撑起盖伞,谢长书坐在下面,就等他一身令下。保险起见,这次由谢洛亲自带队。
谢长书眯起眼睛。他看到一条黑色的线从白音部族中延伸出来,在雪地里顺着官道往这边拉长。
“父帅,下令吧!”
城墙下,迎着纷纷降落的雪花,谢洛大声喊道。
“不急,再等等。”
白音部族有人前来,事情就没有到谢长书想象中的那样恶劣。他不会丧心病狂到随随便便就灭掉一个部族。
白音部族一行二十多人,拉着雪橇走的很是艰难。
等了半日,这行人才走到城前。
雪水渗入到士兵的鞋子中,初始的那股兴奋劲已经退去,现在就觉得寒彻骨髓,士兵心中开始焦躁。
距离士兵尚有五百步的距离,白音部族领头的老年牧民跪倒在地,一步一叩首地带着雪橇队前行。
雪橇上,放着牛羊皮和宰杀好的牲畜,还用红色的绸布系着。
士兵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奇怪地看着老年牧民一步一叩首的在军队中穿过,到了城门前跪倒在地,几乎把脸埋到了雪中:“白音部白音朝鲁前来觐见。”
谢长书看着跪在雪地中的白音朝鲁,没有说话。他有点失望,这不是他熟悉的人。想想也是,草原上的牧民,生活的环境更是恶劣,鲜有长寿者。恐怕他认识的那批人都已经不在了。
见没有人回应自己,白音朝鲁再次大声喊道:“白音部白音朝鲁前来觐见天朝大将军!”
回应他只有寂静的雪花。他不禁抬起头来,待看清城楼上坐着的人,更他的心如雪凉:“白音部白音朝鲁觐见谢天将军。”
谢长书稍稍一愣,随即笑了:“他竟然还认识我,让他上来吧!”
陪同白音朝鲁上去的还有一个年轻的牧民。这也是一个心中藏不住事的主,现在他就差直接在脸上写上“不忿”两个字了。
白音朝鲁诚恐诚惶地登上城墙,在谢长书面前先是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礼。
旁白的青年牧民在他的拉扯下,才不情不愿地施了一个同样的大礼。
谢长书盯着年轻的牧民,却是问白音朝鲁:“你认识我?”
白音朝鲁必敬必恭地答道:“当年白毛河一战,小民有幸瞻仰过天将军的容颜。”
谢长书呵呵一笑:“还真是荣幸,我还以为你们部族中没人记得我了!”
白音朝鲁只觉得口干舌燥,皮衣中闷热异常:“天将军天神般的雄姿,小民没齿难忘!”
谢长书依旧是呵呵一笑,笑声中带着嘲讽,手指向远处白音部族的帐篷:“我记得,我们有过约定。非约定的日子,牧民不能出现在百里范围内。我朝士兵无故去部落者、欺负抢夺牧民着杀无赦!那么牧民呢?”
汗水从白音朝鲁的额头滴了下来。按照这个约定,就算谢长书灭杀了他的部族,也没有一人是无辜的。
白音朝鲁咬咬牙:“这些决定都是我做的,愿意接受天将军的惩罚!还望天将军放我部一条生路!”
谢长书饶有兴致地指了指还悬挂着的三具尸体:“他们惊扰王妃的安眠之地,企图不轨。也是你做的决定么?”
白音朝鲁睁大了眼睛,这件事情承担不起。他知道里面埋葬着谁,能被称为天将军也不过就那几位,都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他无奈地说:“我不配做这个首领,愿意用命为部族赎罪!”
他的确很无奈,就算是搭上自己的命,对方愿不愿意接受还是未知数。
谢长书笑了笑:“这个我可以同意。但是城墙上的砖呢?”
白音朝鲁伏在地上战战栗栗说不出来话。
他身后年轻的牧民却愤恨的喊了出来:“我再陪你,命!”
他的官话不如白音朝鲁流利。
白音朝鲁大惊失色,想要拉他跪下,但是已经晚了。
身边的士兵还没有反应过来,腰间的佩刀就被谢长抽走。
年轻的牧民还在倔强不肯下跪中,刀如闪电划过他的肩膀,卸下了他的一只胳臂,顿时血流如注。剧痛让他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他几乎咬碎了牙,也不肯让自己发出声音,依旧倔强的站着,不肯跪下。
白音朝鲁正准备为他求饶。
谢长书正色道:“我不愿多造杀孽!半月之内,墙砖必须全部归还!念现在大雪封路,让你们离开这里就是送死,我特许你们开春之后再去寻找草场。至于这三具尸体,就在这里挂着吧!”
白音朝鲁谢过,忙带着年轻的牧民的下了城墙。失血过多,已经让他站立不稳。
应对受伤,牧民有自己的办法。他们给年轻的牧民止住了血,腾出一架雪橇往回走去。这恶劣的天气对伤口肯定是有影响的,至于能不能活下来,只能看天意了。
虽然他们弱者,谢长书有借势欺人的意思,但是让白音朝鲁无话可说。他以为他们不会再回来,结果却回来了。
按照以前的约定,谢长书真的屠掉他所有人,其他部落也挑不出来毛病。
他的部落男女老少都加起来不过六百多人,给易马堡中的军队塞牙缝都不够。后怕让他感到阵阵发冷。
对于这座城,谢长书有千般的计划,他要重新重新开凿护城河,他要在建窑打烧砖整修这座城。
这场大雪让他的计划无从实施,他有点意兴阑珊地看着白音朝鲁离去,吩咐谢洛:“散了吧!多准备点热水,让士兵都烫烫脚,别留下什么毛病。”
大雪让他计划延迟,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生死攸关。
武神庙内塘火还在燃烧着。两个人唯恐孩子孩子有什么闪失,轮流值夜,直到后半夜孩子退烧,吃了一些米汤后沉沉睡去,他们才放下心了,偶尔用手放到孩子的鼻翼处,试试他的呼吸。
现在是沈毅在照顾着孩子。
王大牛其实也是醒着的,许久没有睡过被褥了,他贪恋被窝的柔软。还有一个原因,他的草铺靠着墙,寒气直接冻透了墙,让他更不愿意离开被窝。
他又不得不起来,因为他憋不住了。
刚刚走到草帘处,他就忍不住一个哆嗦,掀开草帘先是感叹一声:“嗬!好大的雪。”
然后就是破口大骂:“这狗日的老天是不打算让人活了么?九月就下这么大的雪。”
抬头却看到郭氏和一个伙计正在门口徘徊,伙计手中还提着一个篮子。
没等他开口,郭氏却先迎了上来:“您醒了,孩子好了么?”
王大牛诧异她为孩子如此上心,这么一大早的就来询问孩子的情况:“托您的福,孩子好了。”
郭氏又问:“哪位大哥起来了么?我想上柱香。”
王大牛大悟,这是为了给郭大锅头祈求平安来了。忙说:“都起来了,您进去就行。”
庙内的情况有点尴尬。
这个庙本来就是为沈毅立的,他就没有拿他当回事。
神像前是供桌,供桌前就是沈毅挖出来的火塘。郭氏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但郭氏还是在供桌的一侧虔诚地摆上贡品点上了香,必敬必恭地磕了三个头。
沈毅的有点感叹。他这个正主自身都难,怎么能保佑别人。再说了这么大的风雪,真就如王大牛说的,老天爷要取人命。但愿郭大锅头能在停留在某个部落中吧。
郭氏站起身来,歉意地对沈毅笑了笑,从篮子中取出为他们准备餐点,欲言又止。
沈毅知道她想问什么,宽慰他道:“放心吧!郭大锅头带马帮这么多年了,肯定有应对的法子,会平安回来的。”
郭氏谢过他,走出庙。她何尝不知道沈毅只是在安慰她。她还觉得沈毅和王大牛一定有在草原上生存的经验,有心请两人去寻找郭大锅头。转念一想,却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知道是否郭氏每天的祈祷感动了上天,还是老天起了怜悯之心。在大雪第四天的时候,郭大锅头回来了,虽然只剩下半条命,不过也带回来了全马帮的人。
这让郭氏松了一口气。马帮中都是沾亲带故的,虽然说做这生意心中都有个准备,但是少了谁也不好说。
回来后的马帮在炕上整整躺了一个月才缓回来。就这样,郭大锅头还失去了两根脚指头,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维持这么大的一个马帮日常开销都成了问题。
意外的,沈毅解决了他这个大麻烦。沈毅用那块面目全非的腰牌和他约定,开春之后,郭大锅头找人给他盖房子,还得给他准备两头耕牛和四十亩地的种子。
普通百姓如此,军营之中也不好过。
城堡中旧的军营已经倒塌。新的军营还没有来得及盖起。薄薄的毛毡帐篷根本就抵挡不住寒气。
好在来此之前,谢洛做了准备,带上了旧的棉衣和被褥。所以,士兵尚能勉强应付。只是一个个的鹌鹑一样缩在帐篷内。对此,谢洛也无可奈何。
谢长书则是面对一份空白的奏折提笔放下,然后再次提笔还是没能落下一个字。他考虑的更多,白音部族是火你赤人中的一个的部落而已。相对来说,火你赤人性情还算温和。
更北的地方还有阿得人,被火你赤成为马背上的恶魔。历史上有多次南下的记录,每次都给火你赤人和关中人带来巨大的灾难。最近的一次,就是前朝末年。
白毛河一战,他们击溃的就是阿得人的主力。失败后的阿得人再次远遁草原以北,间接也救了火你赤人。然后才有易马堡之约。
这次天气异常,火你赤人守在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更北的阿得人受灾肯定更会严重,面对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会选择南下。但是易马堡这个样子……
最终,他叹了一声气,扔下了笔。
这奏折写与不写没有什么区别。写了也不一定能到皇帝的面前。就算能到他的面前,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盘算着怎么能摆脱这个困境。这场大灾后,流民肯定会多,弄一批流民来开垦荒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能解决重新建城的用工问题。
但是粮草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军中粮草不过是刚够用到开春。指望把持着朝政的大臣更是一个笑话。大臣都是名门贵族的代言人,名门贵族已经把怎么国家当成了自己的私产。
从他们手中弄点东西,不亚于铁公鸡身上拔毛。
谢长书就在书案坐到天黑,也没能理出来一个头绪。
一只信鸽摇摇晃晃飞进他营帐栽倒在书案上。
他皱了皱眉头,拿起信鸽。信鸽浑身冰凉,冒着大雪飞来已经是灯枯油尽。他解下一个小竹筒,竹筒中只有一张小纸条:“八月三十右安府庞天龙杀知府黄一安。”
黄一安他认识,建熙二年的恩科状元。只是和皇帝气恰好同姓,并没有特殊的关系。
这是一个正直的人,眼中更是容不得沙子。
他很欣赏这样的人,暗中对黄一安多有照拂。后来更是让他去了江南做了知府,还准备以后重用他来着。
庞天龙他也知道。燕北望族庞家的子孙。作为和这些人妥协的交易,黄山平把他安置到了军营中,镇守右安府。
右安府在易马堡的东边大约二百多里。
最初,它的作用和易马堡类似,并且和易马堡还能相互呼应。只是那里并没有出现瘟疫,所以渐渐的成了一个府,也是长城外唯一的一个府。
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黄一山到了这种地方,还惨死在了庞天龙的手上。
他不禁叹气。这些家族越来越过分,开始肆无忌惮地清除异己了。朝廷刚刚建立了二十多年,就要改朝换代了么?
他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夜风又起,卷开了营帐的门帘,带进来团团雪花。
夜幕中,一团巴掌大的雪花带着虚影逆行上了天空,向南消失在夜幕中。
他轻蔑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