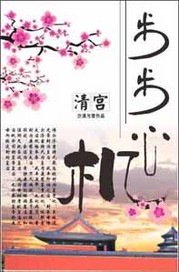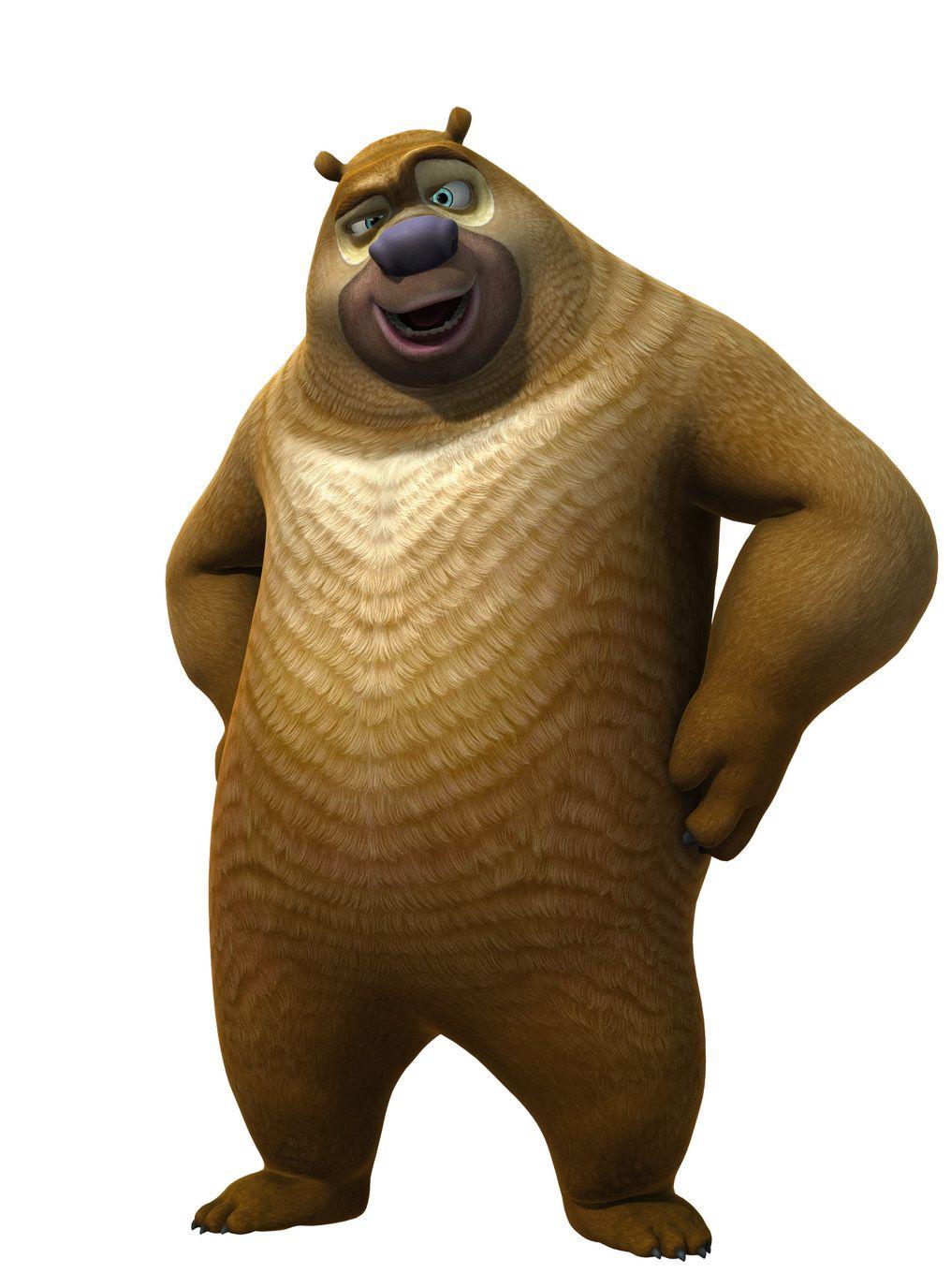储秀宫中,炎修羽坐在一座亭子里,一身粗麻布衣裳,神情淡且宁静。
他本以为自己上次闹过那场拆屋大戏,可以让太子答应定时见到家人,没想到,见了柔福长公主一面后,却反被她劝诫,不要在宫中那样闹,因为极有可能他遂了心愿,而宫外的炎王府会倒大霉,乃至于会影响到严清歌,甚至她舅舅那边。
柔福长公主说,她会尽量给炎修羽争取到见家人的机会。面对那样的保证,炎修羽最终只能无奈的点头。
但是,他心里却不是那么好受的。
生平第一次,他在心底隐约感觉到了点什么——成家以后,曾经的那个嫂嫂,好像和以前的那个嫂嫂不太一样了。
具体在哪里,他说不出来,却可以敏锐的感觉到。
柔福长公主好像说的很对,是的,他可以不顾一切的抗争,但是去不能不顾及家里人会受到的影响。但是,他心底深处总有个东西告诉他,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先前柔福长公主的保证,让他很是失望,他明白的很,那保证兴许就只是一个保证,要实现真的非常难。但没想到,还没到八月,便有了机会。
他目光悠远,紧紧的盯着储秀宫通向外面的出入口处,不放过一点风吹草动,终于,那小路尽头,走来了两个人。
太阳升起来有一阵子了,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地面,将七月末夜里起的白露一点点晒干。天气似乎有点热,也似乎有点冷,就像他现在这颗七上八下的心一样。
炎修羽的淡定顿被抛到九霄云外,他忽的一下站起来,顾不得旁边紧密盯着他的太监们,快步迎了上去。
只见严清歌也是急着见他,竟然一时间顾不得礼仪,看到他的一瞬间,就加快了步伐,越过柔福长公主,几乎是踮着脚,提裙小跑起来。
他瘦了!严清歌想着。
她瘦了!炎修羽想着。
二人的眼中只有对方,直到严清歌一头扎进炎修羽的怀里,用头发顶着他的心窝蹭了好几下,将热泪在他前襟压干,才重新抬起头。
炎修羽伸出大手,轻轻的摸了摸严清歌脸颊,灿若星辰的眼眸离都是心疼。
这是他的妻子,他最了解。距离上次不见,严清歌的身上多了点儿不一样的东西,若说之前的她是古琴上的琴弦,现在的她,就变成了弓箭上的弓弦。
这两种东西猛一看不都是一根线形的东西么?但实际上绝对是不一样的。
他的清歌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
炎修羽贪恋的吸着鼻端她身上的香味,一颗心却是沉甸甸的。
“羽哥,我好想你。”趁着旁人还没围过来,严清歌的大眼里全是委屈,对着炎修羽娇嗔的说道。
“我也好想你。等我!”炎修羽心里一阵儿不好受。
“耐心等舅舅,他有办法。”严清歌小声又含糊的交代一句。炎修羽的眸子微微一缩,不动声色的握了握严清歌的小手。
就这么一小会儿,旁人都赶了过来,严清歌和炎修羽也分开了,方才两人拥抱的一瞬,就似所有情不自持的男女一般。只有那几名太监略带怀疑的看着炎修羽和严清歌,觉得他们一定背着自己交流了什么。
“来亭子里说话。”炎修羽微笑着给柔福长公主行过礼,牵着严清歌的手朝亭子上走去,落落大方,完全无视那几名太监好像要将他们身上烧出个洞一样的目光。
柔福长公主对此也恍若没看到一样,被两个丫鬟服侍着,敛步上了亭子台阶。
尽管有人看着,但炎修羽早就习惯了所有的举动都暴露在旁人目光下,只将那些看守的人当做空气,旁若无人的和严清歌说着话,甚至连柔福长公主都沦为陪衬。
严清歌见他这么重视自己,一时间,觉得这些时日吃得苦都值得了。
“清歌,来,我给你摸摸脉。这些时日在宫里面无聊,我学了些医术。”炎修羽淡淡道。
严清歌乖巧的伸出一截皓腕,放在石桌上,炎修羽似模似样的将两根手指搭在她温热的皮肤上,黑长的睫羽微垂,过了好一会儿,又换了她另一只手摸。
“你最近没有好好吃饭!”炎修羽盯着严清歌,说道:“你的胃本就不好,怎么可以这么对自己。”
严清歌没想到他竟然真能诊出些什么,着急辩解道:“不是我不肯好好吃饭,是前些日子热,我有些苦夏。”
“胡说!我摸你的脉象,你前段日子饮了酒,催吐过,何必找苦夏的借口!”炎修羽的眼底闪过一丝狡黠,面上却时一本正经。
严清歌的手指轻轻一动,在炎修羽的手腕上扣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哪里会诊病,根本就是有人一直在给他通风报信,告诉他严清歌的情况。上回严清歌饮酒催吐,是欧阳少冥的手笔。再联想到炎修羽现在学医术,必然不会是简单的自己看看医书,怕是叫了御医院的人指教,而欧阳少冥又是御医院的院正,一切变能说得通了。
严清歌咬紧素唇看着炎修羽,微微嘟嘴道:“只是饮了一小杯酒,有什么大了。若不是苦夏,我也不会吐呢。”
见她将头骗过去,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炎修羽急忙哄了哄,明明知道是在做戏,可是生怕她真的不高兴了。两人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会儿时间,他不要看着他的宝贝难过,哪怕是假装的都不可以。
柔福长公主给晾在一边儿,半句话都没说上,索性只是将目光朝亭子外四处打量,似乎在欣赏着夏末的风景一般。
严清歌心里柔情似水,跟炎修羽小声窃窃私语,一副快要化了的样子,倒是很出柔福长公主意料之外。
这些时日,严清歌越来越脱离掌控,让她这个做嫂嫂的,未免多想,甚至使了一些不该动在自己家人身上的手段。
现在看来,严清歌的心中,还是只有炎修羽。早知如此,她今天绝不会交代下去让人办那件事了……
她心中的后悔没什么用,现在的严记绣坊,已经乱成了一团。
丫鬟们的尖叫声此起彼伏,翻箱倒柜声,呵斥怒骂声,乃至瓷器落地的噼里啪啦声,掺杂着阿满跟炎婉儿吊着童声的高嗓子,甚至是不是出现的皮肉相击殴打声,让整个严记绣坊的后院,鸡飞狗跳,热闹非凡。
鹦哥嘴角带血,给一名身强体壮的嬷嬷一巴掌打到墙角去,却还是哀求道:“陈姑姑,您这是做什么,有什么事,等娘娘从宫里回来再说。”
“臭蹄子!生你养你的是炎王府,没有炎王府,你早不知道给卖到哪家楼里头去了,现在胳膊肘拐到哪儿去了?我问你,雪燕呢?”
这姑姑一边骂着,一边走上前,巴掌抡圆了,不等鹦哥回答,噼里啪啦就是一阵猛扇,打的鹦哥眼冒金星,差点儿昏死过去。
鹦哥当然知道雪燕怎么了。她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连翘邀请雪燕一起去厕所,中间连翘回来,说鹦哥没带草纸,回来拿知给她送去,结果人还没离开,就有人来报信,说雪燕掉进粪坑里了。
绣坊里住了近百口人,厕所底下用的是巨大无比的粪缸储存肮脏物,每过几天就会有乡下人来掏粪,但好巧不巧,那天恰好里头东西满了。雪燕本来身量就不高,下去就给淹个死死的,捞上来以后惨不忍睹。
旁人都嫌恶心,不敢碰,还是连翘一阵阵哭,说自己不该拉雪燕姐上茅房,亲自上手把她拾掇干净了送行。
除了鹦哥,没人怀疑连翘这个才一点点高的小人儿,大家都只说连翘人小却重情义。
雪燕是个机灵的,在炎王府的时候,就喜欢攀扯,那姑姑想来和她有旧,也不知道是不是雪燕认得几个干妈之一。打起鹦哥来,毫不留情,真真是下了死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鹦哥给打的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而院子里的混乱,还在继续着。
“快找!哪儿都别放过,床底下也搜了!把那大点儿的柜子全都打开,匣子里头东西都倒出来,仔细敲仔细摸,看哪儿有夹层。” 一名气势汹汹的婆子以手叉腰,站在庭院中间,指挥着众人动手。
今天来的这些婆子都是炎王府里的精英,颇有几分地位,以前见了严清歌,虽然说不上不卑不亢,但还是能得几分脸面的。
但今天,她们半点尊重都没留,恨不得将严清歌的房子拆了。
阿满虽然太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懵懂的给炎婉儿护在身后,但在看到一名婆子将他箱笼里的玩意儿全都倒出来在地上以后,忍不住迈着小短腿跑过去,一把将几个布偶揽在怀里,道:“阿满的!不要动!”
炎婉儿到底大了些,赶紧拉住阿满,道:“阿满,别跑!”
她害怕极了!
听奶娘们说,早上婶婶来叫娘亲一起进宫去看爹,谁知道娘亲才走,这些人就冲进来,大搞破坏。她亲眼看到鹦哥给打的满脸是血,昏在墙角,她的一个奶娘因为护着她不叫那些嬷嬷们动,也给揪着头发往墙上撞。
炎婉儿从来没受过这么大惊吓,哭了一会儿,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弟弟牢牢抱在怀里。只有姐弟俩相互依偎时带给对方的体温,能叫她那颗狂跳的幼小心脏稍微安稳些。
站在院子中央的那吊梢眼嬷嬷冷冷的看了姐弟俩一眼,有看看阿满手中填了棉花的玩具,冷冷道:“拆开来!看里面有没有藏着什么信啊,纸条啊!有些不自重的,连自己的孩子都要利用!”
炎婉儿和阿满当然听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不妨碍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几名嬷嬷冲过来,强硬的把东西从阿满手里拽走。
“刺啦!”
洁白的棉絮露了出来,曾经陪伴着他们玩耍,由严清歌亲手制作的可爱小玩具,成了一堆破布和散棉花。
阿满嚎哭起来,而炎婉儿也泪流满面。
娘亲,你到底在哪里啊!